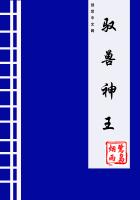庐州,南郊,风和日丽,春风习习,一个平静而普通的下午。
一辆四匹马牵引着的马车在林间小道上疾驰,随行的还有一人一马,护卫模样。
这马车远远看去便知不是来自一般人家。大齐对于马车所用马匹的数量有着严苛的规定,一般的有钱人家只允许用一匹马拉车。若是做了官进了爵,才可以用两匹马。当看到有三匹马时,那行人就要注意避让了,这里面坐的八成是个大人物。而像这种四匹马拉的车,大多是皇亲国戚,出了京城可不得多见。再说这马车,也是极尽奢华。车顶、窗沿镶金嵌玉,车轴、车轮都用的是上好的木料,由崭新的铆钉牢牢固定好,在阳光下泛着紫铜特有的光泽。
如此排场,马车中坐的会是谁呢?
“三弟,没想到此次庐州之行竟能如此顺利,理当庆贺才是,为何还如此闷闷不乐呢?”马车内,一个大腹便便的中年男子捧着一袋子干果零食,已吃了一路。
车窗边坐着一位文质彬彬的公子,白白净净一副书生气质,一手搭着窗沿望着路边大片大片荒废的田野,想着自己的心思,并未在意有人唤他。
车上这两位正是大司徒方霍家的大公子方恒邑和三公子方恒轩。
“恒轩?”方恒邑见弟弟在神游,拍了拍他,“想什么呢?”
方恒轩这才回过神来,忙答话道:“大哥,庐州也算是鱼米之乡,近一年来风调雨顺未曾听说过有什么自然灾害,你看眼前这番景象,良田无人耕作阡陌不见行人,实在蹊跷。”
“蹊跷什么?想来是给卫扬这老狗给剥削的,这里是他的封地,还不是随他胡闹,连私盐坊他都敢开,还有什么他不敢做的?”方恒邑不屑道,“再说了,三弟你这是出门少了,这些年比这惨的光景哥哥也见的多了。”
“也是。”方恒轩轻叹一口气,“苦了庐州地界的百姓了。”
听他这么一说方恒邑乐出声来:“三弟到底是承载了父亲的希望,我大齐将来的昌盛还得靠三弟来主持啊。”
“大哥见笑了,”方恒轩摆手道,“只是协助父亲处理一些琐碎之事罢了。大哥一己之力挑起我方家商行重担,才是我方家脊梁。”
方恒邑摆摆手笑道:“你打小聪明过人,好读四书五经,深得父亲喜爱,如今父亲也有意在政途上栽培你,倒也甚好。你哥哥我向来不爱官场上那一套套,拘束得很,像如今这般时常走南闯北岂不逍遥自在?只是有时想来,这官场到处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你从小心性善良,下不了害人的心就算了,没有个防人之心怕是会吃暗亏啊。”
“我倒也不是没有防人之心,只是懒得勾心斗角罢了,凡事都摆在台面上说开了,岂不公正轻松?若真遇上了小人我向来是敬而远之的。”方恒轩为自己辩解道,“好比方才,换我选择定还是选择走那官道来的省心些,这条乡村野道从未走过,又人烟稀少,我是不愿冒这个风险的。”
“三弟,出门前爹爹吩咐过,此事贵在神速,我们越是快,留给卫扬那老贼收拾烂摊子的时间也就越少。再说了,如今太平盛世朗朗乾坤,你大哥我平日里走南闯北,几乎都未遇到过什么意外,这回总不至于这么点背吧?”方恒邑满不在乎地回道。
方恒轩不说话,继续望着窗外,废弃的田野已是再也不见,取而代之的是大片大片的竹林,由近而远延伸至眼睛所能及的尽头,绿茫茫的一大片,风过时带着竹叶的清香,他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
“三弟,有时候你们读书人又过于呆板了,凡事要讲究个变通嘛。就算真要遇上什么不测,我们这不还有薛岳和潘贵护送么,好歹他们也是京城的十大高手,在这荒山野岭里一般小毛贼奈何不了他们。”方恒邑仍在喋喋不休,然而他说的越多,越像是在自我安慰,言语里透着不安起来。不知为什么,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上他心头。
风儿可劲地吹着,竹林如江面般波澜迭起,远处半山腰隐隐约约可见一四角竹亭。方恒轩眯起眼睛,这会是何人所建?在这山间沏上一壶清茶,或邀三五好友,或翻翻经书典籍,不必顾及世间的纷扰,倒真是好不痛快!
就在他心生怯意时,马车突然一个急停。方恒轩反应及快,一把抓住窗栏才稳住平衡,方恒邑则没那么幸运了,满身横肉的他就像一个球一样直接滚出了车外。
见到大公子这么滚出来,负责驾车的薛岳连忙搀扶起方恒邑。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方恒邑气急败坏,一边挣扎着调整好坐姿。
薛岳朝前方指了指,只见十几丈远处一人一马立于小路中央,挡住了他们的去路。来人蒙着面穿一身夜行服,光天化日下显然来者不善。
方恒轩侧着身子望向窗外,心说,好嘛,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方恒邑这些年到底走南闯北也算是老江湖了,深知出门在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强龙不压地头蛇嘛。对他而言,能用钱解决的问题都不算问题。于是他笑脸相迎道:“这位英雄,我们几个是做小本买卖的,路过此地,不知是否误闯了兄弟的地盘,还望行个方便。”边说边从身后摸出一袋银两扔了过去,补充道,“出门在外大家都不容易,还望兄弟行个方便……”
这一幕方恒轩看在眼里,心中却充满无奈。此人明显是早有准备,与一般的山匪强盗不同,很有可能是冲着他们手上这刚得手的账本而来,大哥想的也太简单了些。
果不其然,黑衣人对于方恒邑扔来的钱袋无动于衷,钱袋重重掉落在地上,里面的碎银子散落了一地。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黑衣人纵身一跃便飞速杀来,身形精壮如一道黑影。薛岳潘贵连忙拔剑相迎,三人厮打在一起,一时间刀光剑影难舍难分。
“这可不好了,咋办?”方恒邑眼见着薛岳与潘贵两人联手都未能占到上风,立马慌了神。他以往行走江湖倒也不是没遇过险情,但每次都能花钱消灾。反正他方家富可敌国,这笔买卖亏了下笔再赚回来,毕竟遇上劫匪的可能性还是很小的。可如今眼下真打起来,他慌了神。
“哥哥莫急。”方恒轩安慰道,“来人想必与这方家的私盐坊有关,冲这账本而不冲人,不会伤及我们性命的。”
“此人来势汹汹,杀气逼人,三弟又怎么能断定他不会赶尽杀绝?”方恒邑脸上豆大的汗珠不断渗出,嘴里喘着粗气。
“来人未接你的钱包,说明不图财,敢单枪匹马来劫我们四人,说明早有准备和谋划。还有,你仔细看这人使的剑法,不正是卫家的岱宗七绝么?虽说还不精熟,但已经让薛岳潘贵难以招架,可见这岱宗七绝实在精妙。”方恒轩淡定地观察着战局,还不忘点评一番。
“看不出来,原来三弟你还懂剑术啊。”方恒邑惊讶道。
“曾经的一位故友喜欢舞刀弄剑,那会时有讨论罢了。”方恒轩叹道。
说话间,潘贵被黑衣人一脚踹在胸口,摔倒在地,薛岳也渐渐招架不住。
方恒邑愈发的紧张,甚至方恒轩能清晰地感知到他的颤抖。
他忙抚了抚大哥的背脊道:“哥哥莫慌,此人是冲着账本来的,到时候给他便是。”
“万一是要杀人灭口怎么办?”方恒邑仍在抖个不停,本是春寒料峭的天气,却出了一身冷汗。
“这可是卫家的封地,卫扬还没有糊涂到在这里要对我们下手。卫家与我们这些年来向来水火不容,若是我们在此地有个三长两短,他老人家如何推脱嫌疑?待会若无他法,直接将这账本交于这黑衣人好了,也让薛岳潘贵他们少受些罪。”这么说着方恒轩去马车内的锦盒里翻出账本。
“倒是可惜了,本以为顺顺利利,谁知乐极生悲,唉。”方恒邑叹道,“只怪我方才一意孤行,未听取三弟的意见。“
“倒也无大碍,这账本昨晚我已连夜翻阅了一回,大致的厉害还是记得清晰的,脱身后默下来便是。”方恒轩淡淡地说道。
方恒邑一拍脑门道:“瞧我这记性,将我三弟这过目不忘的神技居然给忘了……”
两人正说着,只听又是一声惨叫,潘贵的肩胛骨中了一剑后倒在地上。紧接着黑衣人又是雷霆万钧地朝薛岳刺去,薛岳只能下意识地格挡了一下,然而来剑太猛却未能完全挡开,剑刃接着余力冲着薛岳的肩膀划下一大道口子,鲜血立马涌了出来。
眼见着自己最后的保护屏障被摧毁,方恒邑更加紧张起来,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昔日翩翩贵公子又何曾体会过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恐惧?倒是这方恒轩依旧镇定自若,毫无惧色地盯着这黑衣人。
黑衣人并不急于解决掉已负了伤的薛岳和潘贵,而是朝这马车走来。
就在方恒邑心里求爷爷告奶奶,又屡次陷入绝望时,一个白衣剑客从一旁的竹林间突然杀出。方恒轩的视线刚落在这身影上,就被剑身折射出的一道寒光晃通了眼睛。再等他看清时,白衣剑客已与黑衣人撕斗起来。
好凌厉的剑气!方恒轩感叹道,目不转睛地盯着这白衣的身影,不知何故,不论剑法还是轮廓,竟然都看着有那么几分眼熟。过了好一会儿,他才说服自己,这白衣剑客不是别人,正是几年前还与他称兄道弟的同窗好友——司空念!
远处,司空念正杀得兴起,好久没有和叔父如此比剑了。从小在他眼中,叔父是一座不可逾越的大山,无法战胜。这些年他幽闭南宫阁苦练剑术与身法,为的就是有一天能与叔父再比试一番,可叔父日理万机总有事物要忙,每次相见便又匆匆别离,哪有这闲工夫陪他比试。今天他算是等来了这么一个机会。
宇文昊也是用心良苦,一方面要刻意模仿卫家的岱宗七绝,一方面经过刚才的缠斗后体力有些不支,面对着使劲浑身解数的司空念终是招架不住。既然眼下该演的戏份他都已经完成,他也无心陪司空念玩下去,虚晃了几招后便夺马而逃,留下还没过足瘾的司空念。
即将与故人重逢,确要以假面示人,司空念感到一阵莫名的心虚与紧张。
“司空念!”
那个无比熟悉却又有些陌生了的声音。
他们曾是坦诚相待的同窗,曾是无话不谈的知己,然而时隔多年,他却需要用这一场戏来与他相见,更要命的是,这还将是一场永没有谢幕的戏。
‘每当你心慈手软,就当去想想你司空家的三大仇人,想想你素未谋面的父母是如何惨死在他们手中……’叔父的叮嘱又回响在耳边。这方家不也正是自己的世仇之一么?在杀父弑母的大仇面前,所谓的兄弟情义又算得了什么?欲成大事者,怎能被妇人之仁所困?
司空念迅速收起了他脸上的不安与愧疚,摆出一副惊喜的模样,要多自然就有多自然。
在确认了这位白衣剑客正是自己昔日的故友后,方恒轩总算是放下了心,跳下马车朝他走去。
方恒邑更是喜形于色,嘴里念叨着:“自己人好,自己人就好!”
方才那一幕他给吓得不轻,走南闯北这么些年积累的胆识这一下午就给扔得无影无踪。
司空念并未急着与方恒轩聊天,而是先给薛岳和潘贵检查伤势。
“可有大碍?”方恒轩问他。
“皮外伤,好生静养些时日便可。”司空念答道,心中暗暗感叹,叔父这下手真是恰到好处,再轻些容易露出破绽,再重些又要伤及性命。
“属下无能,让二位公子受惊了。”薛岳忍着胸口的剧痛欠身道。
“来者非善类,怪不得你们。”方恒轩安慰道。
说话间,方恒邑走到他们跟前。他体型肥硕故而行动缓慢,迈着小碎步没走多远便气喘吁吁,见了司空念满脸堆笑道:“这位英雄便是三弟在白鹿院念书那会认识的故人吧?多谢相救了。”
司空念上下打量一番来人,暗想这方家家业的继承人果然不一般,如此肥头大耳,生意上的油水一定没少捞。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便是方恒轩,一副文弱书生的样子,实则骨子里是个倔脾气。
“真没想到能在这儿遇见你。”方恒轩的话语透着惊喜。
“方才路过这竹林,恰巧远远看见有人在厮杀,没想到是你们。”
“司空兄路过此地也是有差事在身吗?”
司空念摇了摇头解释道:“离开白鹿院后,我便流落于此地,幸得南宫阁老阁主收留。每日为阁中做些事情,维持生计。让二位公子见笑了,方才我正巧是要去捡拾一些竹料,谁知正巧遇见你们。”
“南宫阁?”方恒轩两个眼睛瞪得滚圆,“你说的可是号称民间藏书第一楼的南宫阁?”
“正是。”司空念笑道,暗想这书呆子果然还是个书呆子,一听到书便如此来劲。
“久闻这南宫阁生了些变故,已不复昔日的辉煌,但书籍经卷可一样未少。昨晚我还与哥哥说道想来拜访,没想到在这竟能遇见了你。”方恒轩脸上写满了兴奋的表情。
他乡遇故知,也是人生一大喜事吧,何况故知还替他们解了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