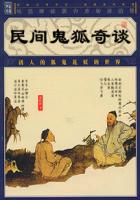“齐遥光,你可知罪?”杨广面色阴沉,语气一片冰冷。
“回陛下,臣不知身犯何罪。”齐遥光跪在地上,腰背没有因君王的威势而有一丝弯曲。
挺拔的身姿又和昭容夫人回忆深处的某个人影重合起来,她暗暗想道:“怎么我和平阳母女二人都钟情于这样满身傲骨、才华横溢的白衣佳客?”随即低低叹了口气,轻声道:“陛下,齐大人如今的身份满朝皆知,他怎么会胆大包天,做那些陛下深恶痛绝的事?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
齐遥光的身姿同样勾起了杨广遥远的回忆。和昭容夫人不同,在杨广的回忆中这个身影没有一丝柔情蜜意,而是充满了狠毒与残忍,让他克制不住心头的暴怒。
“身份?他有什么身份?朕给了他什么身份?”杨广转过头,恶狠狠地盯着昭容夫人。昭容夫人的嘴唇动了两下,终于还是没有再说话,缓缓低下了头。
“齐遥光,你只是一个区区二品侍郎,却包藏祸心,妄图结党营私,翻动风云,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吗?”杨广的声音中还是充满了冰冷。
齐遥光愣了一下,随即道:“回陛下,臣只知忠君报国,恪尽职守,在朝中也仅与同科士子户部的相大人交好,没有与其他任何一位大人交往过密,结党营私一说,实在不知从何而起。”
杨广的脸色更加阴沉,道:“靠山王,把你在信中向朕禀报的说给齐遥光听,我看看他还有什么可狡辩的。”
齐遥光闻言将目光转向杨林,心道:“我好意拉你出泥潭,你却栽赃我结党营私,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
杨林感受到齐遥光的目光,坦然道:“是,陛下。齐大人,本王并没有向陛下参你结党营私,一切只是据实禀报,其中是非如何陛下自有圣断。”
齐遥光琢磨着杨林话中的含义,没有说话。
杨林从容的声音仍然在紫微殿里飘荡:“两个月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齐大人忽然光临寒舍。那时臣正奉圣命在京城外的别院修养,每日逍遥自在,心情舒畅,少有朝中同僚来访,忽然听说齐大人光临,臣也有些意外,但还是将齐大人引了进来。”
“齐大人在后花园中与臣相谈,用御赐的金牌支走了陛下派来的天机悬侍卫,要求臣与他一同查一件案子,但并未说明究竟是哪一桩案子。臣未得圣旨,不敢轻易应承,便随口应了几句,齐大人话锋一转,又问臣是否真的安于现状,要做一只温水中的青蛙。臣听不懂齐大人的话,客套了几句便将齐大人送出了府。”
“可齐大人走后,臣越想越觉得他的话不对劲。齐大人是刑部侍郎,查案是他的本职,可臣不司刑狱,他查案子来找我干什么?就算有什么疑难需要本王协助,他也大可以开口直说,何必遮遮掩掩?更何况臣荣升亲王,能在京郊立府,那是陛下天大的恩赐,满朝皆知,这安于现状、温水中的青蛙一说又是从何而来?”
“臣左思右想,觉得齐大人这话有些蹊跷,不敢隐瞒,便上书陛下,以免日后有什么变故时说不清楚。”
杨林一席话说完,齐遥光听得心惊肉跳,心想:“我当时与你说好的,此事绝不可外泄,怎么一转头你就告诉了陛下?再说我找你帮忙,也是为了共同对付天机悬,洗脱你身上的冤屈,哪里存有什么私心?你这么掐头去尾地向陛下一说,陛下会怎么看我?”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可这话充其量也就是查案手法有不妥,话语间有些不敬,皇上又怎么会想到结党营私上去?”
杨广冷冷地道:“齐遥光,你还有什么话说?靠山王是朝廷重臣,是朕的左膀右臂!朕让他在京郊立府休养,是体恤他多年的操劳。可你呢?到你嘴里怎么就变成了温水煮青蛙,好像朕要对靠山王有什么不利之举,你这分明是在挑拨君臣之间的关系,想要拉拢靠山王为自己所用,用心何其歹毒!”
杨广这话说得很重,萧皇后和昭容夫人都暗暗替齐遥光捏了一把冷汗。但这时杨广正在气头上,两位娘娘说什么也不敢开口相劝。
平阳公主听不懂这些话里的玄机,只是觉得齐遥光一向对自己很好,父皇一定是冤枉他了,鼓足勇气道:“父皇……”
杨广猛然回头,厉声喝道:“闭嘴!朝中大事,什么时候轮到你一个十几岁的小丫头插嘴?”
平阳公主吓得不轻,小嘴一撇,眼看就要哭出来。杨广怒道:“萧氏,你是怎么教化宫廷的?紫微殿是朕议事的地方,平阳怎么敢在这里放肆?这还成何体统?”
萧皇后赶紧拉过平阳公主,道:“陛下,是臣妾教导无方,请陛下息怒,臣妾这就带平阳回避。”说着向昭容夫人使了个眼色,两位母亲将平阳公主连拖带拽地领出了紫微殿。
看着亲生女儿瘦小的背影,铁石心肠的杨广心里终于还是软了一下,暗暗叹了口气。
齐遥光心道:“陛下……陛下怎么竟然想到了这些?夺靠山王兵权这是满朝文武心知肚明的,他自己也清楚得很,我何曾有过半分挑拨之心?”但这话终究不敢说出口,转头看向杨林时,杨林仍然恭恭敬敬地垂手肃立在堂下,脸上没有一丝波澜。
杨广的责难仍在继续:“还有朕交给你的案子。靠山王手掌兵权,不司刑狱,按律除非他自己犯法,否则任何案子他都不能接触,就算有什么大案需要他协助,你也要向刑部申请,等朕准了才能去找他。可你倒好,一声不吭,擅自跑到靠山王府上胡说八道。”
杨广的目光忽然锐利起来:“齐遥光,朕问你,朕交给你的案子是绝密,你到底有没有向靠山王透露?”
齐遥光面色坦然:“回陛下,臣没有。”齐遥光也不算说谎,他确实没有向杨林明说究竟是什么案子。
似乎是齐遥光平日里一贯忠直的性格深入人心,杨广犹豫了一会儿,还是相信了齐遥光的话,脸上的神色略见缓和:“那你还不知罪?”
齐遥光挺拔的身姿微微颤抖了一下:“臣知罪认罪。”
杨广和杨林没想到齐遥光的态度忽然转变,这么爽快就认了罪,两个人一时倒不知该说些什么。齐遥光略微停顿了一下,紧跟着朗声道:“但是臣只认查案不规、言语不敬之罪,绝不认结党营私之罪!”
一股杀气腾的一下从杨广身上散发开来,凛冽逼人,连杨林也禁不住倒退一步,跪了下来。
“你说你没有拉拢靠山王结党营私,可有证据?”
齐遥光的声音依然清朗得没有一丝犹豫,在君王夺人的威势中屹立不倒:“回陛下,臣没有证据。但臣忠于陛下,此心日月可鉴,若说私心,也不过是担心此案牵扯巨大,牵连家人,才想尽快破案,绝没有半点拉拢党结之心。”
杨广目光猛地一收,缓缓站了起来,一步一步走下龙椅,逼近跪在堂下的齐遥光:“好,你说你没有拉拢之心,那就证明给朕看。”
迎着杨广缓缓走近的身躯,齐遥光心中终于感觉到一丝压迫,他的目光开始颤抖起来。
杨广走到齐遥光面前,从怀中摸出一柄匕首递了过去。
齐遥光大惊失色,一个头重重磕在地上,道:“陛下,臣万死也不敢在陛下面前手持利刃。”
杨广脸上闪过一丝残暴,声音再度变得冰冷刺骨:“朕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不然朕当庭治你一个抗旨不尊之罪!”
齐遥光只好低着头接过匕首,大气也不敢喘,生怕杨广安他一个身携兵刃进殿行刺的罪名。
但杨广接下来的话比强安罪名还要离奇。
“齐遥光,你说你没有拉拢靠山王的企图,那你当着朕的面把靠山王杀了,朕就相信你。”
齐遥光的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他做梦都没想到杨广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
“陛下,靠山王是朝廷重臣,臣怎么敢……”
杨广忽然咆哮起来:“你不杀他,朕就杀了你全家!蔡奉!”
蔡奉低着头推门进来,缩在门边候旨。
“传令天机悬,杀齐遥光满门!”
蔡奉大气也不敢出,跪下来磕了个头,也不知是遵旨还是不遵旨。
齐遥光猛地跳了起来,死死捏住匕首,咬牙道:“陛下息怒,臣动手就是。”
杨广将手一挥,蔡奉知趣地又退了出去。
杨广将目光转向杨林,没有丝毫要解释的意思。杨林将双手背在身后,坦然迎上杨广的目光,脸上甚至还浮现出一丝微笑。
齐遥光颤抖着走向杨林,低声道:“靠山王,对……对不住了。”
杨林云淡风轻地道:“不妨,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本王没有怨言。”
齐遥光回头看了看杨广,大隋皇帝冰冷的脸上依然写满了残暴和酷烈,他知道,这一刀在所难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