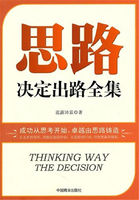两人不多时到了凉州城,季吉一路东张西望,甚是新鲜。凉州城灯市如昼,身着各族服饰之人怡然自得,在夜市中穿梭而行。季吉叹道:“何曾想一个边陲小城,竟是如此繁华。”
洛哲笑道:“原来你也是爱热闹的,一向不知热闹为何物罢了。”
季吉一抬眼,忽见前面一座楼台张灯结彩,门庭若市,喧嚣之声由内而外不绝于耳,招牌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她不知不觉念出声来:“红袖招!”
洛哲惊讶地看了她一眼,“你识得汉字?”
“汉字?”季吉呆了呆,她全然没有意识到这点,待转身再看向那招牌,却与一青衣男子目光撞个正着。男子身着汉地衣衫,样貌清俊,一派风流儒雅,本来正和身边一位娇俏少女言笑晏晏,偶一抬眼与她四目相对,顿时两眼灼灼放光,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洛哲见此情状,急忙拉着季吉走开,低声取笑道:“果然应该戴上面纱,免得路过这里太过招摇。”
“这是什么地方?”
“红袖招啊。”
“我知道,可是……”季吉还是很糊涂,洛哲却不肯深说下去。
“就是美女如云,男人寻欢作乐的地方。”青衣男子不知何时掠上前来,在一旁笑容可掬地解释道。季吉望望招牌,又看看门前浓妆艳抹的女子,终于有些明白。
青衣男子不错眼珠地盯着季吉,微笑道:“你还记得我吗?”
季吉一脸茫然:“你认错人了,我并不认得你。”
青衣男子目光闪动,盯着她沉吟不语,唐突却并无轻薄之色。
“你错认了。”洛哲上前一步挡在季吉跟前,语气温和,神色却极为坚决。季吉心中忽忽未稳犹自迟疑,洛哲早已拉着她离开。
“廖公子!”娇俏少女追上前来,看着洛哲的背影小声道:“你可知道他是谁?”
廖公子摇了摇头,“流香,他是何人?”
流香轻轻一跺脚,“他就是幻化寺的洛哲公子。凉州城里阔瑞王是皇爷,幻化寺的法主班智达便是佛爷,你何苦去招惹他?”
廖公子闻言置之一笑,望着季吉远去的背影自语道:“为什么我一眼就能认出你,而你将我们悉数忘却?”语气中竟是透着深深的失望。
洛哲和季吉来到鸠摩罗什寺,因为后日是金塔寺的开光****,适逢林卡节日,法主索性带领众人先行来到必经之处凉州城,在鸠摩罗什寺居停一夜,亦凑节日之兴。此时恰那、仁增、尼玛、阿尼哥等一众少年人已结伴去过林卡,法主正与腊可纳缓步寺中,驻足在罗什塔下。
法主手触玉石莲花座基感慨:“八百多年,塔犹在,唯舌不坏!”
腊可纳道:“鸠摩罗什大师一生翻译佛教经典七十多部,所译的经律论既不失原意,又保留原有语趣,可惜只译成了汉文。想姚秦时凉州高僧云集,络绎不绝,何等盛况,至今令人向往。”
法主看到洛哲,问他:“你还没有去林卡?”
腊可纳笑道:“劳动公子去接我这位弟子,想来主殿壁画完成,一切准备就绪。”
季吉见法主面目慈祥,自然一种逼人威仪,不免侧立一旁。法主看了她一眼,季吉垂着头,昏暗的光线下未能见其分明,法主一怔,“请问姑娘名字,何方人氏?”
“季吉颇纳,大理人氏。”
“季吉颇纳,你抬首。”季吉依言正视法主,法主目中神光闪动,回身对洛哲道:“明日你和她同往莲花山侍奉索巴阿妮前往金塔寺。”洛哲心中奇怪,此事法主前日已安排他前往,不知为何又特意让季吉同去。
洛哲和季吉告退,季吉问洛哲:“刚才法主说‘塔犹在,唯舌不坏’是什么意思?”
“当年鸠摩罗什大师在这里讲经说法十八年。他是梵汉经文的大译师,就像我们吐蕃的俄·罗登喜饶大译师那样,有弟子三千。鸠摩罗什曾说过,倘若译经没有违背原意的地方,火化时自然‘薪灭形碎,唯舌不坏’。他在长安圆寂后,弟子受其遗命将其舌舍利供奉于鸠摩罗什寺塔中。”洛哲看看季吉,“看来你当真需要学习很多。”
季吉笑道:“我也学了很多你不知道的。”
“是么?说来听听。”
“写汉字,读汉书。”季吉随口一句,说罢自己也愣住了。
洛哲眼睛一亮,“那我们去一个地方,我要考较你一下。”
法主看着洛哲和季吉一路说笑而去的背影,忽道:“你可知道为何恰那已与阔瑞汗王之女莫可都订亲,而洛哲身为长兄却未曾结亲?”
“法主心意,众人皆知。”
法主叹道:“若非远离吐蕃,洛哲现在应该受过比丘戒了。我年事渐高,此事耽搁颇久,不可再拖。明年我想带他回萨噶,倘若势不能回,也定要迎请吐蕃高僧前来为他受戒。”
“我闻得萨噶三祖皆是白衣修得大法……”
“彼时萨噶和现在的萨噶,乃至未来的萨噶事业不可同日而语。彼时萨噶是后藏一寺,现时萨噶号令吐蕃,未来萨噶或可以遍布中土,未来座主任重道远。阴阳双修固属密宗至高无上之大法,可惜历来修成者绝无仅有,或走火入魔,或误入歧途,反而为其所累。”法主停了半晌,“不知洛哲是否心意已定?”腊可纳没有接话,不知缘何法主见到洛哲与季吉一起后生出这番话来,一时颇不自安。
洛哲出了鸠摩罗什寺,不往热闹地方去,径直到了一处所在。只见院墙高耸,墙头杂草摇曳,门头破败,落得一把铁锁锈迹斑斑。洛哲拉着季吉飞身纵上墙头,跃入庭院之中。刹时与墙外繁华隔在了两个世界。
墙内久无人迹,荒草丛中碑石林立,但闻草虫凄鸣。
洛哲郑重道:“这便是旧时唐宋国子监。”
于是季吉看到斜挂于门楣的匾额,她走近一块汉碑,夜色昏黑,不免躬身凑上前去,眼前一亮,却是洛哲点起火折子。季吉凝神细读,一阵恍惚,脑海中蓦然印出总角年纪的自己拿着毛笔写字的稚嫩模样,画面中还有两个年纪略大的男孩子,在书斋中一起吟哦书写。那是何时的自己,依稀汉装?两个男孩子仿佛梦中相知,直到画面中踱入一个青年男子,季吉的心猛地一抽,几乎失声叫起来。
洛哲见她久不出声,笑道:“考倒你了么?”转眼发现季吉目中莹光闪动,不觉讶然,“怎么了?”
季吉勉强笑了笑,“这是唐代诗人岑参的一首诗,《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遂照着碑文缓缓念出:
弯弯月出挂城头,城头月出照凉州。
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琵琶一曲肠堪断,风萧萧兮夜漫漫。
河西幕中多故人,故人别来三五春。
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
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
念着念着,季吉吟哦起来,那抑扬顿挫的腔调自然而然地流淌而出,将她左右。念完,季吉整个人呆在了那里,记忆就在这似曾相识的诗句中涌将出来。这首诗父亲曾经不止一次地吟过,每吟一次便涕泪相和。她问这首诗是何意?父亲说长大了自知。画面里的一个男孩子突然跳出来说,因为凉州——大唐时的疆土为夷族占领。家国之恨,此恨何及!
洛哲在季吉耳边低声笑语:“原来你是汉人!”
季吉如五雷轰顶,她目光迷离地看看洛哲,忽然不知今昔何昔,身在何地。
季吉魂不守舍地呆望着大唐诗碑,她记起来了,她还有父亲、哥哥,可是他们在哪里?为什么八年来她似乎都将他们遗忘?季吉拼命地回想,这才发现生命中多么重要的一部分却成为空白。他们在哪里?“原来你是汉人!”洛哲不经意的这句话重重地敲在季吉的心上,她猛然意识到竟是有近十余年没有读过汉字了,读来既亲切又陌生,早已忘怀的那一段父女之情陡然萦绕胸中。她一时百感交集,泪眼婆娑,不能卒读。
洛哲愕然地唤着她的名字,温柔相问:“我虽不懂汉语,听你读来音韵铿锵,别有情致,写的究竟是何意思?”
“诗写凉州,唐时的凉州城。”季吉抬头望空中初月,“诗中描写的也是一个月夜,月亮挂在城头,月光照在凉州。凉州十万人家,风露一曲琵琶。琵琶曲调哀伤,更见风清露冷,长夜漫漫。多少故人,相别多年。”
洛哲听得入神,见季吉停下,颇感意犹未尽:“就到此处么?似未完结。”
季吉摇了摇头,出神地看着碑文反复念道:“花门楼前见秋草,岂能贫贱相看老。一生大笑能几回,斗酒相逢须醉倒。”念及此情此景,忽觉一阵悲从中来。洛哲但闻语调怅然,不解其意。良久,季吉一字一句释道:“今日同看楼前秋草,何曾能相携到老?一生之中有几回放浪形骸,倘若杯酒相遇,不如不醉无归。”季吉看着洛哲,想今夜与他同游何等快乐,人生际遇,一生****,终不过镜花水月,一场虚度。念及此处,只觉万念俱灰。
洛哲轻轻握住她的手道:“这就是汉人的诗么?果然很美,纵是即时行乐亦太过感伤。走吧,去领略一下现世的凉州,那种狂欢的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