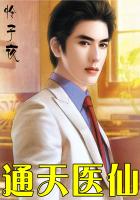只听得那说书人继续皱着一张脸说道:“临川王那是何等人物,那可是皇上寻了十几年才寻回的皇子啊,十几年的凶险生活造就了他的临危不乱。临川王大喝一声,命护卫拿出盾牌置于队伍两侧,阻挡道旁射来的羽箭。但伏兵攻势凶猛,并沿路设有爆竹惊马,才一会儿的功夫,原本有序的车队便已是人荒马乱。”
南清皱眉听着,手不自觉地握紧了茶盏。她听得真切,也想得分明。这哪里是什么临川王的本子,明明说的就是齐王的事儿!他果然出事了!
“队伍乱作一团之时,伏兵已有人欺上前来,他们使的是长枪长勾,武功不弱,专攻人要害。侍卫长和几名侍卫誓死护主,竟也让伏兵占不得半分便宜。且听得林中一阵虎啸,众人心中大惊,但见一斑斓猛虎自山坳处奔至此地,奔得近些,临川王竟瞧见那猛虎上还坐了个人,正义一支短笛驱策大虫。临川王的队伍虽高手众多,但与伏兵打斗已是筋疲力尽,哪里还分的出手去与那大虫缠斗。但见临川王面色一沉,提起手中长剑,直直朝那一虎一人刺去。虽说是人与兽斗,但临川王何等聪明,招招都是要拿驱虎之人的性命。他一边要防备猛虎扑袭,一边又要盘算如何结果那人,一心二用,不出几招已是满头大汗。再看那虎上之人,面色虽平静,却也没料到临川王功夫如此了得,且每每都是狠辣杀招,一时也有些应接不暇。但二人一虎你争我夺,吃亏的毕竟还是临川王,大虫一个扑杀,临川王躲闪不及,便被大虫的爪子给抓了,当时便是血肉模糊,骨头都显露了出来。”
“啊!”南清大叫一声,手中的茶盏应声落地。
其他茶客纷纷朝她看去,之间她眉头冷汗直冒,眼中也尽是氤氲之色,都十分疑惑,不就是听个书,说得再好不也是编的吗,至于如此入戏?
此时,南清心中似是有千万根针在戳着,疼得她险些要倒下。齐王受伤了,还是这么严重的伤,那二哥呢,他好不好,他们如今都在哪儿,可都平安?
庄斯年垂眸看着南清的表情变化,心中也不太好受。一方面,他的任务是去接应齐王,如今齐王性命堪忧,人却找不到,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好处理的事儿,另一方面,南清如此在意齐王,似是任何人任何事都无法将二人分开,即使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他仍有些无法释怀。庄斯年想去拉南清的手,好给她一些安定的力量,但此时的他是否应该这么做?在南清为心上人揪心之际去拉她的手,他的心又有谁来管呢?
说书人撇了一眼南清,有些高深莫测地瘪了瘪嘴,继续说道:“侍卫长见此情景,立刻断了面前阻挡之人的喉咙,便跑去增援,另几名武功极高的护卫也纷纷扑了上去。忽听得那驱虎人笛声一样,节奏明显加快,那大虫的动作也更是迅猛,招招带风,让人近不得身。趁着侍卫们被大虫缠地脱不开身之时,伏兵迅速发射羽箭,当即了断了好些侍卫的性命,连侍卫长如此身手都在背心上挨了几箭,一时间鲜血涌出,脚步也虚浮了起来。”
眼见南清又要摔杯子了,庄斯年忙抓住她的手,将她拉近自己,小声道:“听下去。”
“情势一下便发生了变化,原本势均力敌的两方,就在这驱虎人出现后高下立判,即使临川王再威武,侍卫长再骁勇,也不敌这精心谋划的一场伏击。驱虎人在虎背上轻吹短笛,大虫扑杀更猛,临川王和侍卫长的身上腿上都负伤严重,眼看着就要倒在当场。正当伏兵即将清扫临川王队伍之时,忽从密林深处飘来一阵白烟,似雾浓重,似气弥漫,转眼便遍及了整片修罗场。驱虎人大喝一声不妙,忙屏住呼吸准备吹笛奔逃,却被身后悄然而至的鬼魅身影一掌劈在了颈上,顿时晕了过去,而那只斑斓猛虎也因吸入了白烟而轰然倒地。连大虫都倒了,其他人自不必说,无论是伏兵还是临川王,山道之上已是倒了一片,分不清哪些是活人,哪些是尸首。路边的野草树木都已被鲜血染红,刀剑砍过的痕迹清晰可见,好一个人间炼狱。”
说道此处,说书人猛地就停下了。众人皆是大气都不敢出,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然而,他却捧起茶盏喝了起来,足足将茶客给别晕了几个。
“今日说到此处,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说书人手中折扇一合,啪的一声,惊醒了众人,更是惊醒了南清。
见说书人起身要走,南清忙一个激灵,起身就追了过去。庄斯年也跟在后面,在说书人进入内堂之前截住了他。
“后来如何了?!你快告诉我!他们人在哪里!”南清拉着说书人的袖子焦急地问道。
说书人看了看南清,又看了看庄斯年,神秘地说道:“你们问这么清楚,想要干嘛?”
“他们……”南清张口就要说,却被庄斯年栏了下来。
“他们的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只听先生说了上半部,唯恐听不全下半部,造成此生遗憾。”庄斯年拱手道。
“呵呵呵呵,木已成舟,大人知道故事的下半部又有何用?”说书人笑了起来,他认出跟在庄斯年身后的人便是长平县令,如此看来,庄斯年定是京里来的大人了。
“临川王若是尚在人间,自是苍天有眼,庄某愿为救人之人歌功颂德,若临川王不幸……”庄斯年用余光扫了一眼南清,终是吞了罹难二字,“我们也好前去祭拜,以表哀思。”
“都是故事,你们歌什么功,哀什么思。”说书人哼了一声。
庄斯年微微笑道:“好的故事,总是让人当了真,先生就当我们是些对奇文传说有痴念的红尘俗人吧。”
说书人又盯了庄斯年一会儿,指指他身旁的南清,问道:“这位娘子,也是红尘俗人?”
“她怕是仍痴缠在故事中不肯走出来。”庄斯年状似无意地挑了挑眉,身子却轻轻挡在了南清身前。
说书人徒自站了一会儿,忽然笑出了声:“好一个红尘俗人,二位随我来吧。”说着,他掀起了布帘,便朝后堂走去,“哎,县令大人,老朽便不留您了。”
距离长平千里之遥的永定城内,秦嗣函有些坐不住了。他重新放下手中封看了十几遍的信,重重地舒了口气。
“好!好!好!”他一连说了三个好字,眉眼带笑地看向了角落里站着的一个白衣男子,“孟臣,做得好!这次能杀了唐涣亭,你立了大功!”
沈孟臣恭敬地垂手而立,脸上看不出有什么欣喜的表情:“谢相爷谬赞,孟臣只是恰巧识得西南之地的兽师,给了齐王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礼物罢了,一切的计谋布置,还都得是相爷的深谋远虑。”
“妙哉妙哉!任凭唐涣亭和梅润苍武功了得,却也斗不过一只吃人的畜生。孟臣,这兽师写来的信你现在烧了,莫要给人留下什么把柄。”秦嗣函兴奋地在书房中转圈。
信中说,齐王的队伍已尽数消灭在了长平,他们派去的人手虽然也是死伤大半,但这对秦嗣函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只要唐涣亭死了就行,只要他死了就行!
沈孟臣接过信,从袖中掏出火折子,当即就烧了。
秦嗣函看着越烧越旺的火,心中有一种无法抑制的满足感。
“他的死讯什么时候回到永定?”
“不出一个月,定能在永定听到人们口耳相传。”
“好!”秦嗣函重重地坐回几前,抬眼向窗外的一片阴霾之色望去,“要变天了,要变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