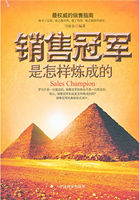我在一座小城市落了脚,那是一片远离故乡热土千里之外的陌生异所,是中国版块上最南面的方位。我离家前和我娘约定了四年的时间,不管四年以后的生活是苦是甜,我一定重返故乡,重回我娘的膝下。
我怀着那万丈的豪情,想在这个小城市里打拼出一片我的天空,于是我又开始不眠不休的去找工作。
我在南方的第一碗饭是在码头当装卸工,后来几经波折我和当装卸工认识的伙伴去了另一座更南方的城市里当建筑工。而后我随波逐流的跟着这个建筑队造访了许多座陌生的城市,那些过眼烟云似的城市让我找不到哪怕一丝的熟悉,可欣慰的却是我和工友们盖出了许多拔地而起的繁华。在许多座对我来说陌生的城市,和对许多座城市来说陌生的我之间,没有什么是值得流连的,而我甘愿这样没日没夜的耗尽两年大好时光不过是为了遵从生活和实现理想。
我变卖了离家前我娘给我新买的手机,我没用过也用不惯,这种稀罕物对于建筑工来说好看却不经用。当我想家时,我会省下一顿饭钱,然后找个电话亭空着肚子对我娘陈述我那腹中满怀的思乡浓情。我也时常会像只井底之蛙一样,蹲在工地上看夜色里只属于我的那片北方星辰,繁星总是眨着眼睛就像我娘在和我遥遥相望一般。
我浑身上下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胸前的一枚玉坠,那是杨小胖为了见证我们友谊留给我的最后礼物,生活虽然困苦,可我就算饿死也不会把它变卖。当年我和小胖曾朝夕相伴,可如今却是天各一方。他去了BJ,在寒冷的冬天时开始了那无止境的北上漂泊。而我则来到了南方,在四季如春的各种时节里出卖青春。
我在这两年里丢过很多东西,鞋,裤子,钱,可我唯一没丢掉的就是信念,我相信生活总会变的更好,哪怕是我现在吃的苦比别人吃的盐还要多上几倍。
由于我的吝啬,工地上的伙伴都叫我铁公鸡,他们下馆子喝啤酒时,我只是独自回到露天搭建的帐篷里啃着馒头蘸着酱豆腐,我不怕吃苦,因为我攒下的钱就像我飞扬的长发一样厚实,我在远离故乡,远离我娘以后,就改变了形象留起了长发,别人都说我很帅,我想帅不帅不重要,重要的是长发会比短发省下好多剪头的钱。
我经常在帐篷里没人时,沾着吐沫一张一张的数那些我攒下的钱,直到把那双干净的手数成脏兮兮后才善罢甘休。我给我娘寄去一部分,然后自己留下另一部分,当我觉得攒下的钱差不多够我去另辟蹊径一个新天地时,我毅然而然的向张工头辞去了建筑工这份职业。老张平日里对我很是关顾,所以走前我买了两盒玉溪塞进了他兜里,工地上的工友就开始起哄,说我是不是发了大财,怎么变得如此阔绰,舍得买玉溪了,他们对我的印象总是停留在我长期吸食的两块五一包软盒哈德门,可他们不知道我在来南方之前的日子里一直抽的就是玉溪。
在工地当建筑工的日子里,我常去一家超市里买白象方便面和哈德门香烟,很多时候我在无事可做时,也会去超市里瞎逛,空着手进在空着手出,什么都不买,就是在人堆里绕来绕去打发时间。由于我性格外向,所以和超市里的售货员们攀谈慎密,一来二去倒有了几分交情,那时超市里一个卖香烟的本地人很喜欢和我闲聊,他叫王小楼,很奇怪的名字,他说他妈生他时由于早产,他被迫降生在一个小弄堂里,所以起名字也因地制宜了起来,叫小楼。
小楼说他在超市里干了很多年,他爸也托了几层关系终于把小楼调入超市的管理层,这事情就发生在我辞去建筑工的一个月前。
当我辞去工作后,我给小楼打了电话,我告诉他有个致富的好项目,问他愿不愿意和我试试。
当初我在逛超市时,总会看到许许多多的人在超市里绕的团团转去采购各种各类的蔬菜,他们的初衷不过是为了能做出一盘或几盘丰盛的菜肴,可这种绕来绕去买菜的方式既浪费时间,又消耗精力,我就想着有没有个办法能解决这种‘前顾之忧’呢?
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方法可以既解决他们买菜费时费力的难题,又可以改良超市里的卫生和环境。我想只要把各种菜肴所需的配菜,配肉,调料,按比例放倒一个真空袋里,然后像卖模型一样的将这几样一并卖出,顾客买走后,只需按照真空袋外面所介绍的方法去做菜,那就又好吃,又省力,又节约了时间。既然一石能三鸟,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小楼后,他叼着香烟拍手称快,他说现在正好还管理超市的物流工作,又说这简直是天时地利人和,万事俱备连东风都刮上了。
我和小楼一面着手注册公司,一面研究着怎么配菜。资金是小楼和我一人一半出的,他在他老子那里要了不少钱,而我都是自己攒下的血汗钱,他出的钱多,我的钱稍少,但平日里并不用小楼费心,所有事情都是我和四个员工来做,他只需坐享其成就行。小楼和我都是那种情义千斤的人,我想朋友之间只要相互信任关系就会变得融洽,所以在利益面前我和他从来没有过任何的争执。
其实机遇就像艳遇,不是常有,但只要出现你就不能放过。我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很珍惜机遇,因为我吃过太多苦头,我卧薪尝胆的等了这么多年,为的就是像猎人逮兔子一样狠狠的抓住机遇,绝不给它稍纵即逝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