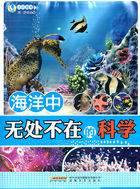叶一平忙着点炉子,杨玉叶去里屋换上了干净的床单、被罩,把叶扬放在床上,出来帮叶一平洗菜、做饭。两人谁也不说话,偶尔对视一下,叶一平有些无奈。
午饭后,叶母去床上睡了,杨玉叶与叶一平回了里屋。下午还要上班,叶一平看了一会叶扬,躺着闭目养神,杨玉叶有些累,不一会竟睡着了。
一觉醒来,叶一平不见了踪影,杨玉叶走出里屋,外屋没有人影,探头瞧了一眼叶母的床,叶母不在。杨玉叶开始收拾屋子。
杨玉叶把沙发罩放到盆里,把角角落落的灰尘打扫干净。
叶母的床上,被子散落着,床单胡乱地铺在床上。她看着难受,叠好被子,铺平床单,她发现床头的里侧鼓着一个包,掀起褥子,是一团裤头和袜子,杨玉叶低头闻闻,倒是没有味,像是洗过的。杨玉叶把裤头叠好,平整的放在下边,把袜子放在稍远的地方。
杨玉叶端着盆去院里的压水井洗衣服。隐约听见叶母在房东秦大娘的屋里说话。
王凤枫悄悄走过来,弯腰伏在杨玉叶的身边,眼神瞄了一眼秦大娘的房门,低声说:“你婆婆在臭你呢”。杨玉叶抬起头,有些摸不着头脑。王凤枫用下巴指指秦大娘的屋门,用手捂着嘴,凑在杨玉叶的耳边,声音杨玉叶刚刚听见,嘴里的热浪却扑的杨玉叶的耳朵直痒痒。
“她说你家不懂规矩,不住满对月就回来了;说你厉害,挑拨儿子不和她亲;说你不知道省钱,儿子不让你买表,你非要买;说你故意给孩子垫很多尿布,好让她洗,不说了,有空再聊。”
王凤枫转头走了,走的是轻轻的猫步。
杨玉叶想起了表,叶母来了不久,总是到里屋问杨玉叶几点了,因为杨玉叶有手表。杨玉叶与叶一平商量:“买一块挂表吧,你娘看表容易,不然她总是问我”。叶一平不太愿意,那时一块挂表并不便宜,叶一平说:“问你,你就看看手表告诉她不就行了,省的再花钱”。杨玉叶坚持,表还是买了。
叶一平把挂表拿回家时,叶母问:“买这干啥?怪贵的”。叶一平回应:“玉叶要买,说你看时间不方便”。
“这些叫事吗?值得去和外人说”,杨玉叶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感觉。
王凤枫在县城的大楼当售货员,是两班倒的那种,杨玉叶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上什么班,倒是她觉得,只要时机合适,她就会出现在杨玉叶的面前,悄悄地通报着叶母说过的话。
“她说,你给娘家拿花生要拿一大袋子”。
“她说,你给她外甥闺女买了衣服心疼,她会叫她闺女给你闺女买,还给你”。
“她说,你家远,不知道你是什么东西,她小儿媳是当庄的,知根知底”。
杨玉叶头都大了。
“从林场带回的瘪花生不是也给她女儿送了一大袋吗?
给外甥闺女买衣服,我没说过什么呀?
家远倒是真的,她儿子要找个什么样的东西她才中意呢?还好,还有个知根知底的小儿媳,不至于两个都不是东西”。
叶一安毕业后,有了几个说媒的,都是看上了叶一安的学历和职业,并不计较他的家庭。叶一安看后,都不中意。叶一安的同学给他介绍了一个,也是他的初中同学,女孩是本村的,没升上学,人长得漂亮,叶一安动了心。叶一安告诉了叶一平,叶一平坚决反对,拉上杨玉叶做他的工作,劝他不要找农村的,单位不给单职工分房子,以后要自己盖,媳妇又没工资,生活负担重。叶一安坚持了一段时间,见哥哥还是反对,就断了。
邻居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家在村子北头,是她的远房表妹,是顶替父亲的工人,单位距离叶一安教书的学校不远。叶一平觉得条件合适,催叶一安见面,叶一安回来后,一脸的不高兴,说:“长得不好看”。
叶一平问:“长得还很丑吗?”
“也不是,不如同学说的那个漂亮”叶一安笑笑。
叶一平心里有了底,劝他:“人家不嫌弃咱就不错了,你就将就着吧,哪有十全十美的”。
叶一安还真是听话,这门亲事竟定了下来。
王凤枫看杨玉叶憋红了脸,连连说:“别生气啊,知道你会生这么大的气,不告诉你了,不过,你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冤啊?”
“走啦”,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压着声音说:“千万不要说是我告诉你的”。
从此,杨玉叶的心就像遇到了南方的梅雨,久久地见不到太阳,她的脸上长时间地挂着阴郁的天气。她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
叶一平问明原因,并不责怪他的娘,倒是觉得杨玉叶多事。
他斥责杨玉叶:“那些娘们的话你也信,和她们搅在一起,你就不怕降了你的身份?”
杨玉叶还是疏远了叶母,她一眼都不去瞧她,叶母意识到了杨玉叶心里有事,她悄悄地观察杨玉叶,知道杨玉叶与王凤枫交流的多了,她变得小心起来。
叶一平照旧上他的班,杨玉叶照旧做着自己的事,叶母在叶一平在时,就在屋里若无其事的和叶一平说笑,叶一平不在时,她一会都不在屋,在院子里各个屋串门。
真是不同年龄说不同的话,渐渐的,院里的媳妇凑在了杨玉叶的身边,叶母只好和秦大娘拉呱,秦大娘的媳妇桂枝在谁面前也不搭腔,帮秦兴喂完猪,在院里帮着秦大娘干家务,王凤枫说:“桂枝怕秦大娘”。
一日,杨玉叶吃完晚饭,回屋照顾叶扬去了,叶一平母子边吃边拉。不久传出嘤嘤的哭声,杨玉叶伸头一看,是叶母在哭,叶一平低着头不语。
杨玉叶走出去,问叶一平:“怎么了?”
叶一平说:“明天是我爹的忌日,娘想去上坟。”
“去吧,反正孩子我自己能带,回家待一段时间也好。”杨玉叶觉得与叶母分开一段时间也好,她可以淡化一下情绪。
叶母听完,忽地站起身,大声说:“我儿还没撵我走,你算什么?你就那样不待见我。”
杨玉叶忙说:“我没有别的意思,你不是想家吗?要不你干吗哭?”
叶母提高了声音:“我想什么家,我想人,人在哪我在哪,你愿意吗?”
叶母伏在沙发上嚎啕大哭,秦大娘进来了,盯着杨玉叶问:“怎么了?你婆婆这辈子不容易,没了那个人,一个人拉巴着两个孩子,现在有盼头了,别再惹她生气了。”
杨玉叶忙说:“大娘,不是这样。”杨玉叶还没解释,叶一平站起来推搡着杨玉叶:“滚,别在这里丢人现眼。”
杨玉叶看着叶一平通红的眼睛,“滚、滚、滚.....”刺耳的声音在杨玉叶的耳边回荡,杨玉叶泪水横流,两眼一黑,竟扑倒在地。
杨玉叶哭了一宿。
第二天,叶一平请假陪她的娘回家上坟了。
叶一平的父亲去世后,叶一平上班,叶一安上学,如果不是在假期,都是叶一蓝去上坟,有时叶母跟着。
很晚,叶一平回来了,叶母没有来,叶一平说:“姐姐留她在家住几天。”
叶一平与杨玉叶都很郁闷,各自想着心事。迎来他们的宝宝,本该是很幸福的事,而随之而来的却是这么不开心,谁错了?
那年冬天,双泉组建各个单位的联合工作组驻村,搞冬季技术培训,叶一平是林业局的参加人员之一。叶一平告诉杨玉叶:“驻村要一周回来一次,你自己能行吗?”
杨玉叶沉默了一会,心想:叶一平不在,她与叶母怎么相处?叶母一定会再产生很多说辞,到处控告她。不如不来的好。
杨玉叶对叶一平说:“我脾气不好,你不在,我会惹你娘生气的,还是我自己吧。”
叶一平明白杨玉叶的意思,没有强求。脸上自然没有好脸色,他像许多婆媳不和的家庭的男人一样成了夹在中间难受的角色。
杨玉叶心疼,却没有办法,她安慰自己:即便是**转世,变成了女人,成了叶母的儿媳,也许结果也好不到哪里去。叶母没有底线。这样想时,她不觉得欠叶一平的。
年关近了,叶一平说:“玉叶,孩子小咱们不回家过年了,叫娘和一安来这里过吧?”杨玉叶想想也是,和孩子回家不方便,叶一平是不会让叶一安和他的娘独自在家过年的,那样,叶一平会像犯了罪一样不可饶恕自己。
学校放假早,叶一安与母亲早早的来了,杨玉叶与叶一平准备着过年的东西。看孩子成了叶一安的活,他倒是很喜欢这个侄女,坐在她旁边逗着她玩。
秦大娘要去洗澡,约着叶母,叶母说去,准备着洗澡的东西。桂枝凑在秦大娘的旁边说:“帮你去搓背。”
秦大娘嗔怒着:“你别跟着,跟你光溜溜的在一起多不好意思。”说归说,高兴已挂在脸上。
桂枝挽着秦大娘的胳膊说“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娘俩还怕看?你儿子要我去,说你年龄大了,怕你在里边摔着。”
叶母静静地听着婆媳的对话,眼里流露着羡慕,她抬眼看看叶一平,叶一平一定也听到了那些话,他对杨玉叶说:“你也去吧,也帮娘搓搓背。”
杨玉叶没吱声。
婆媳之间与男女恋爱有相同之处,没有感情时,谁会有亲近的渴望?如果不接受了,男女是要分手的。婆媳没法分手,只好敬而远之或相互尊敬,强迫亲近能有好结果吗?
叶一平不去想这些道理,他要他的母亲享受她想享受的,他自己做到,他要求杨玉叶也要像他一样去做。
杨玉叶没给叶一平面子,叶一平迁怒杨玉叶的情绪愈演愈烈,他常常训斥她,杨玉叶在叶一安面前保持沉默,冷寂的表情早已传递给叶一安。
冷冷静静的春节过后,叶一安拽着他的母亲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