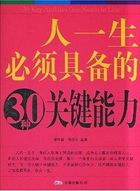骆祥森这次是扎足了面子,‘小爷,小爷’的称呼,使他爽了一把,十分过瘾。小辈们的‘大爷爷,大爷爷,’使他来个大出血,在三活鬼和阿二黄胖的下辈手里都出了见面礼,晚上回到主人家,身边随身带来的3000多元私房钱去了一半,当晚又拿来出一千元是赞助印刷家谱费。留下的只够回家的路费了。在这骨节眼上,明天得走人,不走不行。骆家兴乘机说:“是啊,今天村长没有露面,你不走,说不定明天村长出现又来个邀请宴,你口袋见底,在席上你的酒还喝得下去吗?老爸是不得不走人,不是骆家兴支开他的,父子俩商量,要问他一起走不?骆家兴是支支语语,抬头向主人求救,示意他出面要他留下,因为他要办的事此今为止一件也没有办妥过。主人家骆金定领会他的意思,就出面说:“阿侄有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现在年轻中有这样好的毛笔字是稀有的,刚好誊写家谱用得上,如果阿侄学习不受影响的话再在村里帮几天,你如果有事你要先走一步也可。”
“小赤佬,一天生,二天熟,这么快与你金定叔混熟了啊,莫不是那三叔小孙女粘住了你,哈,哈。如果这样也算你有本事,不过不可打打棚来着。”骆祥森心直口快说穿了他。
“黑七搭八。我誊写家谱,那以后是做底本的,是会世世代代传下去的,我的字迹永久保存在家谱里,那不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吗?”骆家兴寻找理由说。
“好了,好了,不跟你多说了,明天起一个早,你把我送送到车站。我一个人先回去,到家你娘问起你,我会说你在原藉被招附马了。”骆祥森说完后,醉醺醺哼着小调倒床就睡。
第二天是起了大早,但去原来的下车的地方半路等车不是办法,能乘得上乘不上是一个问号,上得了车有没有坐位也没把握。在主人骆金定的陪同下首先与三公公作别,主人又叫来那个车主开趟到县城始发车站,这次是不好意思坐白车了,付了三十元的车钱,骆家兴帮父亲买了车票,找到候车室,为不影响车主的时间,未等父亲上车,骆家兴与车主一道先回村里。临别时父亲还把余下的钱给了骆家兴。骆家兴问清父亲尚留有县城返家的那一车费后才安心收钱。
骆家兴送走了父亲后感到一阵轻松,要办的事可‘从长计议。’三人小组继续从事家谱工作,有条不紊进行着。由于多了一双人手,进度加快了不少,骆家兴的就餐问题是继续在主人家‘搭伙’,胡老师也是正好是假期,做后勤备菜备饭,中午前是让骆梅芳早一步回家的,让她去做中饭,乘假期里孝敬一下爷爷,所以在骆家兴与骆金定二人时,他也不失时机间从骆金定口中得知三公公以上生活的轨迹,他爷爷临走时他家全部佃田都归三公公管理,说是管理,他是全善不管的,佃农,佃户要交的租粮不管你交不交,能应付皇粮上交后就行,他一个人要吃的粮食随便到那家取一点就行,所以骆家兴家的田地其实变成无主之田,家家户户后悔事先没向骆家兴爷爷家多租些田。三公公变成了不成文的族长村长。在村里威信甚高,到了土改时,这村变成无地主之村,最高成份富农也没有。土改事实上变成了把各家所租的土地再集中均匀一下而已,都说骆家兴的爷爷有先见之明,在土改前几年就跑得无影无踪。各家都分到了田,还要找骆家兴爷爷干吗?正因为这些田,变成了负担,骆家兴的爷爷是不敢回老家的,而按时间算,骆家兴爷爷是在取消阶级成份后就马上有心想回老家了。可惜是差了一步。
通过前因对照不难知道骆家兴爷爷自己和把父亲改名的用意了,隐姓埋名几十年。
土改后三公公一直是行医为生,几年后成了远近闻名的土医郎中,主要擅长急救毒蛇蛟伤者,刮痧,挑小孩犯贱,治疮毒。在五、六十年代,那时农村卫生条件差,与他擅长的病人较多,困难的人家来治没给钱,他也治,有给钱他也收。特别是被毒蛇咬伤者,经过他的及时救治,是拣了一条命回来,救命一条,胜造七级屠浮,三公公是不知胜造了多少级屠浮了。
三公公可谓是学识渊深而莫测,志趣高邈而难知;宗尚老子,无争的处世原则,挫脱解纷,和光同尘,不涉功名利禄。行动是独来独往,时而是闲云野鹤,对酒当歌。时而愤世嫉俗,挥毫捷书。鳏寡孤独,孑然一身。却出现众人意想不到的一幕,有一天三公公傍晚游医回来,右手抱着一个婴儿,左手摇着手摇鼓逗小孩玩,小孩生得瘦小,一付菜色面孔,衣着褴衫,很明显小孩是营养不良,出自贫寒之家,回家后找人做了全新的衣服给小孩穿,又经过三公公的精心调养,脸转为红润,小孩面貌为之一新,从小女孩咿咿呀呀学话开始,教她叫爷爷,那个小孩就是现在的骆梅芳,她从小就聪明过人。又生得十分可爱,三公公一直没有亏待她的,吃穿不比有爹娘孩子差,至于梅芳是从哪里领来的,三公公一直是秘而不宣,问急了就说是在街上走散的小孩,他在原地等到天暗才把她带回家的,估计是对方爹娘有意丢弃的,看她可怜就带来了。
那时大食堂刚散,人们对饥饿的恐惧还心有余悸,弄不明白三公公这把年纪却去领培养一个小孩,而在村中从前从未泄露此意,有多子女的家庭后悔没有探得三公公有此意,在三公公面前不时地说:“三公公啊,您有此意何不早说,我们家的男的女的让你挑,过继给你,又是同姓,那比你在外拾一个是好多了,你知小孩的来路吗?好还就还掉算了,在我家挑一个。”
三公公总是淡淡一笑,那是一种缘分,可遇而不可求。
但在特殊时期浩劫中三公公还是吃了一些苦头,因为在村里没有地主、富农成份的人,实在揪不出人好批斗,就抓他充数,说他做过地主的代理人,在解放前与大地主,反动派结过帮,是潜伏村里的阶级敌人,与外逃的地主分子,反动派分子有无联系,是不是暗中勾结,等待变天。结果是关也关过,打也打过。最终是一无所获。骆家兴知道三公公如此遭遇,实则是代他家受罪的。
三公公昔日行得春风便有夏雨。曾在命悬一丝,被三公公救治过却根红苗正的人,壮着牛胆为三公公发话鸣不平,这样的事一有人带队,其余呼应纷纷群起随之。却不说三公公治病救人,就是在骆家兴的爷爷外逃后至土改那阶段时期里,没有代收过半粒米谷的佃租,其立场不言自明,于是一场滑稽剧就粉墨登场,三公公不仅不是阶级敌人,而在解放前已为广大贫下中农谋利益,抬杠的抬杠,硬被拉入至村(当时称之大队)革委会成员,成为副主任一职,三公公是荣辱不惊,淡然笑之,你说没用,今天看来其作用可大了,在紧接着是雷厉风行的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运动的梳篦中,三公公成了‘四旧’签定专家,将宗谱列入四旧之外,使历年宗谱幸免火中焚毁殆尽,被视作小资情调浪费占用土地梅林岗上的梅树也作个折衷处理。不然的话,今日续修家谱是无从谈起。
七十年代村里成立合作医疗,三公公成了村里的赤脚医生,但他是排斥西医的,他也作游医,出门捕蛇,估计收入自食其力有余,那是在过去,近年分田到户后,年事已高,小孙女长大,开支增大,估计是入不敷出,旁人也为他经济发愁,而他是处险不惊似的,是个很深奥的老人。
到了吃午饭正要收摊时,一个洪钟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交谈:“金定哥,大客人在哪个家里聊天呀?”一个大踏流星的人闯了进来,骆家兴抬一看是村长。
“村长好。”骆家兴礼节性地叫呼了一声。
“你说是他爸是吗?他先回了。刚上午回的。”骆金定回答说。
“怎么?。。。那怪我疏忽,要命啊,刚好挤着上镇里开一天会,我还没有好好请请他呢。”村长说着一边很焦急地搔着头皮,骆家兴暗暗庆幸自己高明之见,不然又要破费了,老爸刮干净不算,也要挖进自己的口袋。
然后他朝金定说:“那天我只露一下面,急,你有看到老人带有一枝手杖来吗?”骆家兴为之一怔,下意识地抬起头来看看村长,相视下,村长感到自己说漏了嘴,马上改口:“一个老人先回,路上我们有点不放心。”
“手杖,哪来的手杖。我爸从没使用过手杖呢,还没有到要使用的年纪。”
“那你家里有一枝手杖吗?”被骆家兴点破后,村长也急着直说了。
骆家兴这时完全明白了对方用意,好像知道他家的底线有手杖,这反而引起了骆家兴的高度警惕,马上不露声色而淡淡地说:“爸还用不上,哪来的手杖,他啥时要用,我到自己的厂里马上可为他制作一枝的,杆子用车床车出来,又圆又滑又直稍带退拔,头里镶铜帽,保他满意。”骆家兴故意南辕北辙越说越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