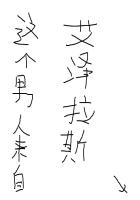有吃的在眼前,白大少一时被遗忘了。一不被关注,人就正常起来了。眼睛会转了,左右看看,无人理他,他饿了,忽地出声:“我要喝水!”把那三人吓了一跳。当然不包括萧齐,他悄没声地把碗水放到白大少面前,拉把椅子坐到对面。白大少忽地矮了一截儿,没声气地叫了声“萧爷”,萧齐略回礼,“白大少”。
方白止了嘴,不明白这两人怎么就见过了。看不出他们这是哪出,不过方白顶气不过谁人在萧齐面前都显矮一头,拿过一只鸡腿戳到白大少嘴前,“吃!”。白大少感激地看了眼方白,接了吃着,却不知道那一眼看得方白浑身不舒畅,谁人刚被她打还用那种眼神看她,就真是个天生的窝囊种子。
不点客栈的一顿饭又吃过了。桌上狼藉清掉,小儿勤快地泡了茶上来。白大少尝了口,茶涩得紧,只是水热得刚好,尚能入口。一抬眼,看见几位眼睛唰唰地盯着他,看样子是要开堂似的。
萧齐先开口,“白大少,今后如何打算?”白大少垂了头,不言语。
萧齐又道:“虽然这次白剑门做得绝路,但实意在于逼你回去,如果你想回去,在下可代为向你父亲说项。”
白大少作犹豫状。
方白在一旁气得心里发痒。她为人最恨自己搞不懂状况时,别人特别明白,讲些没头没脑的对白,在她面前摆做派。这一点做得顶顶恶劣的人就数萧齐,大家都是混江湖,为什么着调的总是他,不着调的总是方白呢?
她气上来又要拍桌子,手腕一挥恰被等在她那里的萧齐格住。
萧齐很为方白操心,客栈做生意的家伙是桌子,像她那么爱拍桌子,不说气力如何,家伙总要受些损害的。方白愣了一愣,手腕一翻,赌口气非要拍上桌子不可。萧齐再挡。一来一往,止不住两个人在桌面上动起手来。
方白这是第一次和萧齐动手。一般说来,方白不爱跟人动手,因为那一边别人家饶有兴致,这一边自己家气得心啊肺啊翻了个个,不用别人教她比武场上气势定输赢,她也知道比不过,那还打什么打,陪人玩?何苦逗人开心!忽地住了手。究竟是不甘心,另一只手翻上来,她知道萧齐是护定了桌子,因此一巴掌扇在旁边人脸上,“啪”清脆地一响,总算泻了口气。只见白大少白惨惨的一半脸上又慢慢晕红起来。
白大少哀婉地看着方白。这一巴掌若是别人打的,他早就跳起来呼天抢地了,凭什么都来跟他作对!可这是方白打的。他,他只想要个说法。
可惜这真是无妄之灾,平日若是老夭坐在那里,挨这一下子的就是他了。这眼神又看得方白浑身不得劲了,多少有些不忍。她喜欢欺负人,可不喜欢欺负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的人。似乎她怎地也得为自己的无理找个说辞。
“回去干吗?回去个屁啊!”
这话忽地从她嘴里蹦出来。她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不过听上去与那个耳光还满搭调,有点棒喝的效果,再说只要能和萧齐唱反调就好,他劝回去,她就偏要劝不回去。
这时再看老夭和小二搞不懂状况地看着她,方白获得了极大的满足。不懂装懂,还不会吗?
如果从头说起白大少这一天来的经历,刚开始时白大少以为自己在经历着人生最有价值的一天,他仿佛终于有找着自己的感觉了;在这一天结束时,白大少发现自己丧失了所有价值,连自己是谁都掂不清了。
起因很简单。白剑门掌门,也就是白大少的老爹,要给白大少说一门亲事。虽然称为“说”,有商量的意思,其实是定下来的,只是通知他一下,说给他听。不想这激起了白大少强烈地反弹。这也难怪。白大少青春妙龄,生活优裕,正值怀春的旺盛期。你让他做什么,他可能都逆来顺受了,偏偏关乎个“情”字。情字之伟大,在于有蛊惑人心的本事,就是再软弱的人在这事上也能被激发起叛逆之心。白大少当即反了,指天起誓,不退这门亲他就离家出走。偏天时地利人和要如了他的心愿。即时他母亲在场,左右是一副说家事的情状,父亲平日里威严的气势未百分百在白大少身上发生作用,而母亲在一旁苦苦哀求,更激起了他男子汉自我的觉醒。更何况眼看着母亲在父亲面前一向低头伏小的样子,更强化了白大少对父亲的怨恨,作为一个男人怎样也要像父亲一样,在妻子面前很有权威感。可凭什么给他说江湖上武功第一的女人,在那么强悍的女人面前,男人的权威从何谈起!当然那时白大少没想起方白来,那也是个强悍的女人,但这也不一样,自由选择的意义不就在于此吗?关键是,人,总是很矛盾的。
也许白大少曾潜意识里以为有母亲在场调和,父亲总会软下来的,可父亲却一点回头的表示都没有,为了把这场剧推向高潮做个了断,白大少只能甩手走出大门,做义无返顾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