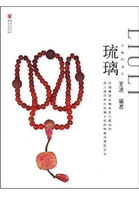白淘兔撞到溪宇的腿上,后脑勺倒地,“哎呦哎呦”的叫疼。肖冥止步,睁大眼睛吓了一跳。
溪宇揪住白淘兔的长耳朵,掂起来问:“哪来的小东西,说,这是什么地方?”白淘兔哪里能说话,眯着眼睛只顾喊叫让她放手。丑生不认识白淘兔却认出了肖冥,丑生蹲在肖冥面前,一脸惊喜的说:“是你呀,还记得我吗?”
肖冥想了起来,又害羞又害怕的点点头,嗫喏说:“你是救世英雄侠。”
“救世英雄侠?”溪宇扔掉白淘兔,转过身问丑生,“你们认识?”
丑生说:“见过面。”然后又问肖冥,“你怎么跑这里来了,你爹爹呢?”
肖冥向石子路方向指指,那个方向被桃红色太阳照得绚丽多彩,视线有些模糊,但可以察觉出特别的美丽。溪宇拉住丑生顺着石子路向前走。
慢慢的,眼前现出一座阁楼,奇花缠着蔓延的藤条布满阁楼,各种鸟儿不时的在檐边逗留,那氛围让人心情舒畅,温馨安谧。
溪宇再仔细看,见楼前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个人双脚绑着绳子被倒挂在一根长梁下,那个人竟然是自己的七舅舅,厝七涂。溪宇不禁大喊:“七舅舅?”
厝七涂和在一旁的人看是谁在喊。厝七涂倒着头一眼没认出来,但听清了溪宇的声音,兴奋的大声说:“溪宇,我的好外甥女儿,啊,你太聪明了,连这里你也能进来,好哇。”
溪宇跑向厝七涂,丑生自然也得跑,但他有种要飞的感觉,两条腿仿佛不是自己的了。溪宇抽出短刀,抬手将短刀抛向梁上的绳索,不想刀飞一半,被一根拐杖半空拦截下来。手持拐杖的人是个佝偻老婆子,她就是在解颐酒楼前给肖平郎和肖冥下迷药的人。
老婆子挡住溪宇去路,溪宇猛然停下,只听“噗咚”一声,原是丑生没及时止住脚步,一头栽在地上,满脸尘土。溪宇厉声问她:“你是谁?活的是不是不耐烦了?”
老婆子哈哈大笑,“哎呦,七七小主,不认识我了?”
“你是……”溪宇眼光一亮,“呀,你是姥姥!”
溪宇印象中的姥姥虽年迈,但身体健好,哪用得着拐杖。溪宇抱抱姥姥说:“姥姥,你又易容又变声腔的,我差点没认出你。”
“恩,可我再变也还是被你这个冰雪聪明的小丫头两眼认出来了。”老婆子刮刮溪宇的鼻子。溪宇问:“姥姥,快说,这是什么地方?你和舅舅怎么跑这里了,舅舅不是在一个神奇的地方吗?”溪宇说时眼睛向楼前的人瞄了瞄。这些人中就有那个被追天涯绑住的大汉,他和两个也是身材魁梧的家伙守在一个女子旁边,这个女子长着一张娃娃般的脸,头发很乌亮,光着两个细致的小脚丫,她是锦弦。她身后站着面容憔悴,双眉紧锁的沧桑男人,肖平郎。
老婆子没回答溪宇的问题,而是盯着丑生看,这时丑生正从地上慢慢的爬起来,气喘吁吁的拍身上的灰土。老婆子抓住溪宇的手,诧异地问:“好外孙女儿,这个……这个丑八怪是何人?你怎么和他手绑手?”
溪宇犹豫了片刻,鼓起勇气,低声说:“他是……他是我要托付终身的人,叫阿九。”
老婆子和吊在梁下的厝七涂顿时傻了眼,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老婆子问:“好外孙女儿,你,你说什么?”
溪宇说:“我,要嫁他。”
厝七涂在梁下翻腾起来,嚷道:“我的溪宇啊,你的眼睛是不是出问题了呀,这个人丑陋无比,一点本事也没有,你怎么会,怎么会……”
老婆子故作镇定,笑了笑说:“溪宇呀,这个玩笑可开不起呀。”
溪宇一本正经的说:“我溪宇从来说一不二,我说真的。”
老婆子从新打量丑生,他除了面貌丑陋,毫无半点风度,哪里配得上宛如天仙的溪宇。老婆子发指,咬着牙说:“我不能让这丑小子把木族和十六族的脸给丢尽了,溪宇,大不了你不嫁人了,天下少了男人,我不信不能过了。”说着举起拐杖抡向丑生的脑袋。
溪宇急忙拉链子,使丑生躲开一劫。她召回短刀,口中念了些什么,一晃眼,短刀变成了把长刀。
“怎么,你要跟姥姥动手?”老婆子瞪着眼。
溪宇摇摇头,说:“我不让你杀他。”
“溪宇,今天我为了你的将来,只有下狠手了,别怪我伤你。”
老婆子抡拐杖恶狠狠的甩向溪宇,溪宇毫不畏惧,迎难而上。挥刀和姥姥打起来。由于她左手有丑生这个累赘,招式施展不开,所以她拼打的十分费力。
溪宇和老婆子过招东跨西撤,丑生则跟着溪宇东倒西摔。厝七涂在梁下,无力的喊:“别打了,别打了。妈,你由她去吧!”
老婆子边打边说:“你给我闭嘴,算完了溪宇的帐,我再算你的帐。”
厝七涂长长一声叹,看向远处嬉笑奔跑的白淘兔。又回想起了这些天发生的事。
那天,溪宇把厝七涂带入平和街,厝七涂以赖着不走终日弹琴为借口要挟介子引借出宝盒。介子引表面不予理会,回家后就在心中盘算着什么长远的计划。而平和街的街民却对厝七涂恨之入骨,他们为此感到恐惧,感到他的出现会打乱他们的生活,会把美好的未来打破。于是街民们私下里会谈决定,让有威望的变戏法武师傅与介子引商榷,劝说一起赶走厝七涂。但介子引没同意他们的观点。
武师傅把所谈结果告诉大家,一些人不能理解,失望愤怒。有人提议:“既然介爷爷不愿出手,那我们自己动手。那魔人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我们百来人难道对付不了他?”
“没那么简单,”有人质疑,“我们毕竟是不懂什么仙魔之术,必须智取,不能硬来。”
大家沉默。一会儿,又有人点出话题:“你们猜这几天晚上,我都见什么了。”
“什么呀,别卖关子了,都什么时候了。”
“就是晚上弹琴的人不是魔人一个,还有个与他一起乱唱的白淘兔。”
“那又怎样,小孩子都让我们没脾气。”
“是啊,难听要命。”
“不是,”点出话题的人说,“我想说,他们弹的都难听,但他们弹的却很投机。”
“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利用白淘兔?”
“对!”
于是街民们开始策划,决定在开井打水那天动手。
平和街按着平时,每隔十天开一次井盖。等夜幕降下来的时候,介子引去关井盖,但武师傅耍戏法偷梁换柱,介子引关的是假井盖。因为大家在一起生活了几千年,没发生过欺骗的事,所以介子引并没有起疑心,盖完井便回家,这时武师傅派人去介子引家,让那人想尽一切办法不让介子引出来。
夜慢慢变深,平和街的灯火照亮整个颭婴亭的山坡。
白淘兔如往常抱着破琴又上了厝七涂的屋顶,两个人相视而笑。厝七涂把琴摊腿上,大发感慨的说:“小淘兔啊,咱们两次合奏合唱,使我大来灵感,后来编上了几段曲子,虽听着十分舒心,但觉得欠缺些什么。”白淘兔也将琴摊腿上,说:“叔叔,不妨弹弹,我听一下。”
厝七涂抚琴,又弹出了令人难以接受的琴声。而白淘兔两个耳朵竖的直直的,听完后赞叹不已,说:“我眼前出现了星星,我觉得少了月亮。”
“月亮?”厝七涂有所领悟,“对,就是月亮,就是月亮。”
这时,白淘兔的母亲来了屋前。白淘兔知道是来叫自己回家的,不舍得和厝七涂说再见。下了房跑向母亲的怀抱。厝七涂和白淘兔一房上一房下再次相视而笑,很默契的眨眼睛。
当白淘兔母亲走到路口准备转弯的时候,武师傅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不容她说什么,武师傅一把将白淘兔从她怀里夺走,将白淘兔装进一个大袋子里,边跑边喊:“这个小子与魔人在一起,一定将来也是平和街的祸患,早杀走除祸害。”白淘兔母亲嚎啕大哭,跌爬在地上哭喊:“我的孩子还小不懂事,放了他吧。”
在屋顶的厝七涂见有人要杀白淘兔,急红了眼,骂出口:“他娘的,胆大包天,看你往哪里跑!”纵身一跳,跳到武师傅前面拦住,举起手里的兵器,劈向武师傅的头顶,但武师傅又耍戏法,厝七涂打中的是假人。
武师傅出现在平和街街口,抱着个大布袋,布袋里传出白淘兔的嚷叫声。厝七涂追过去,他追的很小心,边追边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距离街口不到五十米的时候,他突然停下,握紧利器,插进脚底的地底下,紧接着地下传出闷闷的极惨的一哀叫,厝七涂将利器一挑,从地下挑出个人,正是武师傅。武师傅趴到地上,胸口不断的往外涌血,四肢抽搐。现在再去看街口,那只站了个草纸编的假人。
位于厝七涂两侧的屋顶站出一大群街民,他们手里都捧着盆子,盆子里装着能着火的蓝色液体。一人高呼:“烧死他!”街民一起倾盆泼向厝七涂。
现在即使有神速之人,也来不及躲开这液体了,厝七涂脱掉上衣,举过头顶旋转当伞,把飞来的液体挡散到四面八方,一时间,少半个平和街着起了火。
厝七涂以衣当伞使液体没能近身,只烧毁了上衣而已。但不少街民却被散开的液体溅到,全身起火,惨叫打滚。街民们拿起锄、铲、锹,还有许多做活工具,蜂拥冲向厝七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