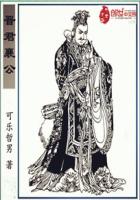(七)
沿途之上,路断人稀。岳家居住的村庄也景象凄凉。那岳府的雕花门楼已显破败,两扇大门紧闭,叽叽喳喳的鸟雀在檐下做了窝,青白色的鸟粪沥沥拉拉浇得门前的小石狮满头满脸。扣响门环,庭院内毫无动静,依然是几束开着粉色花朵的夹竹桃默默探出墙外。
房玄龄心里一紧,慌忙绕着院墙向东走,这才发现往日停放车马和居住下人的东院,那车马门是虚掩着的。推门一看,总算见到了人。只见在大院的一侧,一位头发花白,衣衫褴褛的老人正在吃力地推着石碾。那碾盘上碾压的是掺合着谷糠的晒干了的青柿蒂。走近细细一看,房玄龄这才认出来,那老人正是岳父家的多年赶车的把式哑叔。
其实,哑叔并不哑,他只是有些耳背,轻易不开口不爱说话。
认出房玄龄后,他又惊又喜,放下了手中的推杠,连忙接过房玄龄的行囊,诧异地问:“姑爷,你,你怎么现在回来了?”说着,他把房玄龄引进了自己住的大车院厢房,并随手关了房门,把声音压得低低地:“前两天,瓦岗寨的人还来过,老夫人说,瓦岗寨与姑爷的仇结大了,非要把姑爷弄上山不可,姑爷不会回来了,可你怎么就,,,,,,”
从哑叔的紧张神情和闪烁其词,房玄龄感觉到家里的情况和自己的处境,可能比预想的还要糟,他急忙问;“老夫人呢,她老人家可好?”
“自从小姐母子被抢走后,三天两头,官府也突然间来得可勤了。怕他们搅扰,老夫人干脆搬到村西的老母庙,不回家了。那西大院就一直空着,倒省了不少麻烦。”
听哑叔说,老夫人还健在,房玄龄的心里稍稍好过了些。他立即站起身,背起行囊,告诉哑叔,由于急于见到老夫人,他就不在这里停留了。出门时,见左右无人,他仍十分謹慎地要哑叔不要把自己回来的事告诉外人。
村西的老母庙,坐落在一座隆起的不高的土岗上。拾级而上,小路蜿蜒于翠柏之中,那尽头的庙观,被几棵高大的枝叶繁茂的梧桐树覆盖着,环境十分清幽。这里原是岳家为祈福子孙而建,本来就没有什么外来香火,荒乱年间就更是人迹罕至了。来到庙前,还是谨慎地回头望望,见身后确实无人跟踪,房玄龄才轻轻地叩响了庙门。
吱地一声,开门相迎的果然是岳母。五十多岁的她,一身道婆装束,倒不显得十分苍老。她怔了一下,一把拉过房玄龄,上上下下地打量,惊喜地自言自语:“好好的,好好的,不是做梦啊,你真的回来了?”
“回来了,真的回来了。”房玄龄回答着,眼泪直往外涌。
把房玄龄带进殿后的卧室,岳母招呼他在桌旁坐下。那桌上摆着一沙锅米粥,一盘子酸菜,一小筐柿饼和大约是柿糠面做的窝窝头。想是正赶上吃午饭的时候,岳母就拿来两幅碗筷,要女婿和她一道用餐:“孩子,凑合吃点吧,这年头,只有这些了。”.
“让母亲受累受苦了。”房玄龄拿起窝窝头,鼻子一酸,那东西进嘴时也不觉得苦涩了。
“孩子,告诉我,究竟为什么,瓦岗寨非要把她们母子接上山?”岳母无心动筷子,好一阵终于开了口。
“她们母子的事,我在外是一无所知,也只是昨天在客栈里才听到了一点消息。”房玄龄将从莫大嫂那里听来的情况说了一遍。
“这就难以琢磨了。”岳母说,从瓦岗寨的态度来看,他们前后的确是很不一致。一开始只是说他们的大头领和你是至交,灾荒年送些米粮给点照顾;后来就变了,说是接她们母子,就是要请你上山,请不动就硬抢。这是逼你入伙呢,还是找你寻仇?不弄清这些清况,她认为:房玄龄不但不能露面,更不能和瓦岗寨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