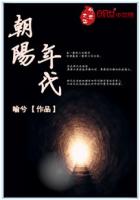重泉县令复反,李儒、张济兵少,绕过重泉,抵达莲勺,方才停歇。张济憔悴苍老,一路上木讷不言。
一路奔逃,众人困顿,于莲勺县暂歇。
“李参军,李蒙、王方二位校尉何在?”张济接过亲卫递来的水袋,也不喝递给李儒问道。
“自然是在该在的地方。”李儒接过水,随意回道。
“李文忧,你信不信本将杀了你。”张济暴起,镪啷拔出佩剑,指着李儒,声色俱厉“你别以为本将糊涂,老樊就是因为你故意的,否则焉能战死?”
李儒有些意外的盯着张济,没想到这张济如此聪明,这一路逃跑居然有些反应过来了。皱了下眉,如不是你有个好侄儿,今次连你一块儿算上。“杀我?张将军你可想好了?将军尚等我为他抵挡段煨,杀了我你去?”
“你。。。”张济手颤抖着,咬着后牙槽“李儒,你若不能灭了段煨,不用袁将军动手,某亲自取你性命。哼!”收起刀剑,恨恨地坐下。李儒毕竟是袁平拜的参军,自己不好杀他,杀个李儒没什么,然而会影响秀儿和根儿的前途,罢了!老樊,我会替你看着李儒,若真不能败段煨,我定在死前先杀了李儒,让他下来为你赔罪。
张济与李儒不合,各自老死不相往来。李儒驻在莲勺,不再后退,派人给袁平快马送信,手里不足千人,就此驻扎起来,像似要在此等候段煨一战。
张济连日来心中紧张,该死的李儒,这是要寻死乎,几百人驻在莲勺,段煨大军一来尚不用攻,自溃也。
“将军,咋就在这陪着李儒找死?”亲卫小心看看周围,低声向张济问道。
张济瞪眼道“找死不找死,本将不知。不过,李儒肯定有计议,你看满城尚有人烟乎?”
亲卫若有所悟的点头,确实,莲勺县城居然毫无人烟,记得来时尚有住户的。李儒那老小子这次肯定要使坏也。
段煨对胡轸多有疑忌,胡轸也有感觉,因之请令追击李儒等人,段煨有心试试胡轸与了万骑,自在临晋整顿大军。一路追赶,胡轸尚以为李儒等逃回长安去也,没想到追至莲勺,发现李儒驻扎在城里,因之团团围住。
胡轸有些纠结,到底攻不攻打。攻打害怕中计,不攻吧,又怕段煨疑心,好一番挣扎。下定决心即刻攻城。
莲勺城潜,焉能顶住,很快城门洞开,胡轸一马当先杀入城中,李儒节节败退。
“李儒,你的手段呢?再不用出,你我今日死也!”张济一剑砍翻杀至身前敌军,冲李儒吼道。
“恩!差不多也,本想擒一“虎”未想中一“狐”,罢了!算段煨命好!”李儒神神叨叨的念道,转身招呼张济从后城门跑出。数百步,眼前出现一土山,李儒不管三七二十一纵马向土山冲去。
张济一边跟着一边心中疑惑,莲勺县城四周平整开阔,什么时候出现一座土山了。正愣神,突然“吁。。。”拉住战马,前面箭戟相交,竟有军队严阵以待,仔细一看,原来是李蒙领军当面。张济颇为怪异,四下看去,山是新造,环绕一圈,中间开出口子,天然形成一座大营,李蒙派人堵住山口。这是要干啥?胡轸是攻不进来,但是派人往口子处一守,咋也出不去了啊?自入死地,李儒你这是要坑死大家啊!
李蒙抱拳对李儒行礼,见李儒以目视己,忙道“参军放心,蒙已经按吩咐做好!保管叫段军有来无回。”
李儒点头,也不说话,自转营中用膳去了,气得张济暴跳如雷。
胡轸树清城里,接报说李儒逃入山中去了,心中讶异。随亲卫至土山一观,这莲勺何时有这么一座小山的?李儒看来是事急,这种死地也敢入。想及此处,便为注意多出来着土山。
“将军是否攻进去,抓住李儒等人。”司马问道。
“不用,这等死地,李儒也敢乱入。你派十数人看住山口,老子饿不死他!”胡轸挥挥手,摇头叹息,李儒号称西凉智者,然一力降十会,人力终有尽时,这不就让老子给堵山里了么,早晚得自己出山投降,段公这次当该不再疑我。
招呼大军回返城中安驻,派人给段煨报捷,一面等候段煨下一步指示。
是夜,胡轸部巡城士卒,立在城楼小心巡视。
“空。。。空。。。空。。。”
“老哥,你听见啥声音没有?”
“恩!好像是地底下传来的。莫不是闹鬼。”几个胡轸士卒闻言,脸色发青,嘴唇颤抖,相互靠拢,小心向四周巡视。
“司马通了”李蒙军士向自己司马兴奋的说道。
“妈的,这些日子,都他妈成土耗子了。总算成了,让兄弟们小心往外退,顺便检查下绳子,可千万别给绑漏了。”司马抹了一把脸上的泥灰,小心吩咐。
不一会,近千李蒙军纷纷从土山中间地底下冒出,洞口巨大绞盘捆着几根巨大的草绳。张济不明所以,摸摸草绳,眼神怪异的看着不断冒出来的士兵。“李校尉,这些时日以来你就做了这个?”
李蒙点点头,“张将军,可仔细看看。”
张济好奇,闻言派个亲卫,执个火把跳入洞中查看,好一会儿爬将出来。
“如何?”张济急问。
“将。。。将军,好大。。。”司马显然有些惊吓,说话断断续续。张济好一阵才明白过来,李蒙挖了一条地道,很大很长,一丈之宽,似乎密布于莲勺县城之下。洞内全是木头支撑,每根木头皆巨绳相连。立时目瞪口呆,李儒要干啥?
此时,李儒刚刚睡醒,睡眼惺忪,撑个懒腰,缓缓行来,开口道“李校尉成了?”
“回参军,成了!”李蒙恭恭敬敬的对李儒回道。
“好!”李儒双目精光连闪,满脸兴奋“开始吧!”
“喏!”李蒙行礼,转身大声呼喝“绞盘,起!”
“呼。。。嗬。。。”号子声响起,上千壮汉精光着上身,缓缓推动巨大的绞盘,“嘎吱。。。嘎吱。。。”
城中胡轸军已经歇下,胡轸正在假寐,震天的号子声将之惊醒过来。披上衣甲,随招呼亲卫、司马等远远望向后城土山方向,眼前着看守土山口的几十个士卒惊恐的狼狈逃回报信“将军,山中好多。。。好多人。”
胡轸皱眉不已,这得不少人吧,这么大的声音。李儒有援军了?怎么弄出这么大的动静?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茫然中,“轰隆隆”如闷雷般声音响起,胡轸等人茫然的抬头望天,月明星稀,没见要下雨的样子啊。怎么还打起雷来了?
张济目瞪口呆,脸色发白,望着身边坍塌下去的巨型壕沟,沟中奔腾着浑浊的河水,艰难转头,咽口唾沫“你。。。你们联通了河水?”
李儒淡然的点点头,“李校尉,可以领兵出击了,勿使胡轸一人逃脱。”
李蒙领命,不久,一条条小船推出,放置壕沟中,随河水沿壕沟冲向莲勺城。船不大,每船十人,皆执弩箭,着长戟,船首尾各立火把照明。
胡轸等人远远望着星星点点逐渐照亮的夜空,瞳孔放大,一丈宽的地面在他们眼中不断坍塌成壕,壕中河水奔腾,沿河而来数十艘快船。
“敌袭”凄厉的叫声想起。
胡轸军立时爆发,哄乱起来,各自着甲,寻找战马。“轰。。。轰。。。”一座座房屋地面塌陷,战马、士卒轰然落入深壕,战马长嘶,士卒惨叫,俄而淹没于洪流之中。
“撤,撤出城去”胡轸目眦欲裂。
纵马沿街外城外冲去,眼看要出城。“轰隆。。。”城门口道路塌了,还好胡轸反应快,一把拉住马缰,险之又险的立在壕边。一马平川的莲勺,片刻如河水倒灌,到处都是壕沟联通,约摸丈宽,河水满壕,掉入壕中战马、士卒,淹死的浮于水中,未死得扑棱着惨嚎,一时间沸反盈天,犹如人间炼狱。李蒙站在船头指挥着捕杀掉入壕沟未死之人,不时补上一戟,站在岸上运气倒霉乱窜的,送上一箭,当真好不快意。
张济一夜惊恐中度过,凡李儒到处,自动退避三舍,此人太过可怕,杀人如麻的张济,从来没有想过,战争还能这样。李儒不出手则以,一出手几乎不伤分毫灭敌万人,这是何等之厉害。
亲卫倒是很兴奋,四处打听,将听到的回报张济。原来李儒派李蒙将莲勺住户全部迁出,派兵压着挖通河水,又联通莲勺壕沟,壕沟宽丈约,外绕莲勺全城,内除街道,因敌军进城要纵马未挖通外,其余所有皆挖开,全用木头支撑,巨绳相连,待胡轸进入城中安歇,于夜挖开各处城门外部分。绞盘用力,拉倒巨木,壕沟立成,河水倒灌,莲勺顿成水中泽国。
一夜厮杀,胡轸等勉强聚拢部分士卒。比及天明,除胡轸处千余人立于莲勺县城主街道上,其余三五成群的立于一座座“孤岛”之上,各自抱团发抖。胡轸浑身都在颤抖,李儒果非常人也,莲勺就像一个星罗密布的巨湖,他被困在岛心,湖中李蒙领着快船,射杀着想要逑水逃走的士兵。胡轸这里人多,也执有弓箭,李蒙损失几个人后,便不再靠近,专施对付落单的,困于“小岛”不知所措的,犹如一条条毒蛇不断吞噬着胡轸的性命,此役不论如何,段煨焉能饶过他。
河水为之染红,到处是浮尸断木,天空似乎也为之哭泣,淅淅沥沥的下起小雨。
“文才,此时可愿降乎?”李蒙给李儒撑着伞,小心的护着立在船头。李儒对惊惶的胡轸喊道,刚刚四下看看合计一下,各处尚有三四千人,加上昨夜于水中擒住的,怎么着也还能有个五六千人马,困死他们不难,但是太过可惜,能够收降自然最好。
胡轸惶然的看着李儒,不敢言,不能言,心中害怕,想投降,但是周遭皆是段煨派来监视自己的人,士卒好办,这几个人却是难办。
良久,胡轸未有回音,李儒眉头大皱,这胡轸如此傲气?不该呀!当下又出言道“文才,看在同为董相效力过的份上,吾再给你一炷香时间考虑,否则万箭齐下,悔之晚矣!”
胡轸心中一紧,他自然是不想死得,尤其死得如此窝囊,但不敢开口。
“将军降了吧!”一个司马跪倒在地,呼啦啦跪倒一片,士卒呼天抢地地冲胡轸喊道。一夜惊吓,此刻他们只想活着,若是两军对阵死于沙场,那是命该如此,如今能活,干嘛要寻死。
“吾不能也!”胡轸语气凄惶,以目视亲卫。
“吾等明白”跪伏于地的几个司马交换眼神,大吼一声,各自跃起,手起刀落,胡轸身边几个亲卫尚未反应过来,人头落地。“将军现在可降也?”
“降”胡轸抹一把脸,不只是泪水还是雨水,斩钉截铁的说道,段煨我胡轸对的起你,自投靠你来我兢兢业业,小心谨慎,不料你一直疑我,今入死地,众军求活,怪不得我。
胡轸率部投降,虽然降军远多于李儒军,但李儒毫不在意,吓破胆的胡轸军,焉敢有别的心思。李儒一边安抚降军,一边给袁平报捷。同时,派李蒙护送莲勺县城百姓,往长安迁徙,莲勺县城恐怕十数年难以恢复。以李儒之意,张济应该也随同李蒙回转长安,不过张济出于对李儒手段的佩服,非要留下来,李儒也由得他。
整军毕,李儒拉过胡轸好一番吩咐,胡轸连连点头,良久招呼数千人呼啸着离去。张济翘首望着远去的胡轸等人,对李儒道“先生,这是又要算计谁了?”
李儒听张济叫自己先生,难得。抬头望天,语气散漫“算计?看是谁送上门来吧!最好是段煨,别又是一胡轸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