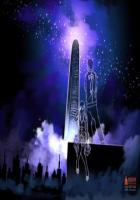-
“你的意思,我明白。”
秦莫泉轻声叹了叹,他低头,袖中的云水绡卷轴将神力源源不断涌向自己身体,修复自己的身体与灵魂,至此时以让他恢复于与赵东垂动手之前,他这便松了心神,随手将支撑身体的长剑放到一边,放松地坐在云雾间。
天空明净如出,微风拂过,送来一阵清凉,秦莫泉闭了闭眼,声音低沉而坚定:“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会退缩在后,让宛绛来替我先坚定、先勇敢。”从前不会,以后更不会。
无论有没有今日的变故,也无论何时,她只要在愿意回头的时候回头,往前或者往后的路,他都会竭尽全力为她铺成一片坦途,她只要走自己想走的路。
他害怕失去他们的爱情中这份未有瑕疵的完美,更怕失去这份爱情,因而小心翼翼,所以一旦真的失去,为了得回,他也就无所顾忌。
赵东垂:“……”
——不,我们说的不是一个意思。
他默默看了秦莫泉一眼,默默把视线撇开。
秦莫泉没在意他的神色,只笑了笑,轻咳两声然后吩咐,道:“画溶,收阵吧!”
朱画溶一点头,立刻施法收了阵。
阵外,弈宛绛等人只看到秦莫泉面色一变,令朱画溶启了凝流阵,而后便是一道激荡翻滚的剧烈术法波动,震动得法力稍弱者微微后退。不过转瞬,待他们定睛一看时,便见原本护在秦莫泉身前的赵东垂远远站在他右方,秦莫泉缓缓站起,身前落了一滩灵气鲜活的鲜血,惯用的武器随意地放在一边,剑鞘剑身隔得老远,他却不看一眼,只看着弈宛绛。用他一贯温和而包容的目光,将她看在眼里,看进心底。
他一边朝弈宛绛那边、或者说朱天妖族皇城出口走去,一边道:“这件事总要对你们以家有个交代不是吗?既然上天未降法旨,那么便按规矩来,若将此事作罢,放我离开,若想处置我,看你们留不留得下我。若是留不下我却又不服,”秦莫泉一扬眉,面容语气都几位平静,那话语的含义却极尽自负傲然,“钧天之上、天宫之中,随时恭候。”
他一面走着,一面抬手,在他开口的同时走来的赵东垂恰好在此时走到他身边,将手中为收回的长剑递上。
暗金色的长剑落到秦莫泉手里,暗沉的色泽竟一点点褪去,像是突然拥有了生命一般,古朴的纹路亮出耀眼的艳红,似火焰在燃烧、似鲜血在沸腾。
就像这时候的秦莫泉,一步步走来中,眸中亮着的生命的光火。如他此刻那般,铅华洗尽、破茧成蝶、浴火重生。
弈宛绛神色怔怔,仿佛回到了数千年前,少女芳心的第一次心动。
便是这一身光彩,教公主之尊的她折节倾心。
可之后数千年,他却收起了一身光华,尽让她将他的岁月蹉跎在毫无天分的事上。
华彩埋没,珠光蒙尘。
温柔得要将她溺毙,却再也看不见当初锐气飞扬的神采。
直至这一天、这一刻。
他缓步走来,脚步扣在地面上,轻得没有声音,但一下一下,如天光破开照下的一寸寸光辉,一点一点破开她的心防。
再一次踏进她的心里。
再也没有人,比他更懂得让她心动。
弈宛绛几乎要忘了一切伤痛,只想将怦然跳动的心压回胸腔。
弈后应扶娆眸光暗了暗,竟不想对上秦莫泉毫无阴霾的目光,转而朝赵东垂发话道:“东垂大殿下,您身为金乌族大太子,看尽天下不平之事,此刻既然在场,可否说句公道话。”
赵东垂笑笑,正要说什么,冷不防听得弈宛绛忽然开口:“东垂殿下对秦莫泉千里奔走救护在前,执剑相赠在后,此时难道不该避嫌?”
赵东垂淡淡撇了她一眼,道:“这把剑本来便是他的,何来执剑相赠之说?”虽然,借太阳精火淬炼本命法器多年,也不是谁都能获得的殊荣,“再者,避嫌?本殿自诞生于世数万载,从未听说此事!公正便是公正、不公便是不公,与亲疏远近何干?宛绛公主既然出此言论,改日我等天宫对峙。”
亲近之人的不公难道不是不公?若是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谈何为神?
别人可以避嫌,他不行!
若需要避嫌,意味着不能公正以待、或者被质疑不能公正以待,何谈执掌公正?
天界没有无心之言,弈宛绛既然出口质疑,无论他想不想追究,她都要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
弈宛绛冷哼一声,道:“随时奉陪。”不就是关个百十年禁闭吗?她正好想静一静,谁怕谁?
秦莫泉毫无被忽视的尴尬,面色不变停在几人面前,道:“若尔等毫无异议,且让一让,放我离开。”
延尤弋太子闻言便从容退开几步,侧身一让,道:“秦公子莫误会,在下不过是被牵累于此,并无与你交恶之意。”
开玩笑,上天和金乌族大太子一同视而不见的事端,他凑什么热闹。
弈宛绛轻轻抬眼,站到他面前,语气坚定而隐忍:“我来。”
秦莫泉神色毫无变化,见有人站出来,便自然而然地拔剑出鞘。
其他人退开合适的距离,留那二人相对而站。
秦莫泉看着弈宛绛,目光平静、言语温柔如初,“宛绛,或许是现在的我没资格爱你,可只要你心里还有我,我就不会放弃。”
他没有说的是——若你心里不再有我,自然不会纠缠。
这并非克制。
只是他此生仅有的这份爱情中,最后的尊严。
弈宛绛听不明白这样一句话跟他们目前的形势怎么对的上,因为她本就看不清他们真正的形势,也因为,这句话并不是交代给她听的。
两人同时起剑,剑光如虹。只对了一招。
弈宛绛的剑,似闲凉清秋的行云,似幽静山涧的流水,轻烟沉暮,如光曳影,窈窕飞扬。
美好幽闲,是她最美的爱情,最好的梦。
秦莫泉执剑的手移了半寸。
这样的剑势,他怎能破开,怎舍得破开?
便让她完整使出这一剑,又如何。
剑光似残花落尽的晚春,虽然绚烂,难抵无边寂寥。时光易逝,春日芳菲终究会凋零。
剑尖相抵,又仿佛交融般迅速划过,秦莫泉的剑在擦到弈宛绛的手掌之前再次偏了剑势,自她颈侧划开。
二人擦肩而过。
弈宛绛只觉得颈侧一凉,长剑擦颈而过,一缕断发缓缓飘落。
一招便分了胜负。
手中的剑由剑尖至剑柄,生生裂成了两半,她握剑的手掌却毫无损伤。弈宛绛恍惚回头,竟觉得后怕而又委屈。
“秦莫泉,对你来说,我是什么?”
弈宛绛看着秦莫泉,声音轻软得有些脆弱。
秦莫泉止住脚步,是什么?在此之前,他有很多很多答案。
你是我毕生的挚爱。
是我自缚的困茧。
是我终其一生只望使之幸福的存在……
可现在,秦莫泉觉得,另一个答案最能表述。
“你是我此生,最后的天真、最天真的自负。”
自负只要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就可以维持。但所有的天真,都终将败于现实。
-
循着前方若有若无的背影,楚银霂穿过数条人来人往的街道。身边的行人渐渐少了,最后一个巷道尽头,一个远隔尘嚣的青山出现在眼前,一眼望去,尽是枝干曲折的苍翠青松。
那身姿曼妙飘忽的身影便停驻在半山腰的密林中。
凝在那一片浓郁的翠色下,仍然维持着不变的优雅从容,又带着与世隔绝的缥缈。
楚银霂停在她身后。
连心术转过身来,那双黯淡的目光便落在楚银霂身上。
“银霂,芝术师妹几番警醒,你为何不去?你不相信我们的话是吗?你,确实有不在意我等的底气,可这一次,我希望你能听一听。”
她怅然一叹,紧锁的眉仿佛承担了一世的哀愁。
楚银霂神色淡然而平静,只问道:“你……看到了什么?”
延芝术修的大梦千年之道,说过的话,她自己都记不清才是,会让另一人知晓,并郑重以待,只能说,她那次说的话,恐怕真的有些重要,才会让她频频记起,而非说过了就忘,也只有这样,她才会向他人提起。
“我看到……”连心术转过身,看着远方层层叠叠的翠绿松针,目光仿佛掠过一片如那般深绿的沉郁,“血海翻腾、天倾地陷,天上灼目的光辉遍布,无法直视,地面万里焦土,了无生机……我还看到,你与夏宛峙站在逆轮宫前,看着彼此的目光,如初遇般陌生……地遗池中没有源胧石,或许是一唯一可以挽回的一线生机,可你错过了。”
奈何,那时候楚银霂没有信。
奈何,不到事情过去,延芝术也不知道,她说的话是真的重要还是不过妄言,哪怕是真的重要,她也不知该如何行事才算重视。
最后,连心术看着楚银霂,声音庄重、认真:“而这次的关键,在今天的你与夏宛峙身上。”
对于之前的所谓错过,楚银霂听过便罢,面上并无愧悔之色,她若有所思道:“这些都是你因地遗池引出的异象吗?嗯……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