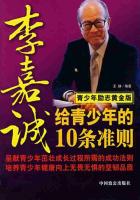衡瑟将身子绷得老直,急声问道:“这又是为何?是要赶我走么?难道因为您公子的疤痕吗,这可是大冤枉儿,确确实实与我无关啊!”
常征表情有些难堪,支支吾吾半天,没有接话,求助似地望向妻子。
白殷只好叹了口气,眉眼微垂,有些不好意思但又比较无奈地说:“你在我们这也呆了一段时日了,除了腿脚治起来比较麻烦以外,其他伤势已经基本上治好了。”
衡瑟感激地说道:“是啊,这段时间劳烦您二位费心了,在下在这向您二位道谢了!”说完,他弓腰俯身,低头肃容,拜了几下。
白殷摆了摆手,示意衡瑟莫要再拜,继而又叹道:“你先别急着谢我们,我们受不起,因为说不得可能我们要做回恶人。”
她接着说:“你这下身不能动弹,也不是不能治好。只是耗费时日过长,可能要费个几年光阴。”说到这,白殷顿了顿。
衡瑟一听自己双腿还有救,不仅极为激动,他脱口而出:“真能治好吗?那要劳烦二位,太谢谢了!”
白殷将脸撇向旁边,不敢看病人。她咬了咬牙,吐出下文:“我家虽不贫穷,但也不富裕。你我非亲非故,况又白吃白住,如何可以耗几年时间对你?光是几年间治疗你病的药材费用恐怕都需耗一笔大数。所以…”白殷转过了身子,背对着衡瑟,声音从空中像流光一样飘着送了过来:“所以…所以你也别对我们生出怨恨之心。我们自己也需要过活,就算我们不计较,村里人也会说的。我们准备让你再休养几天,然后…然后你就走吧。”
衡瑟听到这话不仅凉到骨髓,惊地直打哆嗦。这流光般的言语真如流动的极光一样孤冷无情,冰莹透明。是啊,这话很透,很冷血,更现实。自己在逃亡时带在身上的盘缠早已丢得没影,就是没丢也不够看病。人家凭什么花上几年时间收养非亲非故的一个残疾?还要让其白吃白住,耗费药材钱财治病?更要像伺候老人一样,床前床后?自己也敢想!这段时间被安逸惯得太舒服了,连起码的人情常理都忽视了。这话还让人提?瞧常医生为难的,白姑娘为难的。自己傻了吧!
傻了吗?衡瑟悲由心生,整个人气势弱到了不存在般,忽又自怨自艾起来:呵呵,自己是傻了!没有付出怎么会有回报?如果不是自己想安逸,又怎么会去欺骗那些无辜的女子?怎么会去欺骗芸儿!怎么会落下残疾?安逸!安逸!安逸到不安逸!不甘心啊,自己其实还想再安逸下去,还不想去世俗,不想去烦恼家族的十年之约,还想看看自己千辛万苦得到的灵介到底带来什么灵能,还想把腿脚医好,还想报恩!可是…又能怎么办?
衡瑟真的流泪了,不过泪水并没有像往常的戏码那样不值钱般地涌出来,只是在眼眶里转着圈,眼圈不堪重负得红出来,连鼻头都被牵连了,酸涩涩地发泄着它的不满。
衡瑟显得可怜极了!他不管不顾地用手抱住头,低头垂下面容。他是真的,他是真的!他很稀少地流露出真实的情感。这种情感很是震撼人,身边的三个大人,被这种悲凉的震撼彻底束缚住了。
他们纷纷猜测:他这是真的吗?如果是假的,也太可怜了些。
少年实在忍不住,首先安慰道:“武士先生,你别难过了。其实我姨姨,姨父也不太想就这样抛弃您,他们是有难处的。只是村里悠悠之口难堵,留个不明身份的人在家,尽心尽力的医治伺候好几年,实在有点奇怪,再加上您这白身白丁,一无诊疗费用,二无理由依据,如此常住也确实有些说不过去,不免会有人乱猜。”
横瑟不答,一动不动。另外三人看了病人一会,村长再次开口。
“不如这样。”少年看来是真的很想帮助病人。“您方才提到您是天空门的弟子?更是一名武士?”
衡瑟抬起了头,眯了眯眼睛,将珍贵的泪水收回,对着村长说:“对,我在那自幼长大,已经学艺多年。”
“如此便好办。”少年显得很是胸有成竹。他转向了常白夫妇,接着说:“姨,姨父,你们可能还不太清楚,听父亲说天空门在村外面名声是极大的,随便出来个弟子在外行走,到哪都是很受尊重的。咱们虽然不能肯定他就是天空门的,但从他的叙述和随身携带的那个门主信令来说,真实性很高。”
村长走到小常汗跟前,伸手拉住他的小手,又用另一手怜爱地抚了一下他的头,让小常汗抬头直看他。村长说:“不如这样,留下武士先生教小汗汗习武,充了医资,如何?对村里人有了交待,对咱们也能落下好处。”
横瑟闻言,如行走于黑暗间欣喜地看见一丝光明。他忙急着答应:“我愿意!我愿意交贵公子习武。只要能让我继续呆下去,腿治不治好无所谓!请二位恩人应允。我定将我终身所学,决不私藏尽相地传于公子。”
常征听村长这么说,似乎也觉得有门。他难为的表情松了一些,但仍不放心地向横瑟问道:“我们村里人是不太懂什么门派,什么武艺的,更何况你的武艺如何,我们都没有见过。你都会什么?或者……或者你强吗?能教汗汗什么?他学了又能如何?再加上你的腿都这样了,又能…如何教他呢?”
横瑟好不容易在水中才抓到了这根稻草,怎么能放手?放弃可能的希望?他表情出奇地坚毅,语气出奇地自豪。他说:“我在天空门自小就有天才之名,学艺颇精。十年世间行走,少有敌手。在下掌握的武学可不算少,体技如:闪行步、绕魂手可随机应变,空手制敌。器技有:撕空斧,青光剑可一刃在手,横行无阻。并且,我幸运地得到了传承:鞭之传承五式,更是有劈星斩月,碎山破浪之大能。”
横瑟偷看了常征和白殷一眼,接着说:“若我传授公子武艺,必将尽心尽力,将我所学,所悟,所观,所知,尽数授于公子。公子日后若在外行走,虽不能无敌于天下,但也有自保的本事,不受人欺凌。若公子悟性颇高,将所学所见细细体悟,随着日后经历丰富,武艺提高,那运用所学建功立业也不是难事。我虽不能身体力行,手把手地教,但通过师门的系统有效的传艺步骤,一样能让公子掌握的。”
他又看了一眼村长,说:“您二位和这位小兄弟都是好心人,应该能体会到我目前的难处。我若此时在外,就是无钱无势有伤的残疾,再加上师门时时派人找我,我又到哪里躲去?我又如何生活?”
横瑟再次转到常白两人这边苦苦恳求:“请二位恩人行行好,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帮助在下度过难关。就算日后我腿仍不能好,那也让我通过这几年的努力,把您二位这次救命的恩情报了。”
白殷忧愁得发着呆,心里却暗暗地佩服对方:“为报恩才要留下”这种说辞都抬出来了,真是好生厉~害~
常征表现得也是比较良好的。只见他眉头随着病人的话语皱了松,松了皱。嘴唇抿了厥,厥了抿。整个人仿佛陷入了无穷无尽的挣扎当中。
终于,他有点累了。
于是,他叹了口气:“罢,罢。这几年都要省吃俭用才行了。既然你说的如此可怜,我们也不好再当这个恶人。我是个医生,确实也不想就这样放你走,如今事情有了个解决的法子,我替你感到高兴,也替自己感到高兴。我会负责到底,将你的腿治好。但你也要对我家汗汗负责到底,不可胡乱应付了事才行。如果被我发现,我们马上就放弃你。”
横瑟赶忙应到:“谢谢恩人大德,在下晓得,定当认真对待。”
白殷接过话头继续说道:“武士先生,你莫怪我们夫妇俩此番无情。这次虽然向你提出,其实我们也不想,只是村里人会说三道四,我们呢又确实比较拮据……所以这次才有此一说。而这么说也不是成心赶你,只想借此和你商量下有没有更好的法子。没想到霸天还真想出了好法子,真是皆大欢喜。如今你就是我家孩儿的师傅,希望我们日后能好生相处。”
似乎为了道歉,母亲立马拉过常汗来,对着男孩吩咐道:“来,汗汗,之后几年,武士叔叔就是你师傅了。叫师傅…”
小常汗自到这,就对躺在床上的这位很是好奇,一直饶有兴趣地望着他。此时听见母亲唤他,兴奋起来,连什么个意思都没明白,就快快脆脆地应了一声:“师傅好!”
横瑟看着这个将要成为自己徒弟的男孩,相当喜欢,甚至非常奇特地出现血肉相连的感觉,真是百感交集:没想到日后终于有着落了!流飘无萍的日子终于结束了,虽然仍然要承担一部分责任,但自己喜欢。这个孩子看着如此惹人怜爱。以后好好对他,有了感情,万一腿医不好,难道他就不会给自己养老送终吗?他父母长辈们可不知道,这个孩子早已经了倾注自己这些年来的心血和心愿了。
你好呀,小家伙。你好呀,小徒弟。我倒想问一问,身为灵能者的感受如何?你的灵能到底是什么呢?芸儿,我不能动了。不过,有机会一定要让你看看这个小家伙。
横瑟俯身到床边,伸臂搂住了小常汗。他关爱地用脸庞在男孩的小脸上亲昵地厮磨着,而且他又感觉自己眼眶湿了。
为什么要哭呢?为什么呢?
********************分割线*******************
常征、白殷两人在送村长回去的路上。他们很乖巧地微微落后了一点,不敢和少年村官儿平行。村长似乎知道两人为什么要送自己,带在前面走得很慢。
终于,白殷禁不住疑惑,向村长询问:“村长!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要让汗汗拜那个骗子为师?”
“因为就像他说的那样,让常汗跟他能学到东西嘛,我看他也不怎么弱的嘛,有什么不好?”
常征立刻跟着媳妇儿反驳:“不弱?他弱的和蚂蚁一样怎么不弱?就是二十年前才进村的,那个弱到家的小家伙,叫什么浪星的,也比他强不知多少倍吧?”
村长声音似乎还微微透着戏谑:“那怎么了?浪星那小子强和我们可爱的武士先生有什么关系?”
“村长!”白殷急了,她声音接近喊了。
村长停住了脚步,皱了皱眉,望向白殷。常征赶忙拉拉妻子的衣服后角儿,和妻子也俱站定了,不过他是站在妻子身后。
白殷可是不依不饶的主儿。她没有理会丈夫,继续道:“别说那个弱得可怜的浪星了,就是我们夫妇二人,也可以吐口吐沫,就压死那个骗子先生。我们是说村里人有的是人教,干嘛要让那人教?”
村长面目冷了下来,吓得常白二人微微后退几步。只听这个可怕的男人深沉缓慢的声音传了出来:“你们教?村里人教?你们是不是脑子进水了?你们不想想这里是哪儿?!”
村长不再看发呆的二位,又徐徐向前走动起来。
“能教我早教海馨了,你们见过我教过她吗?”
村长一提到这个女儿,脸色有些发青。“如果是我教,还能等到前几年她才被送走?恐怕早被送走了。”
“我告诉你们,这都是命!她是自己悟的!比你们两个白痴要强无数倍!比你家那个汗汗要强无数倍!”
常征弱弱地回了一句:“我们是说常汗的事,没说那个小姑娘的。”
“那不一样吗?!”村长发青的脸色变成厉色。
村长看者惊吓过度的两人,将情绪缓了缓。继续说道:“我知道你们有疑问。其实我作出这样决定,又让你们配合着演这么一出戏,只是为了让那个什么横瑟能多呆一呆,更能让你家汗汗能多呆一呆。”
白殷还是不明白:“那这么做又有什么效果?”
村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我给你们讲个故事。”
“从前有一个书生,作画作的很棒。但是由于本身并没有什么名气,他不得不通过一个有名的画坊来宣传自己的作品。但是!但是这个画坊收作品是很严格的,他们总是会在这个书生的画里挑各种各样的毛病。书生每次送上去的画都或多或少地被挑出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这让书生心里很不好过。虽然他自己的画也换来了银两,也通过画坊的热卖赚了不少人气,但每次被退回来修改,让他无法维持自己的想法,非常的不舒服。于是他通过冥思苦想,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在自己的作品右下角处总是画一只小狗。之后画坊挑毛病时老是挑这个小狗的毛病,让他去掉。但每次有新作品他又画上,再被要求去掉。久而久之,画坊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只小狗上,而书生很好的把纯粹自己的东西保留下来了。”
村长虽然不高,但依然“俯视”着两人:“那个横瑟,就是那只小狗。我故意留他下来,但终究是要有一天被去掉的。所以,让他在被去掉之前发挥发挥余热,干些咱们不能干的事,不是很好吗?”
<ahref=http://www.*****.c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