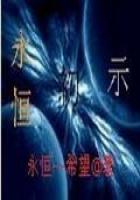就这么过去了一年。
我变成了高二的学生,我又回到了G县一中。它现在对我来说已经很熟悉了。如果说我在我的家乡呆了二十几年,有二十几年的感情,那么这里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没有怎么留恋它,但是,当我有一天离开了她,我也会很留恋她的。
同学依旧,只是熟悉了。
大家头天开学都是兴高采烈和和气气的。人人都有新的面貌,人人都有新的变化。见面也不忘讲几句客套话,三分钟一过,该谁好谁就好。
高一期末我没有考好,但没有落地。可我开始不满于这点成绩,我觉得愧对我的父母,发狠要好好的学。这一年是我心里最活跃的一年,我接触到更多的人,经历更多的事。
我也习惯了高中的生活,高中有高中的方法。
我还是时常喜欢看一些文学书,看一些伟人的感人事迹。有时候我讲给别人听,他们总是笑笑,我不明白,为什么要笑呢?大量的数字,字母,公式冲昏了他们的头脑,不过不用担心他们会变成书呆子,变书呆子的也就几个。
高二这一年我不无感慨地观察周围的每个人。我考虑和他们划清界限。我有我自己的理想,我的理想到底是什么,我自己也不清楚。不过我惊奇我的目光变得远大起来。
刚来时就听说班主任调走了。
听说来了个男老师,秃顶,叫胡力图。听说是个经验丰富,教学有方的教师。我很高兴,那个班主任,我对她的印象一直不好,尤其是她那张老脸。
不光是我,她的离开使得每个同学的脸上都洋溢着不可磨灭的喜悦,就像奴隶知道了一直禁锢着我们的奴隶主死掉了,努力制度废除,他们解放了一样。
新来的老师五十多岁,头发稀疏,笑呵呵的,眼睛不大,长着一张能说会道的嘴,有教授风度。
“我叫胡力图,是你们新老师。从此以后,我将和大家一起努力奋斗,争取人人有所收获。我们抓科学方法,注重信息。下面我来点名,李志,白林,郝静。。。。。。”
不知道这个老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管怎样说,变化总是看不见的,发展是漫长的。取代思想的方法来了吧?可能就是这个老头吧?
就这样伴随着这个老师的到来,我们也慢慢适应了那些枯燥,干涩的日子。
除班主任外,我们还加了一个语文老师,是高三的,给我们兼作语文老师,这个老头是教物理的。
教学上我们也没有太大的改进,每个老师的语调没变,教学形式也没有变。题是做不完的。
班主任老头也逐渐把他的计划落实了,首先根据我们的实际成绩定出了班委会成员,然后找到王力,又让他干班长。
一系列日新月异的教学方法和制度开展起来了。当我们对它们有异议时,他便会摆出许多大道理,侃侃道来。看他读书不少,词很能甩。
记得,他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表情依旧,那一米六五的个头来回在讲台上走动,边比划边讲。
他也没跳出那个圈,理论和概念是丢不得的,不过时不时他也讲些名言锦句,名人轶事。
经过了几次摸底考试——他的物理,他认为摸清了我们的底子,以为我们很有潜力,比那一年的学生都好。
他也说过,我们底子薄,基础不牢,应该抓住基础,然后步步提高。这是我们希望的,但除了他讲课时讲基础外,其他时间也只是给我们做题。我们平时就只学数理化,所以每次考试我们都没让他失望,他越发觉得我们希望很大。
时不时,学校还开一次会,总结一下学习各方面的事,抓一抓校风。
我有时觉得校领导们在主席台上,很威风,说话很有条理,他们摆道理,讲条例,说得一套一套,真厉害。
开完会,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开会,摆摆样子,费点口水。
记得刚上初中的时候,每个人的学习劲头就像刚打过气的皮球,只要稍一用力就有很强的反作用力,可现在这反作用力小了,是因为皮球泄气了。
大了,同学们都可以静下心来。学习文化知识是不懈的努力,题是不可以不做的,而且应该多做,做的越多成绩就会越好,所以,在我们的头脑里除了听课,便是做题,而做题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没有一个老师不是这么干的,就连我们的班主任——从省重点调来的特级教师也是这么干的。
再没有那后窗户可跳了,像初中一样,因为我们在五楼。不过可以逃课。
我和我同宿舍得王炽编了个理由,逃出来。去玩电脑。
刚摸电脑的手,禁不起兴奋,我的嘴老是合不上,这东西是好玩,比做题强多了!我忘我的玩着游戏。高兴过后,很累,而且我发现口袋里没了那么多钱,游戏又没玩够,心里堵得慌。我开始讨厌电脑。
高中的课程里,天天都有自习,有时甚至一天五节之多。老头说自习自习就是自己学习,所以自习他是不来的。
有的人,第一节课就开始小声唧唧,有的做了几道题,满意了,就开始聊天。球星,明星,社会新闻是我们的谈话内容,最能说得那个家伙永远是大家的红人,这样的人,不管他能不能干一些事情,别人也认为他可以干一些事情。
刚开始班里是世界局部战争,然后发展成世界大战,美国与RB战,中国和法国战,战得越来越凶,哪里冒火了都不知道。
偶尔一个大战役结束,使得整个世界大战停止了。那个战役是班主任老头打的。他来到教室,各国战火停下来。
他的战役就是演说,他颇有口才,书籍看来读了不少。老头神采飞扬,激扬文字,上至天文下至地理,从克林顿讲到**,从**讲到袁隆平,这些统统成为他的论据,不管充分不充分,必要不必要,反正做题是唯一。那个一米六五的老头在穿来穿去。
突然,一女生尖叫:“哎呀!老鼠!看!还在那爬呢。”
这个倒霉的小家伙。矛盾的中心转移到这只弱小的老鼠身上。真可怜!竟然连一只老鼠他们都会感这么大兴趣。整个班沸沸腾腾的,抄棒子的,拿球鞋的,跑最快的在前面。伸不上手的就眼巴巴看着。
我真是觉得好笑。来到我身旁的这个杀老鼠的小子,他平时连自己父母的死活都不管,此时却这么聚精会神地追赶着一只小老鼠。
这个时候的我,往往在发生危机的时刻,我是最镇静的那一个人,我正在做稳重的摇头,突然眼珠子差点掉出来,再也镇静不起来了:一个文静的再不能文静的女生正挥舞着扫埽飞快的拍打着仓惶而逃的小东西,它大概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凶悍的女学生吧?如果这次它能大难不死的话,它一定会讲讲这件事的。
最后,这只被弄得莫名其妙的老鼠找到了通向别地儿的逃路,跑到了老师的办公室。
老头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