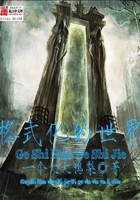冬天的夜晚,来的很快。
千寒被三个警察拉到一个黑漆漆的房间里,还没进去就能够闻到一股臭味,而且不知道从哪来的风,乱串着把臭味卷到房间内外。千寒做了个干呕的动作。一个警察把门打开,门立即被风晃得咿呀作响。等门关上了,灯打开了,千寒的身体被绑在了一张椅子上,脚被放在另一张与椅子齐高的板凳上。一抬头,是一盏昏黄的摇摇欲坠的电灯,灯泡上有许多小黑点,估计是苍蝇屎之类的。窗边的墙根上,有一拳头大小的破洞,风从洞中灌进来,呜呜作唱。
千寒想要知道他们究竟要玩什么花样。
“再问你一次,说还是不说?”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察瞪着他那双像是十天十夜没有合过的眼睛问千寒。眼球浑浊而布满血丝,眼珠像是别人吐的一口老痰。
千寒不回答。
那个警察摆摆手,示意他的同伙(又或许是下属)可以动手了。
他们把一些像一般的枕头那么粗大的木块搬到千寒脚边,垫上一根在千寒的脚跟下。
千寒面无难色。
两人都看了对方一眼,然后继续加码。
几块木头加完了,他们见千寒还是没有动静,于是毛了。
其中一个把挂墙上的鞭子拿下来,结果两手用力一拉,绳子就断了。
“奶奶的,那帮孙子这么快就又使坏了一条好鞭,”另一个白了一眼那鞭子,“用小刀吧。”说着一边盯着千寒无表情的脸一边从裤兜里掏出小刀。
“先把舌根给割了。”满脸横肉的警察往座椅上靠了靠,座椅发出咿呀声,听起来像是一种警告。
拿小刀的警察对他点了点头,另一个警察从一个抽屉里找出了用长尾夹夹住开口的半包盐,吸了吸鼻子,向千寒走去。
千寒的嘴怎么撬都撬不开。
那个拿小刀的警察于是给他嘴上来了几拳,却不料自己的拳头青红了。
千寒的表情依旧木然,他扭过头来,嘴唇微微张开,动了动眼珠。他生气了。
空气似乎已经凝固了,只有风还在固执地呼啸着。
拿盐的警察放下盐,掏出自己的小刀,正想要往千寒腿上插,不料身体突然僵硬,再看一眼脚下,一层冰正从脚底蔓延上来。
玻璃窗突然全碎了,洒落一地清脆。风吹得更猛了。
三个警察都冻住了,包括那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冰爬满他的脸,爬进入他惊恐的双眼,将那两口老痰冻成了琥珀。
同样结冰的还有绑住千寒的绳子,最后它们被冻碎了。
至于那盏昏黄的灯,摇曳得更厉害了,地上的影子也跟着摇曳着,阴影与昏暗的灯光在千寒的脸上交替划过。
窗边,一个将自己裹得紧实的人正背风站着,用他那亮如夜间猫眼的眼睛盯着千寒。
“你来了?”千寒张嘴说道,声音有些沙哑。
“不是你要我来的吗?”那人反问道。
“我知道你必定不会想要见她。”
“还没到那个时候。”
“那你又为何要来?”
“朋友邀请,盛情难却。”
“我不是你的什么朋友。”
“从今往后,就算是朋友了。”
千寒斜着眼看了来的那个人。“你守护了她那么多年,到底为的是什么?”
“年轻人说话太直,总是要吃亏的。”
“年轻人?”千寒嘴角微微一笑,“我都快要在这个地球上活腻了。”
“十一空间是一个让人无论在身体还是在心智上都成长或者衰老缓慢的空间,即便你活了几亿年,也不过是像打了个盹,过分的安逸是不会有太大的成长的。”
“是嘛?”千寒抬起头,看着还在风中摇曳的电灯,一种莫名的伤感涌上心头,笼罩着他的脸庞。
“怎么?被我说中了吗?”来者将衣服裹紧一点,坐了下来,右手食指开始在地上画着图案,“想开点,年轻人,世上的事情总是好坏参半。”
千寒握了握拳头,将盯着电灯的视线移开,面对着来者也坐了下来。
来者的脸庞被大大的夜行衣帽遮住了一大半,只能依稀看见下半张脸,而且下巴和人中部分被密密的白胡子遮住。
“但是现在,”千寒把身子稍稍往前倾,“我的朋友想要知道她的身世之谜。”
“你的朋友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强,我的孩子。”
千寒皱了皱眉。
老者停止了画画,接着嘴角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然后站起来整了整衣襟。“我该走了,后会有期,我的孩子。”
千寒愣愣地杵在原地,过了一会,他慢慢走到老者刚刚坐下来的地方,发现地上有一个闪光的标志,蹲下来一看,发现是一个类似徽章的图案,两个同心圆的中央一只麒麟的头被钉在一个十字架上,外围的圆环是一排龙胆花由生长到凋谢的过程,一共七朵。
千寒伸手去触摸那个标志,标志就变成紫蓝色的亮光,慢慢涣散了。他又突然麻利地站了起来,迎风看着破窗外灯火通明的世界被一团黑暗压着,自言自语道:“这漫长的黑夜,原来才刚刚开始,呵呵。”
事实却是,这漫长的黑夜,总要有人彻夜清醒着面对。
文琴一个人东躲西藏地回到家中,洗刷完毕后便全副武装地等待客人来访。
她穿着特种女兵的衣服(从小就梦想着成为特种女兵),裤兜里放着双面胶、绳子和高浓度酒精,衣服的口袋里放着手帕、小刀和小手电筒,房间的显眼位置还摆放着防狼水、电棒、拳击手套等防御工具。她熄灭了家里所有的灯,站到房间的窗台上,她向下眺望街景。
大街上空荡荡的,人烟稀少得很,偶尔不知从什么地方传来几声狗吠,声音在飙高后又急促地归于平静,好像一把尖刀要故意划破这夜的宁静。
文琴的眼珠动了一下。
楼下有动静!
她快速冲到楼下爸爸的书房,拧了拧门把,果然,门把较之之前松动了一些,虽然只是细微的松动,但机警的她还是能够察觉得出来。
砰!地板被踩踏的声音!虽然声音那么小,但听得真切。对了,来者就在附近!
文琴将手轻轻地从门把上移开,屏气凝神地听着屋内的动静。依她的判断,除非来者有登天的本事,否则不可能那么轻易就进入爸爸的书房,况且她还有一定的把握认定此人是谁,所以她还是能够确定爸爸书房里的东西是安全的,自己的处境也不算太恶劣,既然这样,自己就没必要弄出太大的动静惹得对方对自己出手,而且退一万步说,如果此人真的进去了,那么自己也难逃其魔掌了,更是要轻手轻脚的。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跳出一个人影来,从后面扑向她,将她紧紧搂住,并试图用熏满酒精的手帕捂住她的嘴。
文琴一把抓住那人的手臂,另一只手用手肘去击打对方的肚子,而一只脚踩向对方的脚板。
那人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使得文琴的这些招数都没有成效,不过她没有被弄晕倒也算是万幸了。
文琴想要看清来者的容颜,于是准备开灯。
来者上前阻拦,被文琴一转身踢中膝盖。
那人噗通一下跪倒在地,见文琴即将按电灯开关,又急忙站起来,走上去摁住文琴的肩膀将她转过身来。
转过身来的文琴见一拳打在那人胸前。
那人双手将文琴的双手拽住。
文琴于是试图抬脚踢那人的肚子。
那人一侧身,躲过了。
文琴又抬脚想要踢他的下档。
那人似乎有一些乱了,不过还算反应敏捷,马上身体往后一缩,放开了文琴。
“我知道你是谁!别给老娘装了!”文琴对那人喝道。
那人一听,突然冲上来,以极快的速度,一手掐住文琴的脖子,见文琴挣扎得厉害,又改为用双手掐。
就在文琴被勒得憋不住的时候,另一个黑影出现了,他飞跳起来想要给掐住文琴脖子的人来个“灌顶”,没想到那人反应很快,一下子就溜了。
“你没事吧?”那人扶着文琴的肩膀问道。
还没碰到半秒呢,就被文琴袭击了。
幸好他闪得快。要不然应该会很疼吧。
文琴转身立马把灯打开。
两人都用力闭了闭眼,睁开后对视了一下。
“原来刚才那个不是你!”文琴吐了口气,对站在她面前的吴愧说。
吴愧好像没听见文琴说话一样,径直走到文爸爸的书房的房门前。伸手拧了拧门把。
“哼,”文琴苦笑一声,“我就知道你们都对这个房间感兴趣。”她双手交叉胸前,歪着脑袋看着吴愧的背影说。
吴愧把手上戴着的红绳拆下来递给文琴,“这个你戴着,我走了。”说完,他到衣架去拿下自己的外套直接穿上,然后头也不回地走掉。
大门被吴愧快速地打开又用力地关上。
“莫名其妙,大男人一个竟然把一个女人丢在这么危险的地方?”文琴嘟着嘴面对着大门说道。
她环顾了一下四周,突然心里有一些害怕,又有一些伤感:怎么连自己的家都不安全了?照这样下去,以后哪才是能够让自己安心的地方呢?
千寒离开了那个房间,径直去找刘大发几人去了,他把冰屑留在了他们的身上,想要找到他们不是难事。
他知道刘大发几个肯定是要受审的,无论是作为证人还是被冤枉的被告。他当然不希望他们成为被告,他也会尽力不让他们成为被告。有什么办法不让他们成为被告呢?那就是把自己的名声唱响,让天下人都知道,那几个警察是他杀的。所以在临走前,他在房间里放了一朵冰玫瑰,只要人一触碰,玫瑰就会自动碎掉并且融化,并且还用那几个人的血留下了话——洁白需要鲜血来祭奠,其中一抹鲜血还涂在了冰玫瑰上。这样看起来像杀人狂魔多了。
他给几人分别留了一笔钱,那笔钱足够他们请一个比较好的律师的了。
事情很快被传了出去。本来当局想将此事遮盖过去的,因为对犯人以刑逼供,最后却被犯人杀了是一件很不光彩的事情,传出去了一定会让政府的声誉扫地,也会让很多中饱私囊、前途无量的人丢了饭碗。不过当晚千寒在当地又连杀了十个人(4个官员、5个开发商极其下属和一个民工),名单是问阴阳鉴要的。他在每一个作案地点都留下了一朵带血的冰玫瑰和那句话。这使得当局终于坐不住了,下了全城通缉令,最后还下了全国通缉令。
由于跟文琴出来的时候,他易了容,头发的颜色变了,肤色也变了,至于五官呢,眼睛由原来的似笑非笑桃花眼变成了长长的丹凤眼,鼻子也变高了,嘴唇变薄了。所以他恢复自己原来的样子,再换件衣服,就再也没有人认得他了。
一时间,他的画像满街都是,有一些激进的人称他是个英雄,因为他杀了该杀的人,那些官员和开发商都活该,不过不能理解为何要杀那个民工;有一些比较中立和理性的觉得这些人虽作恶,但应由法律来制裁,况且那个民工很有可能只是普通民众;另外一些则觉得事不关己,不凑热闹。他偶尔也当一回观众,挤在人群里看自己的画像,一边看一边嘻嘻傻笑,然后在心里赞一句画的不错。
满城找他的,除了警察,还有一些邪恶组织,比如当地的黑社会。千寒知道,自己必须时不时地杀人,才能够让一些无辜的人免遭冤枉。一想到这个,他就会皱眉:这帮蝼蚁,总是把人往绝路上逼。
文琴对于自己的身世真的不太在乎,以前她想要成为英雄,现在有这个机会了,反倒希望自己过得平淡。而且近几天千寒又似乎没有逼自己往外跑的意思,所以她一天到晚地在家里晃着,偶尔看看书、拉拉筋、打打拳、跳跳舞什么的,她小时候学过芭蕾,后来因为觉得芭蕾跟superwoman没什么关系,所以就放弃了。
多焱他们到达乌鲁木齐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的晌午,虽然可爱的太阳温柔地烘晒着大地,但仍然让人感到身体如刀割般干冷,就差像大地一样皲裂了。
文夕和母亲都缩着身体,多焱显得镇定很多。
他们打的到之前预定房间的酒店,准备休息一晚再做新的打算。
茫茫人海,巍峨天山,该怎么去寻找那个传说中的实验室呢?对于他们来说,乌鲁木齐不过是个中转站,接下来要去的地方必定险象环生。之所以选择现在乌鲁木齐下榻,是因为文母当年就是在这里被绑架到那个实验室的。
文夕曾经跟一些考古爱好者一起在天山和罗布泊一带活动过,不过当时那群考古爱好者们中的大多数对于地质研究更感兴趣,并且都没有深入冒险的胆量,大家在罗布泊外围转了一圈,就各自离散了。
第二天一早,他们整装待发,要去哪儿呢?昨晚他们愣是没有研究出目的地来,倒不是心中没有目的地,只是想要去的地方太危险,而且不一定能够从中找到那个实验室。文夕的顾虑在于他的母亲,而多焱的顾虑在于文夕的态度。
“这个空间里仅存的与愈水痕有关的地方就是那里,我无法要求你放下你的忧虑,但我始终在等你做出那个决定。”多焱一边收拾行李一边对正在披上军用大衣外套的文夕说。
文夕冷了一下,披上围巾后径直夺过行李,二话不说地出门,在酒店一楼的大堂里,他的母亲正在等着他。
等到多焱下来的时候,正在喝着热可可的文夕将另一杯热可可递给多焱,将他拉到一边去,说道:“我们去那里吧。吃完早餐就出发。”
多焱将热可可一饮而尽,看了一眼正对他微笑的文母,便转头对文夕轻轻地点了点头。
冬季的楼兰遗址绝对是一片魔鬼地域,先不说生存环境恶劣让人望而却步,恐怕你一路想要靠近它也会有好心人阻挠,所以他们不单止要跟恶劣的环境作战,又要跟阻挠他们前进的好心人作战。
他们准备齐全了大半个月的干粮和水,租了辆越野车,在车顶绑了个大水箱,为预防不测,车内也放了不少瓶装水。个个神色严峻地出发去楼兰。
这绝对是一场艰辛的旅程。哪怕有多焱在。
“如果能够找到一位十分了解沙漠气候的人结伴就好了。”文夕心想。
可在这个季节里,谁敢跟他们同行?
他们的车辆行驶出城镇,越来越靠近沙漠。在最靠近楼兰的城镇边缘生起了篝火。由于有车,他们想吃完东西便回车里休息,所以没有搭起帐篷,这样做也是为了省时间。几人团团围坐在篝火前,用正烤着半只路上向当地人买的羊,多焱也要跟着吃,因为在第三空间找不到更适合他的高能食材,只好将就着补充这些,况且他曾经也是第三空间的人,尝尝久违的烤羊肉也不错。他们在烤之前做了一些简单的处理,只要是把盐和酱油、蜜饯涂在羊肉上,还能够讲究食材的味道,证明他们现在的处境还不算艰难或者说他们的心态还算好。
就在文夕身后不远处的沙漠,此刻已经开始张牙舞爪起来,风时不时吹起沙浪,将沙粒撒到文夕他们身上。文夕啃着带沙尘的羊肉,笑着说:“还真是第一次吃沙子烤羊肉,嗯,味道还不错。”
文母拍了拍他的头,笑了。
天空彻底地暗了下来,仿佛是转眼间的事情。
文夕和妈妈回到车内休息,一天的奔劳让他们很快入眠。
而多焱一个人呆呆地坐在车顶,把脚伸到车窗处,抬头仰望着近乎一片漆黑的夜空,几颗幽冷的寒星发出凌厉的白光。多焱的左边身体,皮肤爬满了红色的脉络,像是被烧融的铝片,感觉快要滴落下来又被外层的氧化膜包裹着。脉络从心口往四肢长,最后从脖子根长到左脸上、额头上。当它试图爬进多焱的眼睛的时候,多焱眼睛中生出的一条小火舌将其逼退。他扭头看向沙丘那边的天空,发现一团滚滚黑烟向自己这边涌来,黑烟像是一条脑满肠肥的大虫字,时而上浮时而下沉地前进着,由于是在高远的上空,因它刮起的风还不致于引起沙尘暴。
那团黑烟很快就挪到了多焱头顶的上空,多焱看着它,用剑指划出火焰,飞向那团黑烟,而他皮肤上的像树枝状的脉络也跟着跑了出来,像是一根燃烧着的藤蔓,嗖地一声跟着火焰串到了黑烟身旁,黑烟见势不妙,想溜之大吉,可为时已晚,藤蔓已经将它死死捆绑住,如论它怎么试图挣脱都挣不开,正当它被藤蔓勒得快要彻底消散的时候,一缕小小的像游蛇一样的黑烟从那一大团黑烟中溜了出来,而在黑烟消散的渐渐同时,一大片美丽的紫蓝色的薄雾状的云朵慢慢地现出它的形状。
在黑烟消散之后,火藤蔓也熄灭了,变成炭灰掉落到地面和车顶上。
“还是让你逃了。”多焱淡淡地说道。
他盘着双腿坐着,然后保持着这个姿势让身体迅速上升到紫蓝色云朵处,薄雾状的云朵开始渐渐向他靠拢,并绕着他缓慢地旋转。云朵中漂浮着紫色和蓝色的微小颗粒,肉眼几乎很难辨认。
“你怎么漂到了这里来?”多焱看着那些微小的颗粒,然后在空中画了一个圈,一条时空隧道出现了,往里看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紫色和蓝色的微小粒子,以极快的速度在运动着,像是一条倾泻而下的瀑布,又像是波涛汹涌的江海。
“回去吧。”多焱一只手扶着时空隧道口,另一只手招呼着云朵进去时空隧道。
云朵像是一条河一样涌进了时光,最终隧道口关闭,一切恢复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