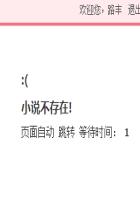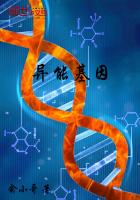十月如约而来。
那天,天刚亮,六指跟阿娘就拎着收拾好的包袱来到了槐树下。今天就是出发的日子,大家都一脸悲戚,拿着大大小小的包裹,有的甚至抱着自家的鸡,牵着猪牛,忐忑不安地等待着。
六指看着熟悉的村子,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九个年头,如今要走了,才知道有多么不舍,努力眨了眨眼睛,不让泪水流出来。
天光大亮的时候,一小队士兵来了,领头的象征性地讲了几句话,无非就是要听话不惹麻烦之类,就押着村里余下的百来口老弱妇孺朝大路上赶去。
大路上已经有好几拨路人,估摸就是附近村子的人,无一例外地向南方迁去。
每一个村子外围都有一小队兵驱赶,就像是赶鸡赶鸭一般,卑贱的村民被驱使着离开家乡,走向不知名的所在。
南疆,六指听说过,那个地方是大齐朝最偏远的地方,尽是深山,毒虫野兽出没,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瘴气笼罩,人在那样恶劣的环境下都活不了多长。何秀才曾说:“幽宁还算好的,要是在甫北,那儿尽是发配过去的犯人,估计一村人更活不了几个。”不知这是幸,还是不幸。
六指一边想着,一边跟着队伍前进。
十月的天,太阳没那么烈了,可还是有些热,队伍每天都要走上四十里,除了中午能休息一个时辰外,余下的时间都被士兵们驱赶着前进,稍有落后,就会被呵斥,甚至鞭打。
头几天还好,大家都能跟上队伍,可连日的疲惫,让孱弱的老人和年幼的孩子渐渐走不动了,落在后面的人越来越多,士兵的打骂声几乎不再间断。
到了第十天第一个走不动的老人倒下了,任士兵怎么抽打,他也没有起来,他死了。
六指眼睁睁看着死去的老人,第一次发现死亡原来这么近,而他却无能为力。
士兵把老人的尸体仍在了路边,骨瘦如柴的老人只剩下了一张皮,每一路过的人都能看见,死亡的恐慌盘旋在每一个人心里。
有了第一个就会有第二个,就像中了诅咒般,不停地有人死去,路边留下的尸体也越来越多。六指不知道他们的灵魂是会上天堂,还是下地狱,他只知道,尸体会成为野兽的口粮,除了白骨,什么也不会剩下。因为队伍的最后,远远地跟了一群豺狗,总是在夜里发出凄厉的嚎叫,而头顶上的那群乌鸦,也从来没有散去过。
悲沧弥漫在心头,他觉得自己心里压抑着什么,然而,除了难受,他依旧什么也做不了。
他没有多余的口粮去接济饥饿的人,也没有多余的力气去搀扶年迈的老人,更没有办法去医治生病的人。他跟阿娘每天只能在中午啃上一个杂粮窝头,而这个窝头就是一天的口粮,余下的时间里就只能靠凉水去填饱肚子。
路远比想象的要长,饥饿却比预计的来得早。
沉重的赋税几乎榨干了村民们的粮食,剩下的那么一点点早已经不起消耗。每个人都不敢吃饱,因为不知道路还有多长,总想着为明天留一口,可留着留着,自己就倒下了,再也没有起来。
这时候,就会有其他人不顾一切地扑上去,抢走剩下的那口干粮,可怜又可悲。
每天队伍里就会有不少人死去,也会有不少人渐渐掉落在队尾,而队尾的人最后总是消失不见。
六指的村子在老村长的带领下缓慢地移动,这个头发都已花白的老人总是极力想带走每一个村民,事实总是让他失望,他的头发更白了。
两个月后,队伍到了澜州地界。
澜州跟雍州不一样,山多,路窄,空气中总是有种闷湿的感觉。为了加紧赶路,士兵们驱赶着人们走山间小路,这也加大了体力的消耗。
别的村六指不知道,可是自己的村子,出发时的一百三十六个人,到现在只剩下了九十八个。包括他所认识的村里最长寿的已经70的李大爷,还有流着鼻涕王二家的小闺女,他们都不在了。
老村长也病了一场,六指以为他也熬不过去的时候,老村长却奇迹般地挺了过来。后来休息的时候,老村长对他们这些孩子说:“不把你们送到地方,我闭不上眼,你们是村子的未来,一定要活下去,哪怕当牛做马。”孩子们都没有说话,不过,在心里都暗暗地对自己说:“活下去!”
这天,天下着细雨,队伍没有停下来,照常前进,路很滑,山道崎岖,一步一个泥印,任士兵再三催促,队伍也快不起来。
六指一手拄着木棍,一手拉着阿娘,阿娘天天背着包袱,已是疲惫不堪,又心疼六指,不肯让他背,一路咬着牙坚持。六指无奈,只得扶着,尽一点力。
好容易翻过山头,接下来的下坡路却更难走,路本就窄,旁边还是高高的悬崖,泥泞的路面站不住脚,一不小心就可能滑下悬崖,六指走得更加小心翼翼。
突然,前面的队伍里传来一声尖叫,人群喧闹起来。六指赶到前面一看,何秀才的娘子何方氏正趴在路边大哭,而路边有些泥土滑下去的痕迹。
有人掉下去了!六指心里一紧。旁边几个妇人正朝下面张望,可是雾蒙蒙一片,根本看不清楚。
六指赶紧问道:“谁掉下去了?”
一个妇人抹着泪道:“何秀才的小妞子没踩稳,一溜就下去了,也不知道死活”
六指顾不上安慰方氏,赶紧朝着悬崖下大喊:“妞子,妞子!”其他人也反应过来,跟着一起朝悬崖下喊。
好一会,才听到一个微弱带着哭腔的声音传来:“阿娘,阿娘!”
还活着,大家都高兴起来,方氏也抹了一把泪朝众人跪下,“求大家救救我的妞子,以后当牛做马我报答大家……”
大家手忙脚乱的把方氏扶起来,边安慰她边想办法。
这一耽搁,路上的行进速度就更慢了,路本不宽,几个人堵在路边,后面的人就没法走了。一士兵发现了这一情况,快步挤过来,鞭子一挥,朝最近的陈婶就抽了过去,骂骂咧咧到:“还不快走,堵在路上,找死!”
鞭子重重地抽在陈婶身上,陈婶一个趔趄,倒在了地上,方氏赶紧朝士兵跪下:“大哥,我家娃掉下去了,还活着,求你行行好,给点时间,我们救她上来。”
士兵不为所动:“掉下去就掉下去了,还少一个累赘,娘的,今天赶路就够倒霉了,你们还在这磨蹭,再不走老子把你们都推下去。”
说着又举起鞭子,朝方氏抽去。
看着蛮不讲理的士兵,六指觉得胸腔里那团火又烧了起来,愤怒冲上头,一个箭步跨过去,手一伸,竟稳稳抓住了鞭子。
士兵吃了一惊,没料到居然有人敢截住鞭子,恼羞成怒道:“小兔崽子,找死。”说完,猛力把鞭子往回拉。
岂料,鞭子纹丝不动,士兵大惊失色,朝六指看去,少年眉间隐隐有青气闪动,眼神冰冷,无端让人害怕,而紧握鞭子右手上,多出的一指格外显眼。
“啊!”士兵吓得松开鞭子,跌坐在地上。
恰在这时,老村长气喘嘘嘘地赶到,见状赶紧扶起地上的士兵,士兵吃了一吓,心内不安,再看六指时,跟平常小孩也没有两样。难道眼花了?士兵暗自嘀咕。六指娘也赶紧把六指拉到怀里,六指愣了会神,不明白刚才自己是怎么了。
士兵被扶起来时,浑身泥泞,有些恼怒,觉得失了颜面,抢过鞭子,一鞭抽向六指,老村长反应快,转身挡在身前,鞭子“啪”一声,结结实实抽在了他身上。“村长”周围人都担心地叫了起来,愤怒地看着士兵,六指也挣扎着想从阿娘怀里冲出去。
老村长忍着痛直起了身子,摆摆手制止了大家的声音,方才对士兵赔笑道:“长官,孩子不懂事,您消消气,给点时间,我们把人救上来,不会耽搁很久。”
这一鞭下去出了气,又见老村长给面子,再看周围人恨不得吃掉他的眼神,士兵有些怯了,不想惹了众怒,怕激起民变,就讪讪道:“给你们半个时辰,搞快点!”说完,拍拍屁股朝后面走去。
众人顾不上再跟他计较,都努力地想办法救人,还是老村长想出了一个折。让大家把绳索、被单、衣服等接在一起,做成了一根长绳,一头拴在树上,再派一个半大小子系着绳子另一头下去查看。绳子没放多长,小子就喊停,说是人找到了。一会功夫,上边的人齐心协力把两人给拉了上来。
原来崖下有个窄窄的平台,又长了几棵树,把小妞子给拦住了,除了擦伤,倒也没什么大碍,只是吓得不行。
人救了上来,方氏领着小妞子给大家一一磕头,众人扶起她俩,各自散去,又开始赶路。
老村长有伤,示意大家先走,让六指娘俩跟在一边,慢吞吞往前走,好一会才道:“六指娘,孩子是怎么回事?都两次了,该不是中了邪吧?”
“我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从小跟村里的孩子一样,也没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六指娘拢了拢额前的碎发,也很是不解。
“六指,最近有没有遇到过不一般的人或者事?”老村长“啪嗒”吸了一口旱烟。
六指仔细想了想,才道:“许爷爷,我没碰到过什么特别的东西,我也不知道咋回事,就是有时候挺生气的,然后就觉得心里有团火在烧,不受控制似的。”
老村长眯了眯眼,看了看远处:“孩子,以后要控制住自己的怒气,变得强大是好事,但现在你还不能掌控,会带来祸害的。”
“嗯。”六指懂事地点了点头。
“走吧,孩子。”老村长带头朝前面大步走去。
雨依旧在下,虽然不大,却没有要停的意思,接连几天,都是在泥水里泡着。据说,这是澜州的雨季,雨会不停歇地下到来年开春。所有人都无法避免地全身湿透,一步一滑地摔着走,手脚都是伤,到处都是孩子的哭声。晚上也只能搭个简易的窝棚,勉强烤烤火,大家穿着半湿的衣服挤在一起取暖。
士兵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一路上骂骂咧咧,抱怨这样的苦差,对村民们也就更加苛刻,动辄打骂,不管死活。
疲劳、饥饿、寒冷迅速夺去鲜活的生命,队伍人口锐减。
翻过澜州,过了平洲,终于在一月底,赶在年节前到了幽宁。
而此时,六指村里只剩下了最后的六十五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