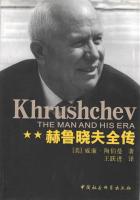一个原本背负着杀戮与血腥的人,此刻周身却散发出一种凛然正气。归一楼士子,均被辰逸展现出如此矛盾且对立的风华倾倒。
只有子兮,绝美容颜上,是与平日里无异的不拘笑意。
“所谓‘显学’,乃世人评说。巨子当真要听子兮这一家之言吗?”
辰逸微愣,继而垂眸道:“在下既上了这论战台,自是要听听先生对我墨家的评判。”
“若单单以学术论,墨家自是当得起这两字。”几乎是在辰逸最后一字还未说出之时,子兮便接口道。
“那么,若论我墨家弟子言行又如何?”
子兮指间轻叩起书案,取下腰间酒囊,狠灌一口,闭目思忖须臾,才缓缓睁开双眸,再度开口。
“为民除暴、扶弱御强!墨家壮士,乃当今侠道之最,当之无愧。”辰逸远望子兮因为饮酒而变得幽暗的粲然双眸,一如当日那般再次迷失在光亮深处,忘记了开口。
然而须臾之后,子兮深邃飘渺的眉眼,随着她轻曼舒缓的语气,渐渐清晰了起来。
“自古大道不两立!巨子因行侠道之举,故而深得民心。但子兮,修习的却是王道、霸道之术,是以纵然心有感佩,却不能认可!”
便是这样淡漠一句,辰逸心中却如被重物狠狠砸在了心底最脆弱的一处地方。
“墨家讲兼爱非攻,自然不会认同。”
“你我道不同,不相为谋!......”
整整十年,他忘记不了当日那些因为战争而死去的人,成山堆聚的尸骨;忘记不了他抚出安魂琴音的内心深处,对统治者的厌恶与痛恨;忘记不了阵阵尸臭间,那股轻而易举便平复了他心底不忿的淡淡酒香;忘记不了少女旖旎如水波的眼眸;以及那与她年龄极为不相称的狂悖与清傲。
同样的意思,说自同一人,然而他的心境,却在十年后,骤然被击打的万分凌乱。
子兮看着男子顿失笑意的如画容颜,自然不知此刻的男子已是陷入心魔而难以自控。然而对手在此刻失神,她只好扬唇轻唤。
“巨子......”
“嗯?”一声后,辰逸慌忙收拾好紊乱的心神,牵强一笑,歉意躬身,“逸失态了,先生勿怪。”
子兮也未深究这个墨家巨子何以突然间有些神色仓皇,遂展颜道:“巨子没事就好。”
抬手一比,袖口滞在虚空处,辰逸面上又复方才笑意,“先生请继续。”
子兮见辰逸恢复常态,一笑颔首后,表情顷刻凝重,继续道:“而今华夏崩离,内有诸侯争伐,外有蛮夷暴乱。墨家弟子侠义之举,对外无益;对内,只是使本已纷乱的中原更加动荡。便说凨国太子姬光一事,巨子看似为民除暴,实则却动摇了原本有可能奠定华夏一统的第一大强国的国本。国本一旦被动摇,国人又岂会安生?照实说,姬光太子也算得上极具魄力的王储,其人虽则崇尚武力而好杀戮,但对凨国国人而言,却相对而言保障了他们生存的安定。巨子以自己喜好,断定旁人生死,不知可曾想过若下一位王储若比姬光还好杀戮,应当如何?难道继续杀之?直到凨王觅的一位才具不及姬光、但却从善亲民的王储当国?果真如此,若遭受他国欺辱,这样只是亲善的王储该当如何应对?这些,巨子在击杀姬光太子之时,可有想过?”
辰逸默默,长久沉思,终是坦率道:“先生所言,逸的确未曾想过。”
“路遇不平,拔剑相助,是为侠。轻社稷而重民生,是为侠义。但巨子可知,侠义,并非大义,亦并非值得人人称颂!”
辰逸俯身长长一拜,似笑非笑变得谨然慎重,“先生所说之大义为何?还请赐教了......”
“所谓大义者,当无国界之分,将天下国人一体视之,弱国如是,强国亦如是;当无强弱之别,不因弱者悯、不因强者恶;当不已一人之准则而妄断杀戮,不已一人之喜好而评判善恶。”
“彩——”
“彩——”
“彩——”
紧凑连贯的三声长彩,是一楼各派别学子内心由衷的赞叹!
如此昂扬大义的阐述,当真空前绝后之亘古奇闻,如何当不起这震耳欲聋的三声喝彩?
“先生所述之大义,逸万分拜服!”诚然一拜后,起身端坐,“但观当今天下,虽有诸子百家,只怕能做到此等‘大义’的学派,还尚未现世矣!”
“儒学看似大任,实则不仁;墨家看似大义,实则非义;道家、阴阳家,只知上窥天意,下观阴阳;兵、农两家只管用兵及田事;名家诡辩自不必说;医家救人,却不知如何救世;纵横家巧舌如簧,更非大义所托......”
不理会台下众人逐一色变,子兮继续道:“能担此重任者,百家中唯我法家!”
“法家?”
学子们交头接耳,议论哄闹了起来。
辰逸却在台上清雅一笑,道:“先生先攻儒墨,后抨百家。便是要引出法家吗?”
子兮倒也不否认,语气顿挫有秩,“不错,所谓大仁不仁者,法家如是!助君主一天下者,非法家不能!”
“那在下倒也想听一听,向来‘浓重典刑、刻薄寡恩’的法家,究竟是如何‘大仁不仁’,又是如何能助得贤君‘一天下’的。”台下士子显然不满子兮这般将百家学说抨击的一无是处,于是出言讥讽道。
子兮还未作答,台下又传来众士子得齐声附和,“愿闻先生高论——”
听着绕在楼中的悠长尾音,子兮倏然起身,以论战台为核心,行过一圈后对着台下学子利落拱手,停于中央。
举止虽依旧如前潇洒,但轻缓的声音却蓦地多了几分霸气,“如兮方才所言!今天下之势,内有诸侯纷乱,使我华夏分崩离析;外有蛮夷侵扰,对我中原虎视眈眈!兮窃以为,如此内外忧困之时,欲攘外则必先安其内。而安内,则必用重典。惟其如此,方可使六合归一,重兴华夏。届时中原,再无国之纷争、战祸之苦,国人便可真正的休养生息!蛮夷亦不敢动我分毫!”
“敢问先生,何谓重典?”台下又一士子铿然发问。
子兮沉着了神色,道:“重典,就是变法!通过深彻的变法,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使一国大出、五国俱灭,从而一天下!”
“照先生此说,当今第一大国——凨国,可会大出天下?”
“凨国虽在六国中率先称王,但观现下,还无此实力!”子兮断下一语,自知对方要问因由,便稍作停顿后,道:“凨国法制不全、国人思想陈旧、老氏族与奴隶之间的矛盾尚存,故而无法凝聚民心民力!”
向来没有出声的兵家士子,这一次也明显不服,自书案前霍然站起,刀凿的眉眼冷峻严厉,气势迫人,“先生觉得变法之功,与兵事相比,孰轻孰重?凨国殇君座下苍龙骑,闻名宇内。既有此等强兵利器在手,凨国何以不能大出天下?难道当真要靠你变法不成?”
子兮淡淡一笑,从容问道:“先生是兵家?”
健壮冷酷的男子手腕一抬,拱手道:“在下兵家英无越!”
英无越,但凡世上所存之兵法,无一不能倒背如流。其祖上,历代修习兵法,皆是举世闻名的兵家大才。其父英烈,更是博采众长著书一部流传至今,此兵书便是如今修习兵道之人必读的《英氏兵法》。
子兮虽不喜兵道,但自小在其父的耳濡目染之下,对此人倒也略知一二。
于是拱手道,“足下虽熟读兵书,却从无调兵遣将之阅历。纸上谈兵,又如何能知兵事与国事之牵涉?”
“在下但闻其详!”
子兮淡然悠远的笑意带着几分飘渺的味道,语气却也不由加重了几分,“兮有幸曾认识一兵家奇才,他告诉兮——世人对战场之胜败的定义,在于将帅对战争的全局方略、在于战士的素质和修养、在于君主能否真正做到对将帅的用人不疑、以及后方军需辎重是否充足等等。但此人觉得,上述这些只是表现,若要战无不胜,真正关键的,是国家庙堂是否清明、安定......”
英无越黝黑的面容,堆起浓浓的嘲意,“此人也称得上奇吗?不谈兵法、未提布阵,也敢自称兵家?”
子兮深深一笑,不答反问,“足下觉得惟有善于兵法布阵之人才能自称为兵家?”
“那是自然!”
“子兮一问,望足下指教。”
“先生只管问便是。”英无越意气满满,视台上风姿超凡的女子如无物。
子兮倒也不与他计较,而是敛眉一瞬,曼声问道:“敢问足下,朝堂动荡、庙堂不稳,国人无衣、无食,谈何养兵?无兵可养,又谈何交战?战场壮士皆有父母妻儿,若知自己亲人饱受煎熬,能否心无杂念上阵抗敌,为国家抛头颅、洒热血?”
“这......”英无越讪讪一字,便再没了下文。
子兮一反常态,变得有些咄咄逼人,“足下只知兵法,可知上阵杀敌的人心中想法?世人皆有趋利避害之本性,他们牺牲奉献,沙场赴死,何利之有?又凭何不顾自身性命?真正让他们如此坦然超脱生死的,便是家人!六国为了扩大领土、攻城夺地。将士们只有用自己的生命来保卫国土,才能保住自己的家!足下自诩兵家,却连麾下将士心理都摸不透,也配统摄三军吗?”
面对子兮激烈的质问,英无越顿觉面上火烧一般滚烫热辣。幸而他面色本来就黑,众人倒也无法看出他不必遮掩的惭愧。
然而子兮却仍未有停下来的意思,匆匆一瞥英无越,明锐无比、掷地有声的话语直逼霄汉。
“当今乱世,欲一天下者,战乃大道!战胜——则可摄令诸侯,战败——则有亡国之祸!何以令战无一不胜?兵之勇?将之才?窃以为不足也。盖因兵有勇、将有才而国人疲弱,将士之亲食无饱而衣无足,将士与闻,何以戮力齐心、鏖战沙场、志决生死?是以,富民乃强兵之根基,民不富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国何以兴?此乃变法之功与兵事之牵涉!”
“法家子兮,彩——”
没有理会众人的喝彩,子兮昂昂继续道:“何以富民?惟有变法!惟有从根本上废除景天子留下来的恶习,彻底推翻腐朽的守旧思想。针对国家积贫积弱的现象进行通盘改革,从而使国力民力迅速统一,方有机会大出天下!”
“彩——”
“人性之恶,必待师法而后正!世人评价我法家是‘重典刑,寡恩欲’。却不知明正典刑,是为以刑去刑,以恶止恶!刻薄寡恩,是因我变法弟子,极心为公,绝无二虑!”
那一刻,整个归一楼里,惟听得子兮赳赳话语在空中漫漫回旋。台上瘦弱单薄的女子,此刻稳重如万仞险峰。那绝世独立的飒爽风姿,那睥睨天下清艳眉眼,无一不昭示着她孤高雄浑的气度!那样无与伦比的厚重,使人再一次忘却,这是一场有关诸子百家的辩和论战;再一次忘却,台上冠绝天下的女子,曾用淡漠的嘲讽,将他们逼的哑口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