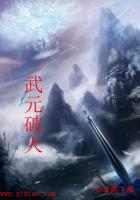面对子兮如此直言不讳的激烈言辞,颜荀平静如水的面容终于泛起了涟漪,虽然那女子所说的每一个理据,他似乎都辩无可辫,然而,却并未打算如此轻易放弃。
颜旬向来彰显名士风范,然而此刻,也不由带着五分肃然。
“先生将我儒家说的一无是处,是否太过以偏概全了?儒家思想既被视为正统,便一定有它成为正统的理由。”
“颜子要听理由?兮给你一个!”子兮意气风发回身落座,莞尔看着颜荀,“儒家之所以被成为正统,不过是诸侯国君想要掩饰自己不仁的本性而已。儒学创世,基于天子威严尚存,诸侯畏惧尚在之时。当是时,中原各诸侯国发动征战,是为取得天子认可,成为霸主而多取贡赋。所以,孔子周游列国,说服各国君主捍卫天子,恪守礼制,继而得到君主认可。而之所以认可,并非他们没有取天子而代之的野心,而是心有所惧。时移世易,当今天下大争,诸侯野心昭昭,便更需将儒学奉为圭臬,欲盖弥彰他们本身对权力的欲望。只有这样大肆宣扬仁义,才不致被其余国家以‘不仁’的理由而共同讨伐!”
“先生一家之言,似乎很难让人信服。”颜荀自然不认同子兮的见解和所陈述的理由。
子兮可悲又可叹的看了一眼执拗到骨子里的颜荀,道:“颜子且看当今天下,哪一位诸侯用你儒家学术治国?又有哪一位诸侯真正做到了‘仁义’二字?”
那一刻,颜荀沉默了。
然而子兮的话语却仍未有半分要停下来的意思。
“六大战国发动连年征战,国人战死不计其数,何来‘仁’?诸侯之间相互攻伐,何来‘义’?
十年前六国合力灭景,天子自戕,何来‘忠’?六国反复无常,时而互为盟友,时而互成仇敌,又何来‘信’?尊儒学而又与儒学教义背道而驰,因由何在,颜子可有想过?并非在于你儒家一无是处,而在于,儒学根本不适合当今天下的局势。”
“当今天下的局势?”颜荀喃喃重复。
“不错,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景朝覆灭之后,中原分而化之,形成六大战国。然而六大战国即将要面对的,便是周而复始的天下一统。每一个国家的君主,要的都不是国人百姓的歌功颂德,而是要成就自己的丰功伟绩。儒家,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其存在的价值,只是为了替国君遮掩他们昭昭天地之间的野心而已。”
颜荀那颗僵硬和骄傲的名士头颅,终于在众人面前挫败不堪的垂了下去。他一直以自己能修习儒家显学而振奋不已,亦希望有朝一日能被某国君主赋予执掌公器的权力,继而创建一个美好的国度。然而,今日,被子兮一席深彻的剖析之后,他忽而觉得自己这种幻想,是多么的幼稚!他自幼便无比向往且深以为傲的学派,在当今世间竟是以这样的价值而存在着,让他觉得自己可怜又可笑。
外表越是与世无争的人,内心便越是难以承受住任何打击。曾经以为自己不争,是因为无人能与之争!然而在面对那个有着冠绝天下容颜的女子一番质问之后,他的心志,终于彻底的崩塌与毁灭了。她反问他的每一句,都如同一把无坚不摧的利刃,那么强而有力地命中他的要害;她每一个凭据的分析,都那般头头是道,让他连自欺欺人的念头也无。
既已如此,自己还有什么资格站在她的身前,和她继续大谈治国、治世?
一场辩和,使他犹如隔世,犹如历经沧桑之变幻、看透岁月之变迁。行尸一般缓缓而起,跌跌撞撞的下了那座象征着荣誉与身份得高台,他忽而想再看一看那女子。将她牢牢地刻在心里。于是回身,白衣女子如同九天下的谪仙,高高在上,气质轻洒不拘。
那一刻,她的脸上竟也敛去了笑意,只颦眉带着几分沉重和深思。
她似乎感觉到他也在注视着她,与他目光在半空中相撞。却是眸若秋水,波光粼粼,没有得胜之后的蔑视、没有对他失败的可怜悲悯、有的只是一种激赏和鼓励。
或许,她赞赏他,没有如同任师叔那般没有风度地一味拘泥成败,懂得进退吧?然而那其中暗含的鼓励,又是为何呢?
他神飞天外般在台下杵立良久,丝毫没有注意到周遭学子的窃窃私语。突然间,脑中灵光仓皇闪过,他,似乎有些懂得了。
迈不开步子的双腿,陡然有了力量,在众人复杂难辨的神色中,昂扬走出了归一楼。
回眸,再望一眼让他从未感受到如此挫败的楼宇,归一楼三个大字流转着灿灿金光。
他对着归一楼的方向,一扫面上灰败的颓色,双拳紧紧蜷在一起,泛白的指节发出轻响。
“子兮,你是在暗示我,并非败在你手,而是败在这个时局之下的吗?那么,今日之败,我一定铭记于心!等到天下一统,我定会为儒家一雪今日之耻!”
颜荀离开了众人的视线,楼上不知是何人带头,率先击掌而赞。于是,沉闷萧索的归一楼里,再一次响起了排山倒海般成片的呼啸。
百里岐从旁捻须颔首,若有所思。
如浪的赞好声中,温温如玉的男子缓步向论战台而来。
着一身墨色长袍,腰间雪色束腰,上坠嵌着秋兰图案色泽莹润得墨色玉石。两鬓边几缕发丝用丝带轻束,其余却柔柔披散与身后。
如画的容颜,勾勒出温文尔雅;紫色星眸似笑非笑,却是沉沉一片深邃。
如此风姿飘逸、气质高华的男子,一出场,便毫不费力的压下众人的声浪。
骤然恢复安静的归一楼里,惟有子兮看见,那道足以令山河日月顿失颜色的目光。
微微回顾间,他已站于她案前,弯腰促狭而笑,用只有子兮能听得到的声音说:“一别十年,我竟未料到再次相见,却是在这论战台前。”
子兮似是而非带着深深笑意,语气却掺着揶揄,“既注定相遇,又何需计较是在这‘论战台前’,或是乡野之处?”
男子起身,眯眼,好奇道:“你怎知是我?”他问的,是在凨国与她在山谷偶遇之事。他以为她无从知晓,不成想她却早已料到。
“本只是猜测而已,但观巨子表情,怕是不幸被兮猜中了!”
——墨家巨子辰逸,当世七大公子之一,其人如珠玉,擅音律,以琴音杀人于无形!
子兮之所以有此推测,是因为当日山谷中欲睡未睡之际,是真切听到一曲琴音的。后来她寻找水源之时发现的新鲜足迹,证明并非是她产生的幻觉,而是谷中确实先她之前便有人在此。当时,她也并未怀疑此人便是墨家巨子辰逸,及至后来还未走出凨国国界,便传来凨太子殁了的消息,在结合国人绘声绘色讲述着凨太子临死前的异状,子兮才冒出了这样一个念头。
谁最憎恶将人命视为草芥的当权者?只有一直以政侠自居的墨家!
又有谁可以在不动声色地击杀完一国诸君之后,全身而退?只有那个看似温润无害,实则将杀机尽藏与琴中的墨家巨子!
想到此处,子兮不由认真打量起眼前俊美如玉的男子,时光倒流回当年尸体成山的墨西战场。当年的少年,不似今日这般举止雅然温润,一双令人过目难忘的紫色冷眸亦不似今日这般透着邪佞与机心。或许,因为如今的他,已然强大到能操控旁人性命,所以才这般肆无忌惮——明知凨国王室遣派死士在六国发出暗杀令,他却仍然明目张胆地前来锦国参加春日辩和。
单凭这样的胆识,足以令人胆战心惊。
促狭的笑意一闪而过,他朗身坐定,令人见之忘俗的容颜堆出与子兮恍如初见的神色,“先生高论,振聋发聩。逸虽不才,也特来讨教一二。”
子兮莞尔,抬手道,“若子兮猜得不错,足下是想以我之矛攻我之盾?”
如此聪慧通透的女子,果然举世无双。
辰逸轻笑,没有否认,也没有被人识破先机的恼怒与尴尬。
“先生说,儒家民心向背,不知我墨家在先生眼里,又作何说法?”
子兮斟酌须臾,难得带了几分敬意。
“墨家高越!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命鬼、非命、非乐、节用、节葬。无一不从国人利益出发,既立足于民心,自得民心拥护。”
辰逸倒也没料到,一向言辞犀利的女子,对自己所在的派别难得有几分褒奖。但也并未因此而忘记自己上台的目的,于是拱手道:“墨家务实,逸便直言向先生请教,有此民心支持,我墨家思想可否治国、治世?”
说到务实,诸子百家当以法家为最。这便是子兮在辩和上为何没有拘泥礼数,而是句句直抒胸臆。然而对方既已开口,子兮自然没有沉默的道理。
“安邦或可。但要治国、治世,无异于痴人说梦。”
剑眉轻轻一挑,面上纤尘不染的笑意却更深了几分。
“先生可否详述?”
子兮也不客气,当下臻首一点,道:“墨家向来反战,并以保卫弱小之国为使命!举凡大国攻打弱国,墨家弟子必定竭力助其农耕及军事防御,使之不被强国蚕食吞并。对此等国家的国人而言,墨家是救星,是希望!所以崇敬你墨家胜过自己的国君。但是,哪一个国家的当政者希望自己的国家出现这样一个光环远胜于自己的学派?哪一个君主可以容忍你们墨家这般越俎代庖?墨家为何全心全意为国人牺牲奉献,却被弱国当政者视为眼中钉,被反击的强国国君视为肉中刺?归根结底,就是因为你们太得民心,所以与天下主政者的权力、利益相抵触,他们又如能能容你们染指庙堂,威胁主政者至高的威严呢?”
“如此说来,儒墨两大显学不能真正治国、治世的原因,如出一辙?”辰逸轻轻一笑,好似漫不经心般一问。
“不错,儒家思想之所以被视为正统,是因为主政者有所利!墨家只能称其为显学,却不能堂而皇之入主庙堂,是因为主政者有所惧。”
子兮话落,辰逸垂首默然片刻后,目光一凝,炯炯慑人的紫眸注视子兮,温吞缓慢的开口道:“先生一语中的,逸拜服!只是如今天下汹汹,华夏狼烟四起。皆因六大战国国君穷兵黩武,不顾国人死生!墨家弟子,向来视自身功业如无物,视高官显爵若浮云。而之所以存在于这乱世,只是为了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为天下民众做些实事而已。纵然不能治国、治世,却也当得起显学二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