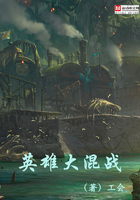景恒走到莫云章的卧房外,干涩的喊了声:“师傅”
“何事?”云章听见景恒的声音,并不意外,情理之中的事。
“师傅,景恒来请罪”
莫云章不出声,片刻之后,推开门便是看见景恒跪在门外,这几天本就是阴沉沉的,这会倒是断断续续的飘着雪片了,书房没有地龙,也没有上火炉······
景恒见云章打开门,抬头看向云章,只见云章负手立在门内,逆着光,面色算是柔和,这让景恒稍稍安心了一点,低下头,“师傅,是我求灼灼教我医理的,请您不要怪她,要罚就罚我吧。”
云章仍是看着外面的雪片,“她可曾偷偷带你取过药庐?”
“没有”
“借了你哪几本医书?”
“《难经》,《神农药草》,《采季治本》,《千金方》。”
这丫头,《千金方》主治妇科,怎么也拿去给景恒看?不由得轻笑一声
师徒无话。
阿奶进院儿的时候便看到的是这样的场景,景恒跪在门外,云章站在门内,师徒无话,云章脸上却还带着浅浅的笑意······
“今年的雪下得格外早了,我瞧着,怕越下越大了”阿奶拎着食盒走了过去,
“是啊,往年的雪十二月才来呢,”莫云章看着阿奶笑道,这些年了,走的走散的散,只剩自己和惠然还没走散,“景恒,你先回去吧。”说着便自己进了屋。
“师傅不肯原谅灼灼与景恒,景恒就不起来”景恒不肯起来,
“管着自己吧,灼灼我自有主张。”云章头也不回。
“可是师傅,我······”还想再说,却见阿奶在旁边朝着他摇了摇头,平时多明白的孩子啊,怎么这个时候犯糊涂?
“回去吧,你师父知道的,哎,这天越来越冷了”这最后一句不知是说给景恒听得,还是说给云章听得,还是说给自己听的。
景恒听出了意思,冲着阿奶一眨眼,用只有他两能听见的声音道了一声谢:“谢谢阿奶。”
这孩子,道的是哪门子谢?代灼灼谢?还是他自己?阿奶浅笑。
关上门,隔绝了外面的风雪。
莫云章坐在炕上,看着惠然将食盒里的点心小菜一一拿出来,就这么盯着桌子看,有些出神,描着梅花的酒瓶落入眼帘,莫云章回了神,“梨花酿?”
“我见你晚膳用的少,便端些点心过来,突然想起前院的梅树下还埋着去年的梨花酿,便取了来。”
“哈哈,知我者惠然也,来来来,陪我喝一杯。”
惠然见云章难得有此雅兴,便也不扭捏,脱了鞋,盘腿坐与云章的对面。也不开口先提灼灼的事,“哎,这混一下就十多年过去了,上次在锦州时行酒喝令也是下着这样的大雪,好似还是不久前的事儿”
听到锦州二字,云章端着酒杯的手不自觉的顿了顿,锦州么?
那时的他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那时的英英还是锦绣年华的少女,那时的司徒翰桢还是视英英为一切的专情之人,那是的惠然还是高贵潇洒的贵族公主,现在呢?都变了······他已是华发早生的糟老头,英英已是黄土盖身的冥冥之人,惠然已是满脸沟壑的老阿奶了,他呢,司徒翰桢呢?如今该是香车宝马,美人在怀吧······想着不由讽刺一笑,这该比戏文里写的还精彩吧!
“是啊,都多少年了?我们都老了?”
“噗,这话搁在锦州那会儿可真不像你会说的,我倒是记得你说你是我们中间的常青树,青春永在,话说回来,这些年你真变了很多。”
“谁又能是不变呢?你看那水中鱼,林中树,一年四季还有个变化,何况是人?你不也变了?”
是啊,又有什么是一层不变的呢?
“这些年说来真要谢谢你,家里家外的操持着”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奇怪?是了,平常夫妻家的的话呢······夫妻?惠然心中讪笑一声。
“哪里就当得你一个谢字,我的命是你救得······西华门之变后固伦公主就死了,我只是你的婢女”婢女?是了,哪里来的夫妻,只是主仆而已。
“你又说笑了,我莫云章可有拿你当婢女相待?你那有时凶起来分明我是你的奴仆”
惠然掩嘴轻笑,云章饮下一杯酒,点点笑意从唇边荡开。
“你准备让灼灼那孩子跪多久?这天冷地寒的,等病了心疼的还不是你?”
“我看你倒是心疼她。”
“你就不心疼?且不说她是英英的女儿,就是平时招人疼的小样,搁谁谁不喜欢?”
想起灼灼调皮时对他挤眉弄眼,犯错时谄媚的献殷勤,莫云章止不住哈哈笑起来,只是下一刻,笑容散去,“只是这孩子没点教训怕是以后要吃亏啊”
“能吃什么亏?给人看了医书就吃亏了?”惠然笑着给他布菜,“我知道,你怕万一这要是本门医术泄露出去,会招来不少麻烦,但你也不要那么悲观,况且这一本《采季治本》也没那么大的内容”
“倒不是怕招来麻烦,该来的总会来。只是景恒这孩子,你是知道的,本来教些医术也无妨,只是皇室中人哪一个是简单的?况且本门医术本就有些另类,解药多,毒药也是多,日后若是善类,这是福,若非善类,只怕这救人的东西便是拿来害人的。”
惠然一怔,勉强笑道,“没那么严重,况且以后不是还有三爷教着么?”
云章默然,看了惠然一眼,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而且,灼灼过年13了”
惠然放下手中的筷子,这搁山下的村里,早的都已经开始说亲了,公子的意思是?“景恒比灼灼大两岁,这孩子自小是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怕是心智早于同龄的孩子。要说这孩子是不错的,只是这身份······公子,你也别想太多,也许只是我们猜测,孩子们天天儿在一起玩,我也没看出一些特别的事儿”
“我记得景恒刚来的时候,两人还相互看着不顺眼,怎么就突然这么好了?”
“这事儿说起来还怪我,前段时间灼灼不小心又拿景恒那孩子刚来时像女娃娃来笑他,你也知道这事儿是景恒心里的一个疙瘩,我就跟灼灼说景恒那孩子打小没有娘亲,一路走来不容易,让她不要欺负他”想起这事儿,惠然还觉得有些好笑,“你猜灼灼那孩子怎么说?她说以后都对他好,一辈子对他好,她哪知一辈子是多久?”
惠然说的轻巧,听得莫云章心里咯噔一会,这怕是不好了,当年他见到英英哭的时候便是想要一辈子对她好,不让她再哭,只是英英这一辈子走得太匆忙。
“只怕万一啊,要不以后尽量让灼灼避开景恒?”
“这样不好,若是弄巧成拙反倒是麻烦,”公子是不是太紧张了点?想着惠然又噗哧笑出声来,“这八字儿还没一撇的事儿呢,你这会子担的哪门子心?再说不是还有子明在么?”
莫云章心里始终隐隐的不安,英英将灼灼托付给我,就不能发生一点点儿的意外!
“你有空担心这个,还不如担心灼灼已经跪了几个时辰了,再跪下去她的关节是否受得了?你瞧外面的雪下得?”说到这个,惠然有些担心,总归是女孩子,万一寒气入体对身体不好。
“算了算了,骂也骂了罚也罚了,你去叫她起来吧,回去用热水多跑一会儿。”
“这会子倒是关心的很了”惠然笑嗔道,下榻,直往书房走去。
惠然其实心里一点不担心,她这边给莫云章送梨花酿,那厢就让子铭领着装着点心和小米粥的食盒去了书房,猜得没错,那孩子应该吃饱喝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