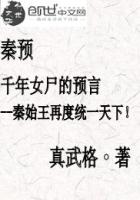阳照在连绵不绝的兵营上,映衬着落雁关,有一种壮烈的美。
我现在走在兵营外围的土地上,因为下了两天雨的缘故,脚下的地面湿滑又松软。兵营的左侧是一个土坡,一条弯曲小道从小坡顶通向兵营,旁边则是茂盛又不太高的树丛。中间散落着战争遗留的残物。
那位大师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手段,昨天夜里,前几日因为冷寒而冻醒多次的我一觉睡到天明。仅管昨夜比前天更冷,身上的薄被也未曾变厚,但我不但没有感觉到冷,反感觉身边有盆炭火一般。
第二天醒来,伸了个懒腰,居然没有感到一点不适。我试着下床,发现除了那些较深的伤口有些疼痛,其它的伤口没有丝毫痛感。这让我对那位一慈的和尚生出些许感激。
经过一夜,屋内的伤兵又死了一个。是昨晚那个哭泣的兵士。我怀着同情深深的看了他一眼,便出了屋子。因为我既将要去不熟悉的远处,我要收拾我的东西。
我没有沿着小道走上坡顶,而是快接近顶时,将身子弯下腰,向左侧钻去。坡顶的植株要比坡底密且高。所以绿色很快将我的身体覆盖。
向前钻了约一百米远,我打量了一下四周,在地面上确定位置,然后用手开始向地下挖了起来。
里面不是我发战争财而私藏的宝贝,也没有什么值钱的物什,不过是我的全部家当罢了。
我现在没有了亲人,参军后,想到自已会战死杀场,我便将一些自已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带在身上。
因为刚埋进不久的缘故,再加雨的渗透,很快便将我所藏的东西取了出来。
埋在土里的是一个很小的箱子,尽管我知道里面的东西不会少一样,但仍旧打开箱子,查看了一遍。
箱子很小,注定能装进去的东西不多,不过三样,第一样是把长命锁。自我出生时便带在身边。带着他是因为这是爹妈留给我的。第二样是些铜钱,除了自已打柴积攒下的还有一部份是军饷。钱虽不多,也不愿装在身上。除了不想让自已的血命钱在自已死后便宜那些同僚外,还会在内心给我生的希望。让我惦记着这里有一笔钱,活着把他取出来回家砍柴娶老婆。第三样则是本佛经。
望着佛经,我的脑海不自觉的生出没过多久我将和一慈大师启程回河洛城。那个困扰我的问题又在我脑子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为什么是我?”
身为河番国的子民不论何时都会自然生出对河番这个国家的热爱。所以我对佛教并不排斥。相反,在六年前,我和这个国家其它子民一样,对佛教所说的言论深信不疑。
六年前,我不过是一个十二岁的少年,那时父亲刚刚去世,我不得不拿起他遗留下的斧头上山。去承担一个家庭的责任。在某一天的某一个下午,我遇到了这本书的主人。
当时他爬在我一条路上,四周全是点滴的鲜血。一直沿伸到后方远处。那是我砍柴所必经的路。想必他走了很远,直到支撑不住。我如果我不把他带回家中医治。他可能就会死在那座山上。
我救的是一位叫道月的僧人。出于对佛僧的尊重,以及佛法所倡导的救人一命,胜做千件好事的教条。何况救的是一个僧人,在乡下人的观念中,胜做的好事自然超过了一倍。所以母亲把他养的活蹦乱跳,脸上生出肥肉才放他离去。
这期间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就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了他的与众不同。他并不像其它僧人一样对佛崇拜,在谈论佛时无论是脸色还是口气都充满了鄙视。当时作为不懂事的我,自然只是觉的奇怪,并未想太多。直到他离开后,我才慢慢思索他的话,并尝试着理解。
虽然我是一个乡下少年,模样作派与其它的乡下少年没什么不同,但我知道,还是有些不同的。我想,他给我开启了一个叫智慧的东西。我慢慢长大,虽没有经过大事,但所接触的小事来看。我似乎越来越理解了他的言论。不过,这样的言论对月番国任何子民来说,不说大逆不道,被人当成异类是一定跑不掉的。
我知道他的话如果真的散播出来后所引发的后果,这些后果并不是我这样的人能够承担的。所以,他的话以及他的话所引发我的思考并形成自已对某事情的看法我只能心里明白罢了。但在表面上,我仍然和其它河番国子民没什么两样,一样的对佛敬重,一样的按照佛法来安排我的生活。这也许是我排斥去大披寺真正的原因吧!
那个叫道月的僧人不知去了何处,可我现在,马上就要去河洛城了。我叹了一口气,将那本《纳融宝经》收在箱子里。然后将箱子放到怀中,从灌木丛中钻了出来,看了下天气,时已正午,便开始向山下走去。
到了屋子前面,那里已经站满了人。正中间是一慈,他仍然笑眯眯的看着我。百夫长也在,不过已经退到十多米之外。因为在他前面有比他职位更高的人。在一慈身边的是一位魁梧男子,满脸刚须。他与一慈交谈着什么,脸上不时浮现出杀气。我认识他,他是此地的最高统帅------项台将军。
我急走了几步,跪在地上,高呼道:“参见将军”。项台望了我一眼,眯着眼,脸上闪出一道寒气。一个小小的兵卒,居然让一军统帅站在这里久等,放在任何时候,他都会治我的罪,但今天不会,虽然不会,但掩饰不住对我的厌烦。
“起来吧!一慈大师在这等有半个时辰,你好大的架子”。我无言,又给一慈大师叩拜。一慈上前一步,将我搀了起来。项台惊愕。大披寺僧人在月番国子民眼中如神人存在,他如昨晚的百夫长一样,不明白一慈为什么放下身段,去搀扶我这个无足轻重的兵士。
他进退两难,不上前怎么让一慈大师做这样的事情,上前又折损了他的官威。我再无自知之明也知此时不应当着众兵士面前受这一扶。急忙站了起来。
“你的事情已经办妥了”,一慈问道。
“妥了。”
“现在可以上路否?”
我点了点头,一慈冲项台合什说道;“打扰两日,有碍将军军务,可我来此乃寺内之命,还望将军见谅。”
“岂敢岂敢”。项台急忙合什回礼道:“大披寺乃我朝圣地,平日请恐怕也难请动大师,我只盼大师能多留几日,怎敢说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