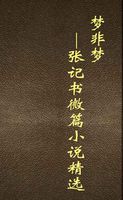且说贾似道自谓三朝权臣,当然是“宰相不出门,执掌天下事”;自己什么风浪没有见过?此次虽然不幸战败,但自己“运筹帷幄”,当不至于“大难临头”罢!
事实上,贾似道的如意算盘打得精明已极:
其一、贾似道确是朝中有人,而且此人竟是处在大宋权力巅峰的谢太皇太后,当然是他最可靠的靠山了。
其二、贾似道于战败逃亡的危急时刻,尚不忘预留后招:于逃亡维扬途中,急遣翁应龙直接赴京,一则将建议移都海上、避敌锋芒的奏疏上呈谢太皇太后;二则将都督府印信私下送交陈宜中,意在为自己安排后路。他很明白,如今宋军的主要力量,葬送在自己手中,失宠是必然的,受罚也是必然的,该找一个可靠的依靠了,到时候可以保他一下,尽可能地从轻发落。而这个依靠,就只能是陈宜中了。——毕竟,陈宜中乃是自己一手擢拔起来的,他还真能忘恩负义不成?!
其三、贾似道当然对陈宜中的媚世与善变了然于心,所以他还有更隐秘的致命绝招:遣翁应龙暗地里给御前都指挥使韩震送了个蜡丸,里面有自己的锦囊妙计,足以险中求安的呢!只不过,此事除了翁应龙,贾似道连廖莹中也没告诉,为的乃是要绝对的保密。——毕竟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
然而,正所谓“人算不如天算”——恰恰就是这个最不可能发生的“万一”,却反倒真的成为了最令贾似道可怕的现实:
且说翁应龙于逃亡维扬途中,奉贾似道之命改道赴京;于路不辞辛苦,这日黄昏终于来到京城之内。本该当即赴朝奏报的他,却遵从贾似道的密嘱,先自躲躲闪闪地到了陈宜中的府上来。那翁应龙身为贾似道府中的堂吏,素与陈宜中是惯常往来的,到他府上自非一朝,此来自然是直出直入、无需门房通报的。
身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参知政事的陈宜中,方才接到特急密报,说是贾太师亲自都督十三万禁军参与的淮西战事,已经失败了,全军覆灭了,连贾似道、孙虎臣也不知去向了。陈宜中这时,真是又惊又喜:惊的是,贾似道位居平章军国重事、都督诸路军马,度宗尊之为“师臣”,众臣视之为“周公”,率领的也是十三万禁军精锐呀,却怎么会如此地不堪一击呢?这一来,精兵丧尽,国都不保哇!喜的是,贾似道兵败,朝中“舍我其谁”?眼看着自己必将登峰造极啦!
正这样想着呢,只听一声怯生生的招呼道:“陈大人,在下给您请安来了!”这声音起自身后,好生熟悉。陈宜中回头看去,见来人竟是贾府堂吏翁应龙,正朝自己施礼呢;这一来,陈宜中真是大出意料之外:“刚刚才得到淮西大败的消息,怎么翁应龙就到了?唔,正不知详情呢,尤其是不知贾太师的情况,更愁该如何行事哩!现在可好,只要问问翁应龙,不就什么都能明白么?”陈宜中想到此处,顿时回礼道:“原来是翁先生来了,本官有失迎迓,恕罪恕罪!”
翁应龙急步近前,左顾右盼、神秘兮兮地道:“陈大人,可否借一步说话?”
陈宜中见此光景,忙道:“行行行,书房请,书房请!”
翁应龙不待领路,自己便熟门熟路地疾步来到陈府的书房之内。
陈宜中随唤管家待茶,翁应龙接茶在手,却只是默然地品着,久久不吭一声。
陈宜中终于不耐,问道:“翁先生,你不是有话要说吗?快请说来听听呀!”
翁应龙见问,这才放下茶盅,缓缓地从怀里掏出一个包扎得相当结实的小锦囊,双手呈上道:“这是太师着我专程送给陈大人的。”
陈宜中不知锦囊中包着何物,不免讶道:“这是······”
翁应龙不假思索地道:“都督府的印信。”
陈宜中听了,大感意外,心道:“怎么将都督府的印信送到我家里来了?为什么送给我?贾太师是否另有深意?!”
一切有待印证!于是,陈宜中问道:“太师现在何处?”
翁应龙听了一愣,心道:“太师只叫我先将都督府印信私自送交陈宜中,再送个蜡丸给韩震,然后将一份奏疏直接上呈给谢太皇太后;却并未提及自己的去向。怕是不愿及早让人知道,以便拖延些时日,就此减轻些罪罚的罢!而且,太师当时一再叮嘱:‘这些事只能分头去办,决不能将实情告诉任何人’的啊!”这时听陈宜中问起贾太师的去向,竟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于是只能摇头不答。
陈宜中这时却已领悟了贾似道将都督府印信私自送交给自己的深意:“他既将兵权交给我了,便是在交待后事呀!只是,他人在何方呢,为什么翁应龙不肯明言?莫非······”于是忍不住又问道:“太师呢,他到底在哪里?”
翁应龙不能再不吭声了,却已暗自打定主意,更不迟疑地回道:“不知道”。
陈宜中听他如此一说,不免判断道:“很可能,贾似道已经不在人世了;或者,即便他还活着,也必是个‘活死人’了,无法再出来视事的。那么,翁应龙所说的不知道,只是担心影响贾氏党朋的分崩离析,进而引发朝中的大哗变”。想到此处,心中忽然有了一个更大胆且极阴险的主意:“不管怎么说,只要我大权在握,那时,嘿嘿······”
刚刚送走翁应龙,陈宜中随即回到书房,心道:“‘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呀!”于是开始用他那支生花妙笔,连夜挥洒出一份奏疏。次日一早便赶着上朝去了。
慈元殿里,谢太皇太后度日如年:
一向慈祥、随和、沉静、硬朗的老人,忽然就快被“千斤重担”压垮,只得来个“火山大爆发”啦!
听,半夜三更的,老人就在顾自念叨着呢:“······老身到底招谁惹谁了,在两代先皇手上,虽说战火频仍,但终究平安度过了;况且那国事大都由他们自个儿担待着,四十年间也没要老身出过几次面!可如今老身已然是六十有五的高龄,身子骨儿、腿脚精神呀什么的都越来越差的当儿,虽然托了三代天子的福分,总是无忧无虑的过日子,也没落下什么大的毛病;但如今这一年多来,朝廷的大小事儿简直就像一副烂摊子,着实压得老身快喘不过气儿来。人家都说老身这一年来明显地老态了,可咱还得硬撑着呀!这倒也罢了,现如今人家都说是‘春宵一刻值千金’的美好时光,怎么却成了老身有生以来最受煎熬的时候呢?唉!”
老人说这话儿,原是为芜湖刚刚送来的战报给吓的:“十三万精锐禁兵,加上沿江的无数厢兵,总有二三十万的兵马,一下子却都被元军给消灭了。这可是大宋的有生力量呀!现如今抵抗元军,保卫江山,最能指望的就只有这批有生力量呀!但一下子就这样‘树倒猢狲散’了,怎么说也不应该的呀!”她曾对贾似道和孙虎臣寄予厚望的,可是如今呢:“一个是三朝老臣,国之台柱;一个是朝中虎将,身经百战。怎么就这等脓包,才几天的工夫,就将全部人马丧失殆尽!贾似道呀贾似道,你真是罪该万死呀!”
正在念叨不已之际,谁知又有奏疏呈上;谢太皇太后不禁皱眉道:“这天还没亮呢,又有什么事情如此紧急呀?”
那呈送奏章的宫官跪奏道:“是贾太师着人送来的十万火急的奏疏。”
谢太皇太后这时十分冷淡地道:“哼,再急又有何用?!”
接过奏疏,谢太皇太后不看则已,这一看罢,顿时是又气又怒:“哼!甚么出路只有一条:移跸海上,积蓄力量,再图反攻?临安还没丢呢,你就怕成这样呀!哼!你倒好,也不出个拒敌的好主意,竟然躲到维扬‘做足准备,迎驾出海’——分明就是怕受责罚么!”想到“移跸海上”,谢太皇太后简直怕得要命:“听说那海是一片汪洋、无边无际的水域,其中却连立足的地坪都找不到一小块,怎么能驻足活命呢?再说啦,住在地面上虽说时有风霜雨雪,却怎么也不比海里总是有大风大浪吓人哪!”
谢太皇太后百感交集、彻夜未眠。
次日俟天初亮,谢太皇太后早早地来到宣政殿,辅佐天子垂帘听政。谁知她到底还是来晚了,只见文武大臣们比她还早,而且一反常态、一个个都心事重重的,全不像往常那样三个一堆、五个一群地谈笑风生。
谢太皇太后在全太后右首、皇上稍后的一张盘龙大椅上落座后,君臣见礼毕;谢太皇太后即便动朱唇,启玉音道:“众爱卿早早来到,莫非皆为芜湖战事?”
谢太皇太后话音刚落,只见殿下班部丛中,一人挺身而出,跪禀道:“微臣陈宜中正为此有本上奏!”
谢太皇太后点头道:“爱卿但奏无妨。”
陈宜中将出连夜拟就的奏折,当众朗声奏报道:“近北兵渡江已逾两月,上而三宫,下而万姓,皆谓平章贾似道督师一出,未必负三朝礼遇之恩,必能以一死酬天地涵容之泽。而乃拥师逗留,不发一矢。今月二十日,忽报孙虎臣;又二十二日,报臣等以诸军皆溃散。初犹有自与一决之语,既乃发为海上迎驾之言。臣见其平日自诡以知兵意,或有深谋秘计,可以救一脉于垂亡。观其所措,有非腐儒所能测识。忽二月二十八日早,有督府随吏回归,乃言似道于二十日夜三更鸣锣一声,回散诸军,窜身而去,莫知所之。臣闻之血泪迸流,欲死无由,因自痛念,曩经丁大全败窜之余,适际理宗再生之德,徼逾末年。似道时适当国,起自书生,叨居枢地。彼虽一出,臣每见其施行时有差舛,未尝不从容纳规,而才弱力薄,凡莫能救。正如范文虎事,争之不力,稔祸今日,涕殒何追!今似道以溃师窜身,上误宗社,臣曩为台谏,既无吕诲之先见;臣今为执政,又不能为社稷力争,罪何所逃!谨自具劾以闻,欲望圣慈重行追窜,正平日苟容之罪,以谢公论;仍乞正似道误国之罪,以谢天下。祖宗德泽未衰,人心戴宋犹故,元气一脉尚可挽回,仍乞将公田、市舶茶盐等拂民所欲者悉赐改正。令学士院降诏,以明太皇太后、陛下哀痛悔恨之意,少回皇天舍逆助顺之心。”
原来贾似道一贯独霸朝政,早成众矢之的;对于贾似道的此番完败,众朝臣愈加不能容忍。此时又看见贾似道的得意门生陈宜中竟已做出如此慷慨激昂的反叛之举,众朝臣更是欢喜得了不得,于是无不乘风而上,纷纷上书,列举贾似道的诸多罪状,要求诛之以谢天下。
谢太皇太后见了,到底心软,心道:“一朝做错,众理难容!真要论起来,其实‘胜败乃兵家常事’;怪就怪这贾似道,纵有难处,也该来当面向我说个清楚明白嘛!”想到这里,便转过话题,命宫官举起贾似道的那份奏疏,说道:“这是贾太师连夜着人呈上来的一道奏疏,说他现在维扬,要求哀家、天子和众爱卿一同移跸海上,避开元军的攻击,以图日后卷土重来。如今他正在维扬等待迎接咱们哩。哀家看来,这也算得上是为朝廷着想的忠臣之举呀!众卿倒是议议看,这移跸海上呀,是去得,还是去不得?”
谢太皇太后平静的话语,却在文武大臣们的心中,霎时掀起了轩然大波:
首先是陈宜中吃惊最大:他原以为贾似道已死,才急着上此奏本欲图清算贾似道祸国殃民的罪行,请求诛杀之以谢天下;这样既顺民意,又好借此为自己今后的飞黄腾达铺路。然而这时却听谢太皇太后亲口说出贾似道未死,而是身在维扬,等待迎接朝廷移跸海上呢!这一来,他心中如何不慌:“一旦贾似道东山再起,我陈宜中不死才怪哩!对了,趁着贾似道落难不起,何不落井下石,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呢?对,就是这个主意!”想到这里,陈宜中又一次抢着出班奏道:“启奏太皇太后:贾太师、贾平章、贾都督这个建议尚容再议呀!移跸乃是关系社稷存亡的大事,轻易行不得的;何况移跸海上,茫茫如野,咱大宋仅存的这么一点根基儿势必全都丢尽了,今后咱还怎么立足?还谈什么卷土重来?臣以为:此事还须周密考虑,待有个稳妥的意见后再行决定为上。”
谢太皇太后听罢,微微点了点头,正准备说些什么,却把殿前都指挥使韩震急坏了:
原来,昨晚翁应龙出了陈宜中府邸后,径自来到韩震府上,将那蜡丸亲手交到他手里,说是太师亲**待:里面有锦囊妙计,让他领会后,小心从事。
韩震礼送翁应龙离去后,启封观看,只见蜡丸当中,封固一小卷素锦,上面惟小草两行:助与权移跸海上,或以力促!
“与权”乃陈宜中小字,韩震岂会不知?
韩震看罢,将那素锦付之一炬,心道:“某与‘与权’皆为朝廷主要权臣,此事料不难办到!”谁知才过了一个晚上,便看到陈宜中如此翻脸不认人;于是待陈宜中刚刚奏完,还没退回班部丛里哩,便非常生气地抢着奏道:“启奏太皇太后,臣以为贾太师所奏十分有理。贾太师正是因为国家当前的危难才出此高策的。丁家洲的惨败,势必加速元军进攻临安的进程与危险性,如果不及早迁都,朝廷必将有落入敌手的可能。而要迁都,就眼下四处受敌的实际状况,很难找到一片安宁的地方。那便只有出海:在海上,可以飘泊无定,元军目前既没有入海的水军力量能够搜寻得了,朝廷也可沿海自由移动,求得一线生机。这才是最安全之举。”
这时,左丞相兼枢密使王爚说话了:“移跸海上?这怎么成?这是要毁我宋室呀!飘浮汪洋大海之中,住无所倚,生无所恃,万万不可呀!”
王爚系理宗时多年任左、右丞相的重臣,为人清修刚劲,对朝廷也忠心耿耿;虽亦为贾似道所提携,但却多次劾贾似道骄淫专权,贾甚恨之。贾似道回天台葬母过新昌时,人人趋而奉之,独爚不见。
谢太皇太后听他也这么说,终于一锤定音道:“移跸海上之事,确实不能做,就这么定了。”顿了顿,又道:“至于似道么,丧师误国,理当受惩;只是哀家想来:似道勤劳三朝,岂宜以一旦罪,失遇大臣之礼?宜罢其平章军国重事和都督诸路军马之职。惩戒若此,众爱卿就放他一马吧!”
陈宜中见谢太皇太后如此一说,心知不好再勉强了,于是适时出班再奏道:“启奏太皇太后,臣还有一事容禀!”
谢太皇太后道:“有事但奏无妨!”
陈宜中缓缓地自怀里掏出那个小锦囊道:“这是贾都督托人私自送交给微臣的都督府印信,微臣不敢擅专,还是交给太皇太后您吧!”
谢太皇太后见状,脸上登时浮现出满意的笑容,道:“朝廷有陈爱卿这般的忠臣,哀家这就放心了!那印信就交给爱卿了;似道的职事今后就通通由爱卿接管了吧!”
陈宜中一听,正合心意;却假意推托道:“这···这怕是不妥吧!”
谢太皇太后微愠道:“眼下元军凶狂已极,大有侵犯临安之势,哀家尚需倚靠爱卿等出谋划策、出力拒敌哩,难道陈爱卿不乐意?”
陈宜中眼见火候成熟,这才顺水推舟,跪谢道:“保卫临安,在所不辞;与权恭敬不如从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