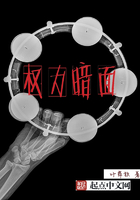忽一日,陈县宰又请贾涉到县衙饮酒。贾涉虽然无心,却驳不过面皮,只得赴宴。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鱼戏莲叶间。
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阳光新雨后,万年县衙中——
后院池塘间:荷叶丛丛,卿卿我我;莲花朵朵,粉面含羞。一双蜻蜓你追我赶、嬉戏其间,那红艳艳的身子如精灵般倏忽明灭,凭添了池塘几许静谧。蓦地,一阵乐音飘忽袭来,霎时惊破一池恬淡:伴着乐音,荷叶摇曳,莲花轻舞,抖落身上颗颗银珠,簇捧出绿荫深处的一叶莲舟;两个翠鸟不甘落后,厮赶着闪电般窜向天空,留下一串脆鸣,根本无暇顾及那泼剌剌纵跃水面的数尾锦鲤。唯剩莲舟之上,一绿衣女轻荡舟辑,纵声高歌;一红衣女和着节拍,翩翩起舞。
塘前凉亭内:陈县宰与贾县丞对坐畅饮,边赏边聊。
陈县宰不无得意地道:“······此景意取‘七绝圣手’的《采莲曲》,妙在‘闻歌始觉有人来’。足下以为如何?”
贾县丞道:“好是好了。不过,倘能远观而非如此亵玩,似乎尤显‘独爱’!”
陈县宰默思片刻,蓦地击节赞道:“‘远观’必绝声色,果然便是‘独爱’;足下此语颇得元公神髓,吾虽爱莲,却远所不及。”
贾县丞闻言,陡然想起胡氏,心道:“我欲‘独爱’而不能,真是愧煞!”一时出神,竟至缄口未语,仰头向天。
陈县宰久不闻贾县丞答言,却见他仰视寰宇,亦不免循目遥望,但见西天彩虹高悬,更有夕阳余晖,便笑道:“你我深陷官场,早已身不由己。正如这雨后彩虹,虽然绚烂,却转眼将逝;亦如这血色夕阳,虽然壮观,乃日暮必坠。谁又能独善其身呢?!”
贾县丞听了,举杯一饮而尽,轻叹一声道:“我倒想着要脱离官场,以便‘独爱’哩!”
陈县宰点点头,又摇摇头,道:“脱离官场,或能独善其身;‘独爱’,必得红颜知己。但终究有得亦有失,甚或得不偿失······咦,足下此言,莫非有了知己,又难以处置?”
贾县丞见陈县宰一语中的,随即长叹一声道:“本来家丑不可外扬,但堂尊情逾手足,说亦无妨:只因家妻唐氏自来未孕,那年我在前往临安府听选途中,偶于钱塘凤口里歇脚,看见村民王小四之妻胡氏颇具福相,因思纳为小妾,继承香火。所幸对方家贫无奈,一说便成,于是花些银两讨了来。如今天幸果然身怀六甲,只是唐氏必不能容······”遂将唐氏相妒之情详述了一遍。末了又道:“本来妻妾相妒,亦属寻常。但贾门宗祠,全赖胡氏一人;偏偏唐氏贼恶,恐发作起来,万一坏了香火。故此烦恼。不知堂尊有何妙策,可解此厄?”
陈县宰听罢,寻思了一会儿,笑道:“要解此厄不难,只怕足下舍不得胡氏离身呢!”
贾县丞尴尬一笑,道:“实不瞒堂尊,如今胡氏被唐氏管得贼紧,想要亲近都难,还有什么舍不得呢?!”
陈县宰道:“既然如此,那咱们只需如此如此,必能成事。”乃取件物事递与贾县丞。贾县丞把来心口藏了,一时愁云尽散。
有道是:心魔难伏。眼看着丞厅好不容易平静了数日,贾涉却不喜反忧,心道:怎么一点事儿都没有呢?巴巴儿地直熬过了约摸半个月的光景,这晚才终于见阿忠来禀,说是夫人直闹腹痛。贾涉情知她那老毛病儿又犯了,当下即命阿忠请医,随即亲来照看不题。
且说次早陈县宰升厅公座,不见贾涉点卯,心知那话儿来了;急忙差人打听时,果是唐孺人有恙,不免心中暗喜。俟午衙散过,回到私衙,同奶奶说知就里。奶奶倒是个菩萨心肠,又听说是个救苦救难的善举,还不是言听计从?俟其病愈,便备了四色茶果,特到丞厅问安,相机行事。唐孺人喜不自禁,慌忙留之宽坐,并整备酒饭相款。两家原就是通家往来,相处得极好的,奶奶便不客气,与唐孺人只顾南聊北侃。聊到兴处,奶奶手指身前左右环伺着的诸婢,还有端茶备饭、往来服侍着的女使,轻叹一声道:“贵厅且是享福!只叹寒舍无人,甚不方便。不知贵厅能否借个小娘子,相帮几时?”嘴上说着,心中却道:“看你如何推诿?”唐氏心道:“这婆娘忒也贪了,连个婢子都要。却又不便得罪。”嘴上便道:“奶奶如何说个‘借’字?不就一个粗婢么?奶奶只要看得上眼的,任凭领去得了!”心里却又着实捏了把汗,生怕将锦儿讨了去。哪知奶奶称谢毕,心花怒放道:“中计了!”只顾把眼来瞄诸婢,果见其中一个面如满月,鬓边插朵红帛花——当然识得那正是丈夫把与的自家佩饰——心知是了,暗忖道:“果如所言,此女天生的福相。可惜犯了唐孺人的克星,一时不得出头!”这便指定她道:“这位小娘子看来极是顺眼,便借她如何?”唐氏见奶奶指的乃是胡氏,不但心中的那块石头落了地,而且有种说不出的畅快,心道:“可巧是她!老娘正巴不得让她离得远远的!这倒好,一则县宰奶奶开了金口,丞厅怎敢不从?老爷要埋怨时便找她去;二则落得做个顺水人情呢······”心中盘算周全了,便一迭连声地道:“这小婢姓胡,来我家也不多时。奶奶既中意时,即今便叫她随奶奶去。”当时席散。奶奶犹恐夜长梦多,便要告别;不意那唐孺人竟也主意相若,急催胡氏收拾前去。胡氏未知凶吉,却也身不由己,只得急急收拾已了,拜了唐氏四拜,当时跟着奶奶轿子走了。俟其走远,唐氏方才入内对贾涉说知。贾涉故作惊惋不题。
且说胡氏到了县衙,听奶奶说知备细,当时嗟叹不已,亦不免对奶奶感激涕零。奶奶随即命人将胡氏另行安顿。这年的八月初八,胡氏如愿产下个男婴,欢喜得了不得。奶奶即时封锁消息,丞厅哪里知道?便是贾涉当时在外公干,亦毫不知情;直到次月归来,方才听陈县宰私报了喜讯。贾涉大喜之下,除了感激不尽,亦央告过陈县宰,方才能够隔帘见了胡氏一面,说了几句体己话儿;又亲手抱了抱孩子,滴了几滴老泪——毕竟碍于礼数;抑且别人家中,哪如自家方便?!但即便如此,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总之,贾涉当时虽觉庆幸有余,但终究是怏怏而回。不过,自此以后,贾涉背地里常常隔三岔五地送些钱钞与胡氏买东买西,或借故见上一面。不在话下。
不曾想“幸福的日子贼快”,转眼二载有余,陈县宰因任满升迁,要赴临安。贾涉无奈之下,只得涎着脸儿将前情尽告唐氏。唐氏不等贾涉说完,便跳将起来,捋袖指鼻骂贾涉道:“我说当年那事儿怎地那么巧呢,原来都是你们串通了骗老娘的!如今想是又要领她回来的么?哼!除非把老娘杀了,否则休想!”又遥指县衙方向,打着哭腔、咬牙切齿道:“你这天杀的,要你来害老娘······”这便窜到门后,抄起门杠乱砸乱扫。贾涉主仆吓得一溜烟的都走了。过了好半晌,内堂终于平静了。贾涉且不管满地的什物碎片,径来对唐氏摊牌道:“拼着得罪你娘家,也不能绝了贾氏宗祠。你看着办罢!”唐氏见状,只得稍让道:“是你贾家的,领回来可以;不是贾家的,休想领进门!”贾涉听罢,一时呆了,心道:“我与胡氏早就咫尺天涯一般,倒也罢了。只是这孩子,没有母乳尚可对付;倘被唐氏借故谋害,那可要了老命!”
正在前思后想、左右为难之际,忽见阿忠来报:“台州有人来访。”贾涉听说故乡来人,只得暂缓心事,来见客人。那人却是亲兄贾濡。兄弟不免亲热一番。贾濡便道:“我今奉旨为朝廷选妃,趁便将女儿玉华选了上去,志在必得。此来为要打通刘八太尉的关系,力求万无一失。不知贤弟可有路数?”
贾涉吃惊道:“只此独苗儿,哥哥也舍得?!”
贾濡点头道:“养儿防老,况亦光宗耀祖的好事!”
贾涉重重地点头道:“此亦十分美事,小弟保管玉成!”
贾濡十分惊喜地道:“哦,此话当真?!”
贾涉闻言笑道:“这还能假?说起来,也是十分的凑巧:小弟当年在临安听选时,赁的正是刘八太尉的房子,交情非浅。待我修书一封呈与他,此事必成!”
贾濡大喜道:“贤弟既有此路数,不愁日后仕途不顺哪!”
贾涉道:“那是自然。便是之前这几年,因了县宰陈履常与咱同乡,一向也是颇得照拂!”说罢,话锋一转,蹙眉轻叹道:“这倒罢了。却是家事扰人,实在将我烦透了!”随将这几年来娶妾生子,并唐氏相妒之情简略地与贾濡说了。结末道:“如今陈公将次离任,这孩子眼看又没安置处。哥哥若念在贾门宗祠的份上,帮小弟将他抚养成人,那实在是感恩不尽!”
贾濡连忙道:“贤弟哪里话来?!你我同气连枝,况且我如今尚无子息;这孩子不是我领去,还教谁看管?”
贾涉大喜,随唤阿忠私下里雇了个奶娘;又亲赴宰衙抱回了孩子,交付奶娘,令与贾濡同去。又千叮万嘱哥哥道:好生抚养。随后修书一封,教上呈刘八太尉;又赍发好些路费送哥哥起身。胡氏则托与陈公领去,任凭处置。不在话下。
且说贾濡自将侄儿领回台州故里,一直待如亲子,悉心养育。一晃数年,眼见侄儿日渐长成,贾濡真是快慰于心。这日早间,贾濡忽地想起兄弟贾涉和女儿玉华,更有过世未久的老伴,自不免望着眼前的天台山,呆呆地出神。但见其山层峦叠嶂,像条沉睡的巨龙,默默地守护着生养自己的家乡。数缕清泉,汇聚成一道玉练,冲刷出一泓碧蓝幽邃的深潭。潭前的一丛百十竿修篁绿如新出,掩映着一式的红墙碧瓦。烈日当头,洒下金光万道;山风拂面,携来暖意洋洋。
正是夏末秋初时节,深院闲庭之间,回响着袅袅童音:“······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贾濡听在耳内,喜上心头。
贾濡正沉思间,忽闻诵诗声嘎然而止;只觉侄儿蹦到身旁,扯着自己道:“伯父,教我玩儿么?”这便不由分说,拉了贾濡回到院里,就着一口陶盆相对而蹲。但见那盆状若酒缶,大可盈尺;质近古陶,高不及膝;色彩天然,淳朴清丽——端的是众里难寻,别样韵味。盆底正趴着两只促织儿,各各低头翘尾、张牙亮翅、伸腿耸身、相对凝视;当此严峻的敌对状态,尚且各自将那对触须儿左右游弋,似欲探视对手的内心企图。
这对老少自是紧张地注视着盆中的阵仗。那少年一边用牵杆逗着促织儿,一边压低了声儿道:“伯父,是您的‘红头颤’赢,还是我的‘黑蝴蝶’赢?”老者手上也不闲着,只将双眼向那盆中张了张,便低声道:“侄儿你看,你那‘黑蝴蝶’形似蝴蝶,色黑、头尖、项紧,脚亦瘦薄——虽然长大,却欠纯良,难免是‘外强中干’;且看老夫的‘红头颤’,却是‘头似花枝身段赤,项肥身阔腿脚长’,极是小巧,亦且精灵,隐隐乎‘身心合一’。有道是:‘赤小黑大,可当乎对敌之勇’;又道是:‘脚长有胜无输,身狭少赢多败’。总之而论,应该还是老夫的‘红头颤’胜算多些!”
少年听了,显然急不可耐,陡地将手中长牵急往盆中插入,想是要催赶那“黑蝴蝶”奋勇向前。老者见状,脱口惊呼道:“不可莽撞!”再欲挥牵相阻时,已自不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两个促织儿如遭霹雳,蓦地窜起尺余高下,跳出斗盆,各自奔逃。
少年不虞此变,一时慌了手脚;眼看着老者闪转扑腾,不但丝毫无功,而且反被两个促织儿捉迷藏般,撩拨得东也不成、西也难就。少年见状不耐,立马加入战团,瞅准了自己的那只“黑蝴蝶”,怎消得三窜两扑,便自逮了来拳在掌心;随即紧走几步,放入盆里盖妥了。再车转身来抓那“红头颤”时,见那虫儿早被老者赶到院门口了。
少年大急,疾步蹿到门外,返身来截。不想那虫儿许是被老者赶得急了,一时竟舍身从少年胯下蹿将过去,出了院门,亡命地奔逃。
少年拔脚便追,老者急劝道:“不要追了!那两个寻常之物,不要也罢!”
少年哪里肯听?急蹑着虫影紧追不舍!约莫过了寻丈远近,那虫儿势将入彀时,却被它奋力一跃,霎时跳到了一件物事儿上。少年疾抬头看时,见是有人抬了口偌大的棺木正朝自家的宅院走来。那棺木黑漆森然,极是骇人,“红头颤”却是毫不畏惧地停在头里,兀自低头翘尾、捋须磨牙,似是得意之极。少年见了那虫儿心痒痒的,却又怕极了那口棺木;何况对方并未止步,眼看就将往自己身上直撞过来。少年顿时不由自主地叫声“妈呀!”随即扭身便跑。进了院子,又急忙返身将院门闩踏实了,这才摸摸胸口、松了口气儿。
老者见状,笑道:“见鬼了么?”
少年大骇,兀自气息未定地沉声道:“不是鬼,是棺材!”
老者这时也不免大惊道:“此话当真?”话犹未了,果听有人拍门道:“开门、开门!”
少年大惊,躲到老者身后直哆嗦。
老者回身,一把将少年搂在怀里,低声安慰道:“不怕、不怕!”随即转头朝院外高声喝道:“什么人,来我庄上做什么?”
却听门外有人接口道:“哥哥开门,是小弟贾涉!”
那老者便是贾濡了,他听见院门外传来的果真是弟弟贾涉的声音,不禁大觉诧异,却疾将院门开了,迎接入内。兄弟相逢,又惊又喜,相抱无语。良久,贾濡似才醒悟的一般,指着那口棺木道:“贤弟,这是······”
贾涉闻言,未语泪先流,好半晌才哽咽着道:“唐氏殁了,老毛病······”一时间,兄弟二人相顾失语,惟剩泪千行。
少年在一旁看见二老只顾着哭泣,甚觉无趣,不由将小嘴一撅,以手刮脸道:“不羞、不羞!”
贾濡忍泪拉他小手道:“孩子,快叫爹呀!”
见少年迟疑着,贾涉探手摸他头道:“孩子,不认爹了?”
少年却猛地蹿了开去,迭声嚷嚷道:“娘亲呢?我要娘亲!”
贾涉见了,不禁老泪纵横地道:“可怜的孩子!可惜他娘!”
贾濡讶道:“胡氏她······”
贾涉抹把泪道:“可惜他娘,听说嫁了个维扬的石匠。真是造孽呀!”
贾濡听了,唏嘘不已。
沉默半晌,贾濡打破沉寂道:“往事如烟,随它去罢!如今唐氏安葬事大呢!对了,给孩子取个名字吧,也好竖碑入祠呀!”
贾涉点点头,想了想道:“咱兄弟为官多年,一向遵道法宪,自也希望孩子将来能做个好官的不是?!便给他取名似道,表字师宪如何?”
贾濡立时赞不绝口地道:“贤弟果然经纶满腹,这名字取得当真妙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