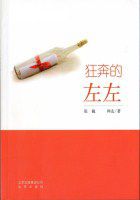公孙博所料不差,这几日东君蛩确实是坐立难安忧心焚焚。国王被刺杀,所幸没有命中要害,匕首上也并没有淬炼上剧毒,经过太医们一番精心调理,本已无大碍。
可谁能料想到,那东君兰为了独邀圣宠,竟挑唆国王服用烈性房中之药,夜夜高烧红烛颠鸾倒凤。这国王初尝房中之事的甜头,加上东君兰妖媚放荡百般迎合奉承,竟是在床上征伐不休,接连泄身还意犹未尽,引得旧伤复发,直到下体流出脓血才意识到危害,可这时已是命如悬丝脚踏幽冥了。
东君蛩与太后知道国王乃是纵欲过度,才落得这般下场后,都将东君兰骂个狗血淋头。太后出于爱子之心,巴不得将东君兰剥皮吃肉;东君蛩思虑更深一些,当他第一眼看见国王躺在病榻上半死不活时,就意识到危机来临了,因而对东君兰的责骂更甚于太后。
东君蛩心里明白,这一次的危机,非是以往可比。不管是围场遭人暗杀,还是轩辕族集体施压反抗,说到底,国王与太后都被自己牢牢抓在手心里,自己总能以王命行事,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可要是国王一旦驾崩,就要迎立新王,可谁能保证这新王也能百分之百顺从自己?国王没有子嗣,到时候就连太后也只剩下了空壳子,就算她还站在自己一边,也是毫无作用了。
自黄帝飞升以来几百年来,龙侯族一直在东部海滨偏居一隅,总是如履薄冰一般在夹缝里生存。到了东君蛩,他凭借着自己盖世无双的才能与胆略,才谋得镇国侯之位,又挑起夏州国与昆仑族之战,还大肆削弱了轩辕族实力,眼见着就能执鼎称霸,偏偏这时候出了这般变故,东君蛩心里的恼怒和不甘可想而知!
东君蛩是何等人物,怎会容忍自己苦心经营的大业付诸东流?他经过彻夜审时度势苦思冥想,已经计上心来,一面要稳住太后,不让她乱了方寸,同时封锁消息,不可让轩辕族占得先机,自己好有转圜余地;一面则要从国王子嗣上做文章,只要国王有后,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三日后就是太后寿辰,到时群臣都要到宫里祝寿,国王当然要抛头露面,这才是关键时刻。只要挺过去,东君蛩自信一切又会回到自己掌控之中。想通关键之处,东君蛩又恢复了以往的杀伐果决之风。
东君兰提心吊胆走进叔父处理政务的偏殿中时,看见东君蛩正在喝着粥,怯生生走过去,行礼道:“叔父,听人说您找我?兰儿来了。”
东君蛩停下筷子,抬眼看到东君兰披头散发眼睛红肿,心也就软了,指着身旁凳子说:“还没用早膳吧?来,陪叔父喝碗粥。来人哪,给王妃盛粥。”
东君兰早没有了先前的骄傲蛮横,还未开口眼泪就簌簌流了下来,她在龙侯国时,最怕的人就是东君蛩。前日东君蛩对着她大发雷霆,吓得她三魂六魄都出了窍,如今被东君蛩传唤过来,心脏突突直跳,当下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说:“叔父,兰儿知道错了!”
东君蛩叹口气,拉起东君兰,柔声说道:“兰儿,叔父能理解,你也是为了我龙侯国着想嘛!你一心要侍候好国王,不就是为了给我争口气,好早日当上王后吗?错就错在,你操之过急,打乱了叔父的谋划。好了,别哭啦,我前日也是火气大了些,你别怪叔父没有给你留情面哪!”
东君兰听得此言,知道东君蛩不再怪罪自己,心里也轻松了一些,可她太了解东君蛩了,便乖巧地说:“叔父,兰儿酿成大错,也不求叔父开恩谅解,只求能有所补救!”
“这才是我龙侯族子孙!”东君蛩心下大慰,吩咐道,“兰儿,接下来三日,你要尽心尽力服侍国王,要寸步不离地守在病榻前,一来让宫中之人看到你的贤惠本分,好堵住悠悠之口;二来倘若一有变故,要及时通知我。形势危急,只有我二人同心协力才能实现我龙侯族几百年强国称霸之大业!兰儿啊,叔父可就全指望你了!”
东君兰被一席话说得心头大热,竟连早餐也不吃,匆忙赶往国王寝宫去了。东君蛩这些话,一方面包含他的用人之道,一方面也是所言不虚,因而也显得情真意切。
东君蛩还有大事未完成,也无心用膳了,放下碗筷朝太后寝宫走去。还未进宫门,就听见太后在殿中训斥侍女,还传来摔打碗筷的声音。
东君蛩屏退所有侍女,弯腰捡起地上的碗筷,放到桌子上说道:“太后可要保重凤体哪!”
“哼!事到如今,你让我如何保重?我来问你,接下来该怎么办?”太后显然已经动了气。
“我也不愿看到今日局面,太后担忧国王龙体,臣下理解。可我要提醒太后,该早做打算了,否则大祸就要临头啦!”东君蛩站在太后面前,眼睛直盯着她,表情严峻。
“有什么大祸?我看那东君兰才是祸根!”太后依旧对东君兰怀恨在心,“这浪蹄子就是千年狐狸转世,****龌龊!你偏要袒护于她,难不成你真把这王宫当做龙侯国国宫了吧?”太后毕竟是一介女流,心里已经方寸大乱,竟然口不择言了。
东君蛩皱起眉头,心头起了一股狠劲,但他明白此时万万不能与太后翻脸,否则轩辕族就有机可趁了。于是不动声色地走过去,轻轻揽住太后肩膀,抚摸着她的秀发,缓缓说道:“这几日害你担惊受怕,是我不好!你看看,你可是消瘦多了。”
太后毕竟是女人,一腔柔情怎禁得起撩拨,眼里泪水打转,语气变得幽怨起来:“当初要不是你百般勾引人家,我又怎会落到这般田地!你啊,真是我前世的冤家。我也不恼你,也不恨你,我只恨自己没有把持住。现在好了,不但我夫君命丧黄泉,而且还要连带我王儿也要在你手里丢了性命,你真是我命中克星!”说着,用手捶打着东君蛩胸脯。
东君蛩任凭太后一通捶打,等她慢慢平静下来,才话归正题:“眼下光是哭骂,也无济于事了!最重要的是,要赶快稳住局面,否则一有变故,我们可就要被敌人生吞活剥了!”
“我看谁敢?好歹我还是太后啊,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哎呀,你也不想一想,没有了国王,你这太后还有何倚仗?”东君蛩的担心果然应验了,这太后目光还是短浅了些,只得耐心解释道,“国王没有子嗣,一旦驾崩,这新王由谁来做?就算新王仍然尊你为太后,哪怕就是太皇太后,你可还有实权?不过是空架子罢了!这已经是最好的打算了,倘若新王稍有不满,你连空架子的虚名都难保啊!”
东君蛩一番话,决然不提自己,只管点出与太后相关之处,早就唬得太后心惊肉跳。太后现在心里总算明白过来,连忙问道:“那我该怎么办?难不成就这样束手无策?”
“只要太后稳住情绪,臣下自有计策!”
“可是我王儿并没有子嗣啊,到头来还不是要从外面另立新王!”太后实在想不到东君蛩还有什么计策了。
“如果王妃有了身孕呢?”东君蛩说出了心中酝酿多时的想法。
三日后,太后寿辰庆典如期举行。公孙博随着道贺群臣进入宫中,在宫门口看见鸠雅,两人默默点了点头。王宫里到处张灯结彩,仙乐飘飘,侍女们脸上笑意盈盈,款步迎候在大殿之外。在一处开阔地方,还有一群歌姬舞女轻展衣袖,脚下生风般踏乐而舞。
东君蛩立在台阶上,笑着迎接众臣。他早就看见了公孙博,立即从台阶上小步跑下来,搀住公孙博手臂,笑着说:“老族长身体抱恙,又何必亲自前来呢?太后最是仁慈,怎能让您受此劳累!”
公孙博也就笑道:“太后寿诞,普天同庆,老朽也要来沾沾这喜气。侯爷才是辛苦呢!”
等进了大殿,看见国王与太后端端正正坐于王座上,公孙博心里一惊,一面跪下去行礼,一面抬头打量,却见国王面色平静,全然不像生命垂危之人,心里直犯疑,莫非鸠雅欺骗自己不成?
太后命众人平身,笑容可掬地说:“本宫本不想如此铺张,只是我儿一片孝心,非得给我过这寿辰不可!也罢,趁此机会,我也该见见诸位了。我一直深居宫中,难得与大伙齐聚,心里想念得紧哪!自先王仙逝以来,国事艰危,多亏诸位王公大臣鼎力支持,我母子二人才能走到今日。来,我敬诸位一杯!”
众臣都举杯饮酒,又跪到地上齐声称颂。公孙博留心国王举动,见他仍然不动不摇,也没喝酒,一时计上心来,跪奏道:“太后寿辰,臣斗胆请我王表率天下臣民,向天地神灵,祖宗社稷献酒!”竟是要逼迫国王起身祭祀天地,好进一步观察国王身体状况。
大殿里忽然静了下来,国王平静如初,众人都抬眼看向他。公孙博事先联系好的几位心腹亲信,都知道他的用意,也纷纷附和;太后脸上已有了尴尬神色,心里暗暗诅咒;东君蛩却抬眼看向坐在席间的东君兰,朝她递眼色。
东君兰心领神会,顺手将酒案上一盘水果掀翻在地,弄出一声响动,待众人都看向自己时,就双眉紧蹙,作势要呕吐。太后也就顺势问道:“王妃怎么了?快传太医!”
话音刚落,一名太医就从殿外低头走进来,却是什么也不问,径直就走到东君兰身旁跪下去把脉。这太医名叫公孙季,也是轩辕族人。他闭着眼把了半晌脉搏,忽然睁眼急速走到殿中,跪下去说道:“恭贺我王,王妃有喜了!”
大殿里人声喧哗起来,公孙博额头上已出了一层细汗,太后哈哈大笑。公孙季又说道:“只是王妃身子柔弱,需要静心养胎。臣下斗胆启奏我王,殿中嘈杂污浊,还是尽快让王妃回寝宫去吧!”
东君蛩点头道:“我王,太医所言不差。来人哪,扶王妃回宫,小心伺候!”
太后也转向国王说:“王儿,你初为人父,就不要为母后挂怀了,你也随着王妃一同去吧,可要多多疼爱王妃啊!”
国王自始至终没有说话,此时也站起来,早有随从过来扶住他,转过王座,朝后面走了。东君蛩举起酒杯,笑着说道:“真是双喜临门啊!来,诸位同僚,我等恭贺太后一杯!”
公孙博无心应承下去,今日之事颇有些蹊跷,可脸上还不能有所表露,强行按捺住,勉强喝得几杯,声称年老体衰不胜酒力,匆匆告辞而去。众臣也都怀有这般心思,见族长离去,也便渐渐散了。
东君蛩和太后目送众人远去的背影,在殿里相视一笑,两人又急忙朝国王寝宫走去。
公孙博回到府中,闷闷不乐坐到天黑,今日所见所闻,全不像鸠雅所说,那国王虽然举止反常,但也不像快死之人,难道是鸠雅存心说谎?公孙博之所以能历经三朝而不倒,就在于他沉得住气,现在即使一筹莫展,他还是决定等等再说。毕竟事情还没到最后关头,他是不会轻易放弃或者贸然出击的。
公孙博如同一只年迈的猎豹,他已经没有精力靠穷追不舍拖垮猎物,但他有足够的耐心潜伏下去,只要猎物丧失戒备,他就会一跃而起,咬破猎物喉咙。他现下在等鸠雅,等着鸠雅前来解释。
这一夜鸠雅并没有出现,公孙博之子早就暴跳如雷,公孙博却仍旧枯坐在躺椅上,手执竹卷静心读书。
“父亲,都到这个时候了,您还能静心读书?”
“到什么时候了?你仔细想想,我们损失什么没有?处境比先前更糟吗?”公孙博总是能一针见血,不错,其实较量并未开始,自己也还没有行动,就算这一切都是东君蛩的阴谋诡计,他也无法抓住自己的把柄。这就是公孙博之所以还如此气定神闲的原因。
“话虽如此说,可鸠雅公子所作所为太叫人费解了!父亲,您看他会不会是东君蛩特意安排下的一颗棋子?”公孙博之子见鸠雅迟迟不来,难免心怀耿耿。
公孙博将竹简搁置在膝盖上,眼里射出一道光芒,说道:“不要轻信于人,也不可轻疑于人。记住这点,往后才能走得长远!”
公孙博虽然洞彻世事,可他也料不到,鸠雅此时正陷于麻烦之中,竟是一时脱身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