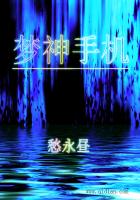“是不是有人说我的坏话了,秘密?”说话者是一个中年男子,深深的笑的皱褶横在脸上,那么繁而密,那么深,像被皱褶剖开了似的。阳光可以愜意地歇身在里面,使他的微笑像金色的阳光一样。笑的皱褶里好像还会浸出微风来,我说它怎么那么轻柔温暖呀?怎么这么轻柔温暖呀?他走在阳光中,阳光像被风吹起的灰尘一样在他头顶弥漫,沿着头顶的轮廓线徐徐往上飘动着。好像光环呀。他头发短短的,黑黑的;黄褐色的鹅蛋脸,光好像一只顽皮小狗的软舌头从侧面舔上来,舔得侧脸微微发红;穿着一件灰色的大风衣,这件大风衣几乎把他整个身体包裹住,只留出两只脚和两个脚裸,让我们端详:青色的袜子,黑色的皮鞋。这是从背后看到的情景。如果从前面看,从大肆敞开的划出八字形的前襟里能看到里面的衣服:一件又小又旧的花白毛衣裹着他宽阔的上半身显得有些勉强。作为对比,他的黑色西裤宽敞笔直,皱褶在上面随着他的步伐流畅地滑上滑下。
“怎么不回答我呢,秘密?”中年男子继续说,脸上带着和阳光融化在一起、分辨不清的微笑,“这里没有很多人看着,出来吧。”微笑像涂了胶水似的久久地粘连在他脸颊上,即使他的笑纹己经变浅了,变平了,可是融化在光里的微笑和微光一起,呆在他的脸颊上,呆在他的眼睛里。呆在脸颊上的清淡宛如轻风,呆在眼睛里的黏稠好像湿润的油漆。他的脖子上微微闪耀出淡淡的光亮,很小很淡的两抹光,它们是眸光,包裹着它们的是两只眼睛。眼睛缓缓地上升,下面的小鼻子和小嘴巴也缓缓缓露了出来,它们和鹅蛋形的轮廓一起向外微微凸出:这是一张小男孩的脸。这张脸缓缓向上移,快与中年男子的脸重合的时候,它忽然向左移,来到了侧脸上,最后来到了后脑勺上。小男孩儿的脸上,小嘴巴张了几张:“我不知道,你别问我——你什么时候来啊?我等得好苦啊。”
“快了,等我把要做的事做完。”中年男子带着温柔的笑容说。他仰着头望向前方,沐浴在黄昏之中的街道变成了金黄色,许多迎着或者侧对着夕阳的人的脸上被染成了蜡黄色;行人己经不多了,何况是在一条又窄又小的街道上。他们多半是在归家的路上,其中有个三十岁左右的男子,鹅蛋脸,贴合着脑袋的短短的平头;中等个头,穿着一件黑色外套。外套的敞开着的两笔前襟夹着白色的衬衫。他坐在街道旁边,一张旧报纸垫在屁股下面;好像在思索着什么,他凝神望着远处,眸子里的光亮仿佛很油腻,也很浓。一辆破旧的三轮车就停在面前,他应该就是其主人。
“这个世界上有太多太多的错误,”中年男子望着前方淡然地说,“世界本不该如此。有些人不该在痛苦和煎熬中度过一世,有的人不该在金钱和权利中放纵。我通过观察一个人的面相能分辨一个人的优劣善恶,可是这个世界往往黑白颠倒,无数善良优秀的人受尽社会的挤压,而上帝总是熟视无睹。但是不能把责任都推缷给上帝,造成这种现像的是我们自己。扭曲的价值观,畸形的人生观。上帝无法巨细亲躬,无法逐一纠正这些错误,他需要一个审判者,而具有洞悉人的品性的我无非是最适合的。不堪的童年、痛苦的少年生活反复地洗涤着我的神经,我相信我已足够清醒,能做出最准确的判断。要成为天使必先成为恶魔,哼哼,”他从鼻腔里喷出来一股气变成了微微发颤的笑声,“要驱散黑暗必先触碰黑暗,谁说上帝的审判者一定得是可爱的天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