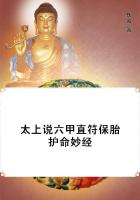路北北和夏冬青一起望着孙伯君,婆婆推推眼镜,又看了看。
“这倒没写。”他说,“但是邮件里说,让你星期一下午两点去系里见新导师,422办公室。”
“两点?”
路北北放下碗,“怎么这么急?”
“这是前天的邮件,你几天没查邮箱了?”婆婆说,“周末连着打了两天游戏?”
火烧眉毛,路北北腾地一下站起身,差点把椅子掀翻。冲出厨房重进房间,掉了一地的键盘鼠标耳麦还躺在地毯上,根本来不及捡。找不到笔记本就先拿一叠白纸,找不到铅笔就抓只签字笔凑合用,录音笔的电池暂时不用换,书包抖一抖,又是一大堆票根落在地上。
仍旧没工夫捡。所有文具塞进包里,北北抓起雨衣就往门外跑。还好夏冬青这会儿已经等在电梯前,按着开门捡了。北北一头冲进电梯,身后是孙伯君的喊声。
“你们又没人刷碗了!”
“少爷不是赔了你三十多个盘子嘛?”路北北答,“拿出来用啊。”
“就知道用新的,勤俭持家懂不懂?”
“婆婆,操心太多要长皱纹的。”
路北北说着,电梯门就关上了,婆婆的愤怒戛然而止。她抬起头,望着显示屏上的数字一点一点往下降,仍旧觉得心急如焚。他们的宿舍虽然离学校特别近,但她所在的学院位置太偏。这个时间出门,夏冬青来得及,她不行。
但身旁的夏冬青突然笑了。“你一直对读书很敷衍,可又这么害怕迟到。”她说。
“不是害怕,是习惯。”路北北答。
“这习惯怎么来的?”
“我也不知道。”
路北北答。电梯已经到了地面层,门刚打开,她便冲了出去,出宿舍拐个弯就不见了。夏冬青也向宿舍外走去。但风雨太大,她撑不开伞。迟疑了一下,她干脆直接走进雨中,反正电脑包防水。
但她不由又向路北北消失的地方望了一眼。那边的道路通向主校园外一座偏僻的教学楼。每日五人离家去上课时,唯有路北北一出宿舍就和其他人岔开了方向。不知为何,头上翘着一撮毛的短发女孩拎着书包独自走向那条小路时,夏冬青总觉得那个身影单薄又伤感。
仿佛她与他们从未属于同一个世界。
---
一手拉着雨衣帽檐,一手抱着书包,路北北在风雨中一路狂奔。从宿舍走路到学校不过几百米,但她所在的学院教学楼位置有点偏,在主校园外另一个方向,中间还要穿过一座大火车站,十分不好走。
但迟到是不该发生之事。跑过楼下小酒吧,跑过人行道,路北北冲向前方的车站广场。踏上滑溜溜的大理石地面,她这才不情不愿地减缓了脚步。
夏冬青这会儿已经到了吧,她想。我算是知道家里有个天天催着孩子念书的娘是什么感觉了,可偏偏她比我小好几岁,比谁都小。
她不由又笑了一下,这事其实C单元谁都没想到。刚刚聚齐时,大家都以为工作了一年才来英国的婆婆最大,而沈畅看着最小。但一报生日,几人却发现最年轻的是夏冬青,年方二十整。这岁数不太对。几人掰着手指头数了半天,觉得夏冬青至少是跳了两级。正要感叹夏冬青少年英才,夏冬青解释说,这在她们那里是正常的岁数。
“我五岁上学,小学是五年制,所以上到研究生正好二十岁。”
“这就对了嘛。”孙伯君一拍大腿,“小学少两年,所以比我小四岁,正好。”
“三岁。”路北北说,“你六岁上学,今年二十三。”
“这不科学。”李凯说。
“不,我们数得很严谨啊。”沈畅说,“我们从一年级五岁一年一年开始数的。”
“我是说夏冬青这脑子不科学,明明少发育了好几年,却比最老的聪明多了。”李凯答,“啊,我懂了,是婆婆的已经老化了,分不清三和四,怪不得叫婆婆。”
一言不合。脑子老化的婆婆抄起菜刀,脑子少发育几年的夏冬青掏出工程师专用瑞士军刀,李凯拔腿就跑。三人冲出厨房,冲出C单元,冲进楼梯间,三道厚重的防火门相继打开又关上,一连串巨响震得路北北头上的呆毛都晃了三晃。路北北起身凑到窗边,低头望向楼下宿舍门口。几秒钟后果然有三个中国学生窜出宿舍,保持着前一后二的完美三角阵型在街上扬起一排烟尘,不知要杀往何方。
“其实我,月份比婆婆还大。”路北北说。
但没有回应。北北回头,厨房里已经空无一人,学神回房间看书去了。
那天她的年龄成了谜,因为谁都没来得及问。而之后谁也没再想起来这件事,路北北也就没提过。一年两年三年又能差多少?大家都已经在同一所学校同一个年级读书了。
——是啊,我也都二十三岁了。一事无成的二十三岁。
雨这会儿更大了。路北北小心翼翼走进车站,而宽敞的大厅里一片空荡荡。琳琅满目的商店橱窗灯火通明,但没有顾客。咖啡厅里也冷冷清清,偶尔有一两个旅客在最角落的桌子里歇脚。被围栏小心圈起来不知是谁的人像雕塑站在大厅正中央,扬着手,抬头望着车站穹顶那一片天窗。晴天的日子里会有阳光从那里洒下,但今日,弧形穹顶上唯剩雨声。
她绕过那座雕塑,顺便和他打了个招呼,雕像仍旧抬着头,不作回应。
而车站另一端出口就在不远处,两旁有成排的巨大柱子撑起整个车站穹顶。平时路过那里,路北北永远能听到钢琴声——柱子旁有几架公用钢琴。
因为欧洲人喜欢在公共场所放公用钢琴。会有不会弹琴的人随便敲敲琴键玩,会有学音乐的年轻男孩子坐下来向女朋友炫耀一下,会有无家可归但热爱音乐的流浪汉自得其乐,也永远会有行人旅客停下来驻足围观。或叫好,或鼓掌,或跟着唱起来。几架琴,一群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一曲旋律,一阵掌声,一切仿若欧洲闲适生活的缩影。
路北北从未曾碰过这琴,甚至从未驻足,她每次路过这里都会低下头,加快脚步,而今天也一样。两旁的柱子慢慢向后退去,洒下的影子和车站的微弱灯光交织,而雨声仍旧大得吵人。路北北低着头,看着地面暗下去又亮起来,又暗下去,突然觉得少了点什么。
她抬起头,向钢琴那边望了一眼,一片空荡荡。没有人,所以没有琴声,也许是因为雨天的缘故。
就是那么一瞬间,她走慢了,望着那几架空荡荡的钢琴。两架木色,一架彩漆,一架红棕。无人使他们歌唱,他们就听雨声。
你们安静点,就最好。
路北北望着钢琴,话终归没有说出口,而钢琴依旧缄默。
她再次加快了脚步。车站出口外,地上被雨水打得起了雾,路北北再次冲了进去。街后那座灰色小楼就在不远处,她所在学院的教学楼,有位素昧平生的新导师约她两点钟见面,她就一分钟都不该迟到。
她冲进了灰色小楼,径直上了五层楼,因为天赋异禀的英国人把一楼叫地面层而二楼才叫一楼。找到五层角落的422办公室,路北北脱了雨衣扔在门口地面上,对着楼道窗户整理整理头发,稍微喘了口气。办公室的门这会儿虚掩着,安静无声,走廊里钟表时针指向正两点。
正好。路北北小心翼翼地敲响了房门,里面便传来一声请进。那是字正腔圆的英文,一听就知道是外国人。路北北有点失望,但她还是抱起书包,小心推开门,带着中国学生特有的尊师重道的谦卑走了进去。办公室里满目的书顿时让她头晕眼花,什么都看不懂。
而头顶是一句英文。“中国人?”
路北北抬起头,一个中年外国人站在书桌旁,金丝眼镜,西装革履,领结棱角分明,头发梳得锃亮。这一身行头气势十足,北北一时发愣,呆呆地答了句是。
老师便伸过手来。“西蒙·戴维森。”他说。
路北北赶紧握住,感觉这握手挺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