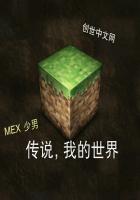当晚明琅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展麟在下边地铺上听着他不断翻身,亦是了无睡意。有心开口相问,又怕触碰到明琅的哀痛之处。
他猜也能知道,明琅小的时候必定经历过一些惨烈到可怕的事情,以至于淡漠如他,居然因为看见红月亮,而丢魂落魄,大失常态。他真的很想替这个打心眼里疼着惜着的好兄弟担待一二,可是明琅不肯开口,他也莫可奈何。
一晚没怎么睡熟,到得第二天,展麟见明琅好像有些精神不济,问他要不要再歇一天,明琅却摇头说没事。
不过展麟还是担心,本想缓缓而行,只是明琅默不吭声催马在前,展麟也只好紧紧跟上。当天下午抵达顺德府,在展麟的坚持下老早入城找到一家大客栈住下。明琅又是一晚上睡不安枕,到早上起来吃早餐的时候,终于按捺不住跟展麟说道:“这里离冀州应该不远吧?要不我们改道先往冀州去一趟吧?”
“往冀州去干吗?”展麟立刻反问,“我们跟任兄弟约好了要在真定见面,若绕道冀州,要多走两百多里路呢!”
明琅转眼他顾,好一会儿,才幽幽开口。
“我爹有个故友是在冀州,他一再嘱咐我倘能抽出空来,最好能去拜访一下。反正现在离九月十八日还早,大不了耽搁几天功夫就是。”
他说得很轻,而且一直不看展麟的眼睛。展麟明知他不过是一整天好不容易编造出的借口,却不能挑破。想着前晚他才因为看见红月亮而大失常态,今天忽然就说要去冀州,只怕冀州的这位“故友”并非与明老爹有关,而是很可能牵扯到他自己所言的那件“很不好”的事情。
但既然明琅不肯明说,或许这一趟冀州之行,他能够自行瞧出一些端倪来。
“既然如此,就往那边走一趟就是。我是没关系,你想去哪儿我都陪着,我就怕你身体弱受不了。”最后展麟这样回答。
于是改往冀州方向而行。一路明琅情思恍惚,魂不守舍。展麟明知他怀有心事,却不敢揭穿,只是不断制造话题逗他说笑。
第四日中午时分到达冀州。先找一家大客栈订了一间上房,就在客栈附近找一家特色酒楼吃了中午饭,之后明琅便急着要去寻访“故友”。展麟自然依他。
从东城门出去,明琅先跟人打听到刘家坪的方向,之后纵马行约小半个时辰,便看见一处村庄。展麟跟在明琅马后,眼见越近村庄,明琅反而渐行渐慢,到最后甚至跳下马背,眼望着村庄方向,一手牵着马儿,呆呆地站立不动。
展麟也随着跳下马背,静静地等了一阵,见明琅始终不言不动,不得不挨近他身边,轻轻问出一声:“好兄弟,你若不想走了,那咱们就回去吧?”
明琅呼出一口气来,向着展麟勉强一笑,转脸见不远处有一个村民探头探脑,遂向那村民走了过去。
那村民见他衣着清贵,样貌不俗,隔得老远便点头哈腰满脸赔笑。等到明琅开口循问“刘财主”家在哪儿住,那村民更是主动引着二人走进村里,一直走到一处高宅大院,又抢上台阶替明琅叩响门环。
一会儿大门打开,一个中年男子探头出来一瞅。那村民不等中年男子开口询问,先陪着笑脸向着明琅伸手一指:“这位贵人打听府上住址,想是府上的客人,所以小人引他过来!”
中年男子向着展麟明琅一望,赶忙开门迎了出来,向着展麟明琅深深一揖。
“我是刘府管家,不知两位爷大驾光临,未曾远迎还望恕罪!”
“我们也是从冀州路过,顺便来府上拜望!”明琅听说他只是管家,便不回礼,只是淡淡回应,“你进去帮我们通报一声,就说有两个晚辈特来拜望刘英刘老爷子。”
“你说我们老太爷?他已经……”
那管家话说一半儿,眼见明琅神态冷淡,赶忙收回话去,躬身作势先请展麟明琅进入院门,在正面靠右的一间客堂里坐定,一边命丫环上茶,他自己告了退,亲自去请老爷出来。
展麟见院落虽然宽敞气派,但墙瓦老旧,木雕破损,看来该有四十年以上光景。不过也幸好刘家数十年不曾挪窝,要不然今日就不可能这么容易找到门上。瞅瞅明琅,却见他面色木然,正襟危坐,不知心里在想什么。
没过多大会儿,便有一个衣着华贵的男子匆匆走进来,看年纪五十上下,富富态态白白净净,一看就是财主模样。
展麟明琅赶忙站起身来,那人抢先向着两人拱手一揖:“不知两位贵客从何而来,找我爹爹是有何事?”
“晚辈是从南方过来!”明琅回礼作答,貌甚恭谨,“只因家父多年前曾受过刘老爷子恩惠,所以这次晚辈北上京城,家父一再交代在路过冀州的时候,要来府上拜望刘老爷子!”
“原来是这样啊!”那人不由得轻轻一叹,“我爹爹一生乐善好施,惠人无数,只可惜……他已与两年前病逝,两位贵客来得晚了!”
明琅“啊呀”一声,一句问话脱口而出:“那那那……老夫人呢?她怎样?”
“我娘她……”那人脸上愈现黯然,“早在十多年前,就一病去世了!”
明琅跳起身来,再一次冲口发问:“十多年前,老夫人……她才五十多岁,怎么就会……?”
那男人上上下下打量着明琅,眼见他清俊绝世,一见难忘,实是生平从未得识!不由得满腹狐疑,先不回答他话,而是反问一句:“不知贵客尊姓大名,怎么……我从未见过贵客,贵客却对我家里情况如此熟悉?”
“我姓明。”明琅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我小的时候,曾在京城……见过老夫人,也曾受过老夫人格外看顾!”
“原来如此!”那男人口中如是,脸上疑惑却未尽消,“只是……我娘虽然去过京城,却已是十七八年前的事情了,看明公子的年纪……顶多只有十七八岁,就算见过我娘,又怎么可能记得?”
“可我真的记得!”明琅喃喃而语,竟不由得哽咽了一下,“我今年已经满了二十岁,最后看见老夫人,是我将近四岁的时候。老夫人……慈祥和蔼,待我……就像我的……至亲祖母,所以……我都记得!”
“明公子能够记起四岁以前的事情,而且记得如此清楚,当真是十分罕见!”那人点一点头,禁不住长叹一声,“明公子有所不知,我有一个妹子嫁给了京城一位姓赵的富商为妻,我娘将我这个妹子看作掌上明珠。在我妹子怀上第二胎的时候,我娘说她第一个孩儿也还年幼,生怕她太过劳累,还专门去京城陪了她几年。明公子倘若真与我娘见过面,想必就是在那段时间。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就在我娘从京城回到冀州不久,我妹子一家……就惨遭横祸!我娘得讯,当时就昏厥在地,之后没过多久,就一病去世了。”
那男子见明琅真情流露,许是心生感激,这番话说得甚是详尽。明琅听着面色苍白,摇摇晃晃。展麟赶忙伸手将他扶住,轻声问了一句:“兄弟你怎样?”
明琅摇一摇头,只是两眼看着那男人,慢慢再问一句话:“却不知……两位老人家灵位在哪儿,晚辈既然来了,能否容晚辈去给两位老人家磕上一个头?”
“明公子能有此心,刘某感激不尽!刘某忝长几岁,明公子若是不弃,可唤刘某一声大叔,刘某便高兴得很了!”
明琅赶忙躬身作礼,口称“大叔”。展麟也跟着一礼。刘财主伸手将二人扶起,引着二人从侧门出去,进了一个小院落。院落里只有两间正房,两间偏房。
刘财主伸手推开正房大门,只见里边素幔张挂,挨着正墙居中摆着一张灵案,灵案上两座灵牌,灵牌下供有香炉。想是三年孝期未满,香炉里香火不灭。
明琅跨步进去,拜伏在地良久不起。展麟也在他身边跪下磕了几个头。刘财主则肃立在灵案一旁躬身回礼。之后展麟扶起明琅,眼见明琅眼眶红润,一时却不能安慰。
刘财主本来见明琅人才出众,已经对他十分喜爱,此时见他诚心拜祭,虽不知他何以对自己的爹娘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心中却也更增好感。等展麟扶着明琅走出灵堂,刘财主不由得伸手向着左首一间偏房一指。
“明贤侄既然记得我娘,想必跟我妹夫一家人也都认识。只可怜他们一家老小全都惨遭不测,竟没有后人供香祭灵。所以我爹命我在此为他们一家五口设下灵位,每年清明寒食,也让他们受些供奉。”
明琅浑身一颤,不由得向着那间房走了两步,这才回脸看着刘财主。
“大叔说得不错,我的确记得……赵家娘子……对我的恩待,所以……能不能容小侄……也进去给他们上柱香磕个头?”
“当然可以!”刘财主忙紧走两步,推开了偏房大门。
明琅迈步而入。展麟跟在后边,眼见明琅脚下虚浮,竟似有些走不动的样子,忙又伸手扶住他的手臂。
抬脸一望,只见屋里同样挂满白幔,正中靠墙摆着灵案,灵案上五座灵位,正中两座分别写着“赵灵安之灵位”、“赵门刘氏之灵位”。想是外姓所供,没有注明供奉人与逝者间的关系。另外左边两座分别写着“赵灵安长子运强之灵位”、“赵灵安次子运生之灵位”,右边一座写着“赵灵安长女宝华之灵位”。
展麟总觉着“赵灵安”这个名字好像在哪儿听到过的,眼见赵家一门尽绝,不由得心中亦生悲戚。明琅更是按捺不住,拜伏在地啜泣难止。展麟忙在地上跪下磕了头,便挨到明琅身边柔声劝慰。
刘财主眼瞅着明琅居然哭得浑身抽搐,心中更是疑惑难解。等明琅好不容易在展麟扶持下站起身来,刘财主终于按捺不住再次询问。
“明贤侄伤心成这般模样,莫非跟我妹夫一家……竟是有着什么亲眷关系?”
“倒没什么亲眷关系!”明琅脸上泪痕未干,却立刻摇头否认,“只是……我幼时家贫,我爹娘都曾受过赵家恩惠!如今……见赵家一家人全都遭遇不测,难免心生悲戚!”
刘财主道了一声:“原来如此!”心中仍有满腹狐疑,但人家不肯说,他也不好追着问。
(请看第三十七章《力锁惊马引窥伺》)
【注:明天休息一天,后天继续更新。一路暖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