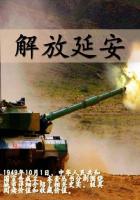朱育才左手托住陈桂枝的小腿,右手便在脚腕处轻揉,忽然用力一托就矫正了。
陈桂枝本来给他揉得挻享受的,给他突然来这么一下,痛得“哇”一声,泪水流了出来。
钟福、钟寿坐着斜坡试穿日本皮鞋。
钟福道:“头领,你来一双么?”
朱育才淡淡应道:“不要!好了,我要去找玉婉她们。你收获的东西就归你,拿回去吧。钟寿你要是跟我就一起走。”说着扶起陈桂枝。
钟福个头长得高大,脚板也粗,长年累月赤脚爬山,脚板变了形。剥来三双皮鞋没一双合适的。听得朱育才把东西全归自己,又叫自己回去,显然不对路数。当下鞋也不穿了,赤脚跳起身,道:“哎,等等,你什么时候回去?”
朱育才道:“怪了,这是我们的事,我想几时回去就几时回去,难道要你批准?”
钟福笑道:“嘿嘿,我不是哪意思,不如我也跟你一起走吧?”
朱育才摇摇手:“别,你还是自己走吧。”
钟福祈求道:“我知道,原先是我不对。你是大人,大人就得有大量,原谅一次。”
朱育才:“我们之间再没什么关系了,谈不上原谅不原谅的。”
钟福发怒了,大声道:“不成,我们之间必须得有关系!是男人大丈夫的,就得跟我锣对锣、鼓对鼓、面对面的说道说道。否则你就不配做头领。”
朱育才:“呵呵,照你说得这么蛮横,我们非得来个‘说道、说道’不可了?”
钟寿提着一只皮鞋,神情显得特别恐惧,紧张得大声喊:“哥,鬼呀!这鞋子自己会出血!”差点将鞋子扔到了河里。
原来钟寿把三双鞋试个遍,勉强找到一双。可是不知怎的,原来只有泥巴的皮鞋竟有点点滴滴的鲜血,再一看手背上也沾上了。
钟福恶声道:“闭嘴!我说正事!小心我揍你!”
钟寿道:“不信你过来看看,真的出血。”
钟福想过去看,又怕朱育才走掉,道:“你不能走!不准走!”就朝钟寿走去,走得二步又不放心,扭转头来看。
陈桂枝看不顺眼,道:“你怎么说话的?凭什么呀?”
朱育才道:“他是情急智浑、口不择言,别理他。”听钟寿说得这么怪异也想看看,走了过去。
原来钟寿的左手臂,不知何时给子弹擦去了一层皮,血从伤口顺着衣袖沥沥往下滴流,自已懵然不知。
钟福道:“操!我说你蠢,还真的不是一般的蠢,自己受伤了懵查查,还说鞋子出血!”见朱育才走开,又大声喊:“喂,你去哪?不准走!”
朱育才:“你不见他受伤了吗?找药去!”
朱育才就堤埧上找来几种嫩藤绿芽,用口嚼烂给钟寿敷上包扎。
钟福见钟寿的伤口不一会就止住了血,不由得你不服。待朱育才从河边漱口回来,走到近前很真诚地道:“头领,其实我对你十分、非常佩服到五官投地的,就不要赶我走好吧?”那年代,五官这词并不流行,钟福不知在哪学得,想在朱育才面前显摆就套用起来。
说实话,这是钟福破天荒跟人认错说软话。
朱育才起初不明,道:“什么五官投地?五官投了地,还得了?”
钟寿高声道:“大哥,你错了,是五体投地,不是五官投地。”
钟福恶声道:“你懂个屁!我说五官投地就是五官投地!叩首、磕头还不一样?你非要说成五体投地,说得出哪五体吗?”
钟寿道:“我当然知道,头、手、脚……”
钟福:“才三样。”
钟寿:“还有……还有腰和屁股,这不是五体么?说你没文化还不服!”
此言一出,朱育才顾不口中苦涩哈哈大笑,笑了好一会,道:“你哥俩都有文化,可以考状元了。”
陈桂枝听得钟福把五体投地说成五官投地也觉好笑,只是不明白朱育才笑什么,道:“钟寿说错了?”
朱育才:”先前钟寿就答对了。五体指的是头、二只手加上二只脚,给钟福一逼就真成了画蛇添足。可我真不明白钟福如何能做到五官投地的!”对兄弟俩道:“我对钟福佩服得‘五官投地’,对钟寿佩服得七体投地。看在‘五官投地’的份上,我们继续来说道、说道。”
钟福大声:“好,是条好汉!在水头我拿别人衣服,你不让,还说要崩了我!现在听了你的,把人家的鞋子也夺了,还是要赶我走。这是为什么,是不是喜欢就翻手为云、不高兴就覆手为雨?”
朱育才见钟福老整些成语出来,也大声道:“这点我就跟你讲清楚:一,在水头,联防队人刚成了俘虏,你不控制俘虏倒去抢人家衣服,这叫做轻重不分、急缓不辨、本末倒置、舍本逐末。二,你不听指挥、目无上级、自以为是、战埸抗命,人人像你这样还得了了?三,我们如果连俘虏的衣服都搜括的话,岂不是和土匪打家劫舍、抢掠财物、为非作歹一个模样?这就是本质上的区别。现下我让你去脱鬼子的鞋子,因为鬼子已经硬翘翘了。这又是生死间的区别。再说鬼子的东西不比你身上破布鞋值钱多多?难道你不想收益改善生活吗?”
钟福:“唔,好像有点道理,可是,我还是要问你:是不是跟你喝过血酒就是兄弟,没喝的就不如别人,就不拿我当兄弟?”
被钟福一激,朱育才真的来了气:“你扯蛋!我并没把你当另类看。我是担心你这只蛮牛不听指挥、不听管教、不听命令,一不小心反而把你杀了!难道你没听过‘违抗军令者,斩’?!”
钟福听朱育才口气凶恶,心却软了。事情有可能挽回,就使出个“打蛇沿棍上”的办法:“我对天起誓!对神灵保证!从今以后全听你的话!为你赴汤蹈火、两肋插刀……总之,什么都成。如果哪一天我不听你教,打也成,骂也成,甚至把我崩了也死无怨言。不过你那点穴功夫就免了,呵?”
朱育才道:“少跟我耍花腔!前几天,我就叫你别叫我做头领,你听了吗?现在你都还在叫。”
钟福笑道:“嘿嘿嘿,我都说了,我错了,请头……请队、长、大人恕罪!小人给你赔礼!”
朱育才道:“这倒不用。你若是真心想留下来,我们就来个约法三章。你记住:我做事是‘事不过三’的,你已经犯了二次,再没机会再犯的啦!”
钟福道:“成,别说三章,就三十章、三百章都成!”
朱育才道:“听好了,一,一切行动听指挥;二,不许打人、骂人!”朱育才对昨天那句粗口仍耿耿于怀。
钟福:“对谁都不成?”
朱育才:“对!包括你这位亲兄弟。”……
钟福掐着手在静静听,纠正道:“不是亲的,是叔伯兄弟……说呀,没啦?”
朱育才:“没啦。”
钟福:“还差一章呢?”
朱育才道:“你可以‘五官投地’,我也可以‘约法二章’。跳到河里去!”
钟福:“现在?为什么?”
朱育才:“别问为什么,跳不跳?”
钟福:“跳!”
钟福衣服也不脱,果真跳到河里。河水齐腰深,钟福在水里扑腾几下,使出狗爬式游起水来。
过了一会,朱育才道:“成了,上来吧。”
钟福马上就上岸。
朱育才又道:“找个地方拧干水。”
好一阵子,钟福才从竹林走了出来。其时,还是天寒地冻的,钟福冻得嘴唇发紫。
朱育才指着狮子岭道:“你们看见那山脚砖窑没有?朱沛居他们就在那里。我们顺着河堤往左边绕过去,那里有条山路直通瓦窑口,到那去和他们会合。”
钟福颤抖着,背上从鬼子那缴来的物品,道:“冷呵,我跑步先走,你们后面来。”
钟寿追了上去:“大哥,等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