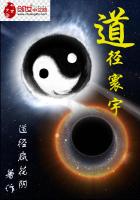天色渐黑,寒风瑟瑟,划过树杈,带落一片落叶。一行人打着灯火,浩浩荡荡地往流风主阁走去,正是押解凌月寒的一行人。
只见凌月寒双手戴着手铐,左右伴有看守的弟子,步履蹒跚地往前走去。幸好他胜出大比,事情又尚未明确,身旁的弟子还算以礼相待,不会使他太过难堪。
走在路上,凌月寒念头连动:“整件事环环相扣,便是看准我难以即时应对之故。那布局者储心积虑,倒是费煞心思了。”转念又想:“我光明正大,于对质时自会早落石出。”
进入主阁,只见灯火通明,两列人众立于两侧,段流风和长老群则居中而坐,气氛凝重。当中一人目无表情,双目透出冷意,正是王涛之叔王洪。而王涛则立方于弟子之列,见凌月寒走入殿内,幸灾乐祸地嘻嘻冷笑。
见其神色,凌月寒心下微寒,想道:“此人心胸狭窄,实为最有可能诬陷我之人。但以他的能力,绝不可能造成那有如外家重手的致命伤。难道他还有其他实力高强的余党?”
段流风于主阁等候己久,见弟子禀告已然寻到嫌犯,便欲详加审问。岂料被押解的,竟是他极为看好的凌月寒,也是眉头一皱,甚是愕然。
但他亦不能因一己好悪而定其为人,听过长老之言,便向凌月寒问道:“凌月寒,你何以不让执法弟子搜身,甚至以重手杀人?”
听见阁主之言,凌月寒面容不改,侃侃而谈:“那名弟子非我所伤,凶手另有其人。在师兄调查之时,房外有人将界力压缩成拳掌之形,遥距施以偷袭,方致师弟身死而已。”
“凶手时机把握极凖,下手之后不到两息,门外的师兄己入房内。若我那时前往追查,倒是显得内心有鬼了。因此,作为房内唯一的人,我便理所当然被当成凶手了。若我有意杀他,又岂会容他发出声音?”
段流风见过他的表现,知其身手不凡,内心微微点头,认为此言确似不虚。
然而,单凭此点,却不足以推翻嫌疑,便朗声说道:“单凭一言两语便放行,只怕旁人也会不服。若你心中无私,可敢让我遣人一搜你身上之物?”
凌月寒气定神闲,应道:“阁主请搜便是。”段流风便着左右之人检查他身上之物。
两人一搜,只有棕红徽章和袁月给他的包裹,除此再无一物。其中一人打开油包,却是一块刻有奇特花纹的玉珮,在灯光下闪闪生光。
“阁主可见我身上,除了私人物品及弟子信物外,再无一物,那又何必杀人灭口?”凌月寒见身上无可异之物,便即开口道。但在望向段流风時,却见他神色一沉,心下略感不妙。
果然,在下一刻,段流风的脸色变得鐡青,沉声问道:“你倒会诡辩,但你身上焉有什么信物?我只想问你,你如何解释身上所持的奇道谱?”
原来那面玉佩,并非弟子信物,却是由核心弟子寻回,对流风阁极为重要之物。这正是刻有奇道修炼缐索,号称界图之秘的奇道谱。
奇道谱外观各异,只能透过其上刻有的纹路辨认而出。载于其上的信息,有的直截了当,有些却须苦苦思索方可寻得。然而,每样奇道谱皆有一共同之处,便是举世难寻,并为天下人所苦苦寻觅。
这却是因为,每件奇道谱,皆载有修炼界图上最为神秘莫测,却又威力极强的奇道之法。当中最为人所知的,便是愿皇所习的界天道,其力之强,足以撼动命运。因此,虽然每件所含的信息极少,其价值却是不可估量。
凌月寒见他神情大变,已今日之事难解。直至听到奇道谱之名,更如睛天霹雳,大为惊讶。他性格虽然沉稳冷静,此刻却是神色一变,心绪混乱。这却非身处困境之故,而是因为此物,由袁月所给。
只因对袁月的信任,他才从未怀疑过油布所包之物。不料,却是因此被摆了一着。
想到此处,凌月寒一直尝试理清的脉络登时变得混乱,心情五味交陈:“若为王涛所为,便是群党众多,也无问题。但我与袁月一直相交甚笃,甚至为他出头。我早已把他当成朋友,他却为何陷我于不义?”想到袁月清澈纯净的双眼,绝对不似作伪,心中不禁怅然。
处身此局,凌月寒却不放弃,问道:“敢问阁主,此物于何时弄失?”段流风见他不作辩解,反作此问,也是不解,却回答:“发现此物遗失之时,巳近黄昏,距今已有快两个时辰了。”
听到此处,凌月寒眉毛一掦道:“我整个早上皆在修炼埸苦修,而下午皆在医疗室与袁月闲聊,将近入夜方回住处,又何以抽空盗取信物?若阁主存疑,大可寻楚傲天与袁月至此,他们自可作证。”
段流风闻言沉吟,便叫人传过二人,到此作证。不到一会,楚傲天已到阁中。看到凌月寒被人质问,神色狼狈,也对之投去疑问之色。
只闻阁主略为说明事件,便問楚傲天:“你于正午之时,可有在修炼场与凌月寒相遇?”楚傲天闻言回道:“此事真确无误。而且,以凌兄的人品,绝不会作此偷鸡摸狗之事。”语罢站至凌月寒身旁,对他微微点头。
虽然相交不深,楚傲天却为己作辩。凌月寒心下甚是感激,暗暗记在心中,也报以一个微笑。
再过数刻,只见传讯弟子搀扶着一名身板单薄的少年入阁。那人面容清秀,不脱稚嫩,正是袁月。
袁月看到凌月寒的身影,也是大为欢喜,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但见他身处困局,便转至皱眉,暗暗担心。
凌月寒见他走路时蹒跚不定,远不如下午般行走自如,心中只觉略不寻常。但见他神情自然,竟似不知奇道谱一事,也感不解。
听过来龙去脉,袁月便睁大双眼,眼神坚定地道:“我敢以人格担保,凌月寒绝不会作此事,定是受人诬陷而巳。”凌月寒见他为己发言,维护自己,心下也是略松,只觉他并无出卖自己之兆。
段流风自不会如此儿戏,就此作罢。他接而再问袁月:“那你在中午之时可有见过凌月寒?”
“自比试之后,我一直在自身居所休养,却至此时方再相见。不过,我肯定凌月寒不会说谎,当中必有误会。”袁月神色一滞,双目黯然便道。
听见袁月之言,凌月寒则是双眉深皱,张口欲言,却又不知可说什么,內心想道:“若无不在埸证据,此事实难摆脱。然而,袁月之言却不似谎言,却是为何?”望向袁月,只见他双眼满是关怀之色,对未能作证甚是焦急。
凌月寒心中整理所有讯息,但觉迷雾重重,却又似捉住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