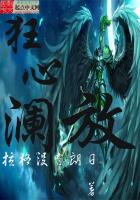王寂惺呆呆坐在葵公子为他特设的“宝座”上,座位旁还立了一面大旗,上书镶金边的“帅”字。他瘫软着不动,回想起许多往事,许多过去不久而刻骨铭心的事情。父亲、母亲、薛月都在他眼前晃,这些至亲挚友都捐弃了尘俗物质的肉体,回归到最为纯粹的“真如”,他想总有一天自己也会突然丢弃行走的“傀儡”,精神上不再有丝毫滞碍。如今,家人们早已轮回了吧?浑浑噩噩、惊慌失措地度过或长或短的中阴时期,最后仍是选择了一个崭新的躯体吧?暂时的心安理得背后掩藏了辛酸,漫长的寄居与转居让人在怪圈里不断循环,每个生命早已疲劳,但仍是不由自主地在主家的领地搬进搬出,什么时候才能有一处属于自己的永久居所呢?
王寂惺望向山头上的旗帜,现在该是什么风向呢?薛月的“离合风”还有多久到来?前不久听说断霜道长去三弓山取回了薛月的骨殖,带往寒林安葬,她最后也算与父母团聚了吧。
人生总是充满烦恼忧愁,无独有偶,三弓山罗军师也躺在他的太师椅上思绪万千。玉之精“岱委”又一次让老罗大泄“五十行”,罗军师此刻冷静下来,意识到必须降低“双修”的强度,还有,三弓山和玉莲教的事务不能再放任不管了。上次,趁着皇帝老儿驾崩,派人前往京都“捞油水”,小犊子们损人折马无功而返,反倒冒出一个大献殷勤的王不留行,这一比较,曾大当家对他老罗确实暗暗责怪。仔细想起来,“无事献殷勤,非奸即盗”,老王的动机真他妈不纯。不过,客观上,老王带来真金白银,的确向老曾交上一份令人心动的“投名状”。
“兜率君!”总管欧阳素青忽然打断了王寂惺奔腾的意识,“兜率君,大头领……不,是葵公子请您赏鸟!”
“赏鸟?什么鸟?”
“古怪的鸟!”
王寂惺懒懒地走往庭院,见葵公子、羊刃、令君山等人都在,围着什么在瞧稀奇。挨近一瞧,竟然是只火红的大鸟,有半人高,却只有一只脚!
葵公子对王寂惺道:“兜率君可识得此鸟?”
王寂惺道:“不认得,《山海经》有记载么?”
葵公子道:“此鸟名叫‘必方’,是火之精灵,《山海经》有载。”
羊刃高声笑道:“这大鸟儿,红得喜庆,肯定是祥瑞之兆!”
令君山也道:“一枝独秀,好征兆!”
葵公子拿出一道黄符,展开了,贴到必方的头上,那大鸟顿时便萎靡下去,被吸入符纸之中,符纸自然化为折叠的三角形,被葵公子收入囊中。
葵公子拉住王寂惺的手,一同回了兜率堂,欧阳素青端上两杯茶便退了出去。
葵公子伸手拔了头上的珠钗,秀发如瀑布一样垂下来,更加映衬出她的娇美可爱。
“今天洗了头发,还没干呢!”葵公子松松长发,王寂惺闻到怡人的馨香。他看着葵公子,不知不觉发了呆。葵公子的脸蛋突然绽放了两朵粉红的桃花。
“兜率君?”
王寂惺不应。
“王公子!在看什么?”
一语叫醒梦中人,王寂惺的神识从遥远的东北寒林被拉回来,只将炊烟和故颜遗落在小木屋里,神识入体顿时化作思念的陈醪。
葵公子笑了笑,说道:“寂惺,这里还住得习惯吗?孤山清冷,真能消去人心浮躁,但也能抹掉人的斗志。这连绵群山自能抵御百万大军,却遮不住天下人的冷眼热眼,朝堂和朝野总有数不清的魑魅魍魉打着这清净之地的主意。”
王寂惺道:“你有什么计划吗?”
葵公子拿出刚刚封存的三角符纸,道:“山有形,人有体,形胜所在,人力难克,不过,鬼神妖魔就不一样了,空间阻碍算不上什么,现在,妖怪们来了。”
“九木岭鬼门洞开,确实成了妖魔的渊薮。”
葵公子又道:“我弥勒圣境、兜率内院都出现了‘必方’、‘倚’这样的妖怪,看来有人已经在行动了。”
王寂惺疑惑道:“你是说山上妖邪的出现不是偶然?”
“当然不是!这‘必方’鸟本就是窃取情报的探子,才不是闲庭野鹤!”
“小心点确实有必要。”
葵公子道:“我现在有个打算,想先派出一军试探各方的虚实。如今形势,小打小闹居多,还没人敢迈出那惊天动地的一步,但这一步也不能由我们走,最好‘抛砖引玉’,引出些风波来,最后才能翻天覆地!你以为如何?”
王寂惺喝光手中的茶,淡淡道:“我不懂,全听大头领的号令。”
这时,欧阳素青匆匆赶进兜率堂,神色有些慌张,向堂上二人禀报:“二位主公,适才藏书阁发出异响,据卫士说王仙儿姑娘被两个妖怪给掳走了!”
葵公子打翻茶盏,嗔道:“欺人太甚!”
“我去看看!”王寂惺倏地跃起,冲出大堂,径往后山千佛窟藏书阁去了。
原来王仙儿近来都在藏书阁待着,想从故纸堆里理出些头绪。鬼门开后,父亲又托了几次梦,但是他相貌模糊、语焉不详,让王仙儿十分揪心。这日在藏书阁翻阅卷宗古籍,遍寻无果,王仙儿不由得神思昏昏,忽听窗外一声呼哨,一双狰狞青鬼跳了进来,张牙舞爪捆住她的手足。王仙儿大惊,奋力挣扎,但手足上的绳索就如铁丝一般挣不松半寸。她大喊,后山卫士已是听到了,但二鬼的动作更是麻利,将王仙儿拖翻在一张肩舆上,呼喇喇担着跑了,一眨眼就消失在丛林中。卫士只瞧见两个状若夜叉的妖精带走了一个缁衣人,再发现藏书阁大门都歪了半扇,方才意识到是王仙儿被绑了,那个曾顶撞过大头领的女人。
卫士将将想到一句“女人何苦为难女人”,鱼雁堂的传信使就来了,很快,消息传到欧阳素青那里,欧阳总管立刻禀报了二位主公。
王寂惺的“神足通”已经今非昔比,葵公子若要追他,自然是少了腿劲。他先到藏书阁,早不见了人影和鬼影,顺着卫士指点的方向,他追下了山。一路山风射眼,两旁猿啼悬耳,远远见到个穿红着绿的人,竟是木下三郎。
“木大哥!你哪里去?”
“哎哟,王兄弟,仙儿被绑了,就在前面,你——你带我一程!”
王寂惺拉住三郎,二人狂飙骈进,顿饭工夫后,隐隐看到前方有两青鬼抬着肩舆纵跃跳闪,肩舆上分明就是王仙儿。
王寂惺急催“神足”,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二青鬼在前方不远处急行,始终没有逃出视线。
二人心里纳罕,但鬼神之属本就有各种各样的神通,没什么稀奇的,意料之外却又是情理之中。
追了半日,早穿过崇山峻岭,远离页尔山的地界,王寂惺尚且穷追不舍,木下三郎有点受不住了。前面两个青鬼扭头一笑,露出森森獠牙,忽然发了狠,旋踵跃起,连着肩與消失了。
王寂惺再狂追数十里,失了青鬼踪迹,正没理会处,见道旁凉亭里有个长须博冠、金带白衣的中年男子在休憩,他侧卧于竹席,手中摇着把宫扇,闭着修长的丹凤眼,怡然自得。
王寂惺上前作揖道:“员外有礼了,敢问员外适才是否瞧见有两个青面獠牙的妖怪抬着一个姑娘经过?”
白衣员外半开双眼,微启丹唇,答道:“青天白日,哪儿来的妖怪,年轻人莫要捉弄老夫!”
木下三郎已是瘫倒在地,上气不接下气,眼冒着金星,他强自言道:“贵老先……先生好兴致,大白天在这幽篁深谷里遣怀,莫说妖怪跑过,就是树叶子掉落,应该都能察觉吧?”
贵老先生员外摇了摇扇子,慢条斯理说道:“倒是有阵疾风往西北去了。”
“谢了!”王寂惺拽起三郎便走,匆匆踏上西北的古道。
白衣员外坐起身,望着西北吐出幽幽的一口气:“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这等破事儿,谁愿为之!”用扇子拍了拍朽坏的栏杆,凉亭后的竹林里显现出一对青鬼来。柔软的落叶上放了肩與,王仙儿坐在與上安稳睡了,一只透明蠕虫从树梢悬丝而下,悄悄落在王仙儿的衣服上。
疾风往西北,穿过瘟疫爆发的村庄,差点刮倒施药救人的济苍先生。海潮小和尚扶住了刘济苍,一面喊道:“好大的风呵!”
济苍先生刚刚站定,那怪风又奔了回来,吹闪了老先生的腰。
“先生!海潮!”话音甫落,王寂惺和木下三郎站到了刘济苍面前。
刘济苍和海潮在遭遇“天魔喜”白先生后,一路向页尔山进发,除了久溺于妖魔侵扰,还缠绵在瘟疫救济之场、奄奄一息之家。救了不少人,收了不少尸,刘济苍和海潮心里悲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场景是他们不想看到的,然而事实却是无比残酷。
刘济苍和海潮都瘦了,脸上的肉快兜留不住掩藏口鼻的方巾。济苍先生很激动,王寂惺的从天而降给予了他莫名其妙的巨大信心和力量。
海潮扯下方巾,扑向王寂惺,将他抱住。
“寂惺哥哥!”
三郎萎坐于地,喘气道:“不是冤家不聚头,天下这么大,这还能遇上!”
王寂惺对济苍先生的看法虽然与最初不同,但是经历了许多事后,他知道济苍先生并非处心积虑的人。玉莲教的创教始祖又如何?如今玉莲教的所作所为是罗文正授意的,与济苍先生何干?太祖创立圣朝,现在让不肖子孙给败坏了,前人建房,后人毁梁,太祖爷又如之奈何?王寂惺将这些都想过了。
不待刘济苍开口,王寂惺便道:“先生可曾见到两个青面獠牙的妖怪经过?”
济苍先生道:“发生什么事了?”
三郎呼天抢地大哭道:“仙儿被他们给劫走啦!”
“被谁给劫走了?”
“两个青面鬼!”
济苍先生望望海潮,道:“青面鬼倒是见过,不过那是数日之前的事了。”
王寂惺急道:“刚才有人说朝这边来了!”
刘济苍道:“贤弟莫急,我二人虽没瞧见,但这些时日也接触了不少鬼怪精灵,待老夫问问。”说着从药箧里取出个一指长的小葫芦,打开抖了抖,倒出个屎壳郎。
“三郎啊!”刘济苍道,“你可听说两个青鬼绑架一位姑娘的事情?”
木下三郎吃惊不已,瞪大了眼睛,龇着八字胡,问道:“这屎壳郎叫三郎?”
海潮道:“对啊!它是我们路上收的小妖精,最是消息灵通!”
三郎来了气,骂道:“成何体统!你个屎壳郎叫什么三郎!污了三郎我的名声!”
济苍先生挥挥手,示意别吵,他把耳朵贴近屎壳郎,听了半天,点点头说道:“三郎说两个青鬼乃是‘天魔喜’的鬼仆,极好辨认,最近比较活跃。绑架的事不清楚,以前从没听说过,要说是‘天魔喜’授意青鬼劫人,它是不信的。”说罢取了一粒粉红的药丸喂给屎壳郎。
王寂惺问:“‘天魔喜’是谁?”
海潮道:“是个高帽子、长胡须的中年男子,穿白衣服,好像就姓白!”
三郎拍手道:“是他!”
“快回去!”王寂惺也不多说,迈开神足,狂奔回幽谷凉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