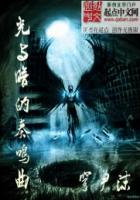今天是上班的第十天。
我交上去的销售计划书,被三文鱼退回来了五次。每次退回都不给理由,就跟你说修改,不符合要求。具体哪里不符合要求,不说。他和我之间不存在直接交流,只有那个正经脸的秘书在当中传话,传话还有道具,就是你之前看到的那只体积庞大的录音笔。正经脸每日早上十点准时出现在我这里,端出一张服务于党政频道海峡两岸的脸,播放一则三文鱼的一句话新闻,然后甩给我前一天才交上去的计划书。
在我毕业之后,从业到现在的数十年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每天上班都像是在演出情景剧。
特别荒唐。
今天上班之前,快走到店门口的时候,我老远就从后面看到了那个正经脸秘书正在往店里走。
她应该又是来退货的,假如今天再来一遍,就是第六次了。唐僧师徒九九八十一难也到西天了,我觉得我再这么下去,九九八十一改之后,也可以跟他们一起去西天。
我转身就给老框打了个国际长途。
我问老框我大约何时才能回归故里,说个时间,好让我心里有个数。
老框在那头沉默了约摸一分钟,只对我说了一句话:“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然后他把电话挂了。
我对着眼前的教堂,暗自下决心,假如今天三文鱼再给我退计划书不把话说清楚,我就把唐字写上一百张白纸,明天一早贴满他的办公室。
我一边脑补着英雄主义动感画面,一边踏进了F。一进门就迎上了马克娘娘的兰花指。他姿态优雅地将他的食指从我的鼻尖抽去空中,画了个花型半圆,定格在挂钟上,“你,迟到了。”说完,脸上堆满微笑晃着脑袋就走开了。他今天头上喷了一吨的发胶,头顶上高高崛起的发髻活生生地把他一米七的身高拔到了一米八。
红发魔女今天一身从上暴露到下,闪闪发光的鳞片装,假如不是我一眼就看到了她正后方与锅融为一体的小胖子,我一定以为我走错了宴会大厅。她对着马克娘娘的高线发髻飞出了一个白眼,然后面带杀气地微笑着走到我面前,“听说你做了销售企划案?刚来就想抢功吗?”她捂着大红唇,意味讽刺地笑起来,“他们没有告诉你,现在这里的企划案一项都要团队合作吗?我们销售部的负责,每个人都要在上面签名,你以为你自己一个人可以顶所有人吗?”她哼了一声,踩着水晶跟扬长而去。
呵。甄嬛传应该再拍个意大利版本的,上个班一个个跟在后宫一样。
慢着!——哦!——!我恍然大悟,这就是为什么三文鱼一直把我的销售案退回来的原因!
红头发真可谓是一个质地优良的双面间谍。
只不过这个签名要拿到,也是一件很头痛的事情。
现在他们眼中的价值观并不体现在企业是否发展得好上面,他们眼里现在最重要的是怎么争取到自己想要的。职位争斗排第一,企业死活排最后。假如某人上位了,企业不行了,最快扔掉饭碗跳槽的一定也是他。
我就不明白,三文鱼到底看上了他们之中的哪一个,而非要和我的姓氏做抗争。
正经脸秘书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办公室里。
大约半个小时之后,她走过来,对我说,“你的企划书我拿去交给费列罗了,他在隔壁。你找他拿吧。”她走的时候冲我点了一下头。那会儿我还不明白她的意思。
费列罗应该不常来店里。因为有他在的时候,办公室通常云雾缭绕,而里面却没有装去除烟雾的装置。
所以我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脑袋也总是吞陷于一片白茫之中。只有大背头在阳光里闪闪发亮。
他并不急着和我说话,而是神情忧郁地望着窗外那台正在抽粪的车,望了好些时候。
“空气不好。”他转身掐灭手里的烟,随口说到。
“坐。”他眯着眼,目光犀利地穿透厚重的变色镜片,直击在我身上。
我本想开口说下计划书的事情,结果他抢先岔开了话题。
“今年天不好啊,你看这二月,下了一个季度的雨。人都快发霉了。”他说着,拿起手机,点开了不知道什么趣味游戏开始玩起来。
我有点愣在当场了。我难道不是进来跟他讨论计划书的吗?但是他的手机游戏按键声不断传出,叫我说还是不说?
他头也不抬地说,“你说吧。”
这句话似乎是他的口头禅。
我说什么?叫我把三文鱼怎么退回我计划书因为我没有集齐可以召唤龙珠的签名的事情跟他阐述一遍?
他看我不做声,抬眼在镜片外瞟了我一眼。
“你那个计划书我看过了。”他依然在进行手机游戏,“销售计划书,你提到了开发非贵皮类商品的问题,这个越界了。”
“我知道,但是这也是我们现在必须面临的问题之一。假如不扩充市场面积占有量,光靠明星炒作和广告我们未必能在上半年的销售季度上拿下漂亮的成绩。”
“你写的计划书,必须要承担责任。”他放下手机。又点了一根烟。
我愣了一下。这话什么意思?我承担责任?要是开发渠道没做好,我这个责任何从担起?
“小姑娘,计划书就是这样的东西,一旦被认可被实施,那就是一本账目,不负责任的计划书,等于废纸。”他表情很轻松地笑起来。就像说了一句玩笑话。
我知道他并非在开玩笑。
但是这个名头分量很重。人都是一个毛病,由于不想冒风险,背责任,就习惯于把身上的责任一点点地卸掉,一点点地和那些非常紧要的问题撇清关系,慢慢累积到后来,你就会发现自己的分量不如以前重了。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甘冒风险也要夺得各个权利的原因。
于是我点点头。我说我愿意为我的计划书负上全部责任。
“我欣赏你。”他说,完了又继续开始手机游戏。
半天见我还在面前,挥挥手说,“别担心,剩余的我搞定。”
这是我第一次和费列罗单独说话。
你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在听又像不在听,他在思考又像不在思考。他身上弥漫着一股穿越频道的气场。
我从办公室出来就见到了一个新来的销售,穿着制服站在爆炸头边上,爆炸头好像在给她讲解店内分布。
我刚想进办公室,突然有种极度不好的红光在我脑中闪回了一下。于是我退到刚刚站的位置,越过毛先生厨具和那些鳄鱼皮,仔细看了一眼那个新来的。
迪奥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