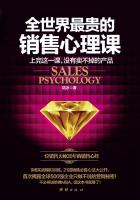黄昏午后。晴了一昼的天说变就变。申时才过,天马上就黑沉沉的,不多时便下起了雪。
清瘦俊秀的掌事感觉到寒意,随手拿起一边的披风搭肩上,然后继续捧着书研读。
客人来往,小二进出,原本寻常。
掌事突然皱起眉,合上书,起身看向门口。
坊里来了两位客人。
看站在门口扫着肩上落雪的侧影,都是较北方人要削瘦许多的人。
掌事沉吟了下,招呼了个小二哥来,吩咐了几句。
那小二哥和那两人擦肩经过时,露出了诧异的表情,忍不住回过头来看了看掌事,见掌事挥手催促自己快去办事,忙拔腿跑了起来。
两人整理过衣着后才敛袍进来。
为首的人不仅模样精致,举止有礼,气度坦然,而且那态度似乎一室的粗俗壮汉都没资格入他眼一般。
身后那耿直的护卫也不必提了,手里一柄长剑散发着骇人的气息。
两人一进来,坊里渐渐地就安静下来了。
掌事盯着他们入座,脑子里忽然念头一闪,下意识将视线转向已经在那里盯梢好几日的几人。
掌事眯起眼盯着他们的一张一合的双唇,大概能读出他们的话。
确实,就像他们说的,在北方哪里有这么矜贵的人。如果不是因为穿着布衣,几乎就可以肯定是京城来的贵族了。
明明约了李中禹,但是去欢喜楼之前却先来药茶坊。
掌事一直看着这两人入座,店里的小二哥上前打点,没说两句,小二哥忙跑到柜台前低声问:“掌事的,那俩小哥说要能治风寒的药茶。”
掌事瞥了那两人一眼,露出无奈的表情。
这哪是得了风寒的样子啊!
“行了,交给我,你忙去吧!”
萧掌事起身转进茶房,茶房里比预定的多了一壶热茶。
萧掌事不意外地拿着那壶茶便出去了,亲自走到那桌边,给两位客斟上。“请慢用。”
“看来他也过的不错。”阮靖唯只浅尝一口就知道是谁准备的茶,含笑抬头看了一眼。
萧掌事笑而不语,点了下头,然后转回柜台后。
被掌事遣出去的那小二哥从外面匆匆回来,手里提着颇大一个个食盒。年轻掌事朝那边气氛分外不同的那两人扬了扬下巴。小二哥马上奔到那两人身边,打开食盒,把里面的菜一个个地摆上。
“主子。”那护卫看向身旁那作男子打扮的人。
他没有接话,只是回头似笑非笑地向着掌事这边看了一眼。
少顷,在四周的人异样的眼光中,这两人用完了膳,结账离开。
掌事抬头看了一眼那两人离开的背影。
他们是来做什么的呢?
正是斜阳懒懒,归家好时。天色愈暗,街上的摊贩也陆陆续续开始收拾。
大概是天气骤变,药茶坊那看起来有些瘦弱的掌事也受不了了,谴了小二,早早关了坊门,匆匆归家去了。
这厢从正门进了那座稍显落魄的小院,少顷便一道人影经后门走出来,有些鬼祟地拐过几个弯,进了欢喜楼的小门。
“小哥可来了,清风坊主已到多时,要是小哥再不来,楼主该让人去请了!”守门的汉子笑道,一边领着人朝里面走。
萧夕抿着嘴笑了下,不提自己已经见过清风坊主的事。
屋里火炉正旺,灯火通明。
萧夕随那汉子走至门前。汉子止步,扣了下门,抬手作请。
萧夕颔首,低声道了句谢后推门入内。
“哈哈,看!刚说着人就到了!萧夕,你快过来见过阮坊主!”
萧夕拉下外衣,递予门边服侍的婢女。
“下午初到翰县时,觉着天寒,就随意找了家坊子吃茶。进去了,才发现就是楼主信上说的‘药茶坊’。”
年轻掌事转过屏风。热闹的屋里,数人围桌而坐,兴致盎然。
正座上的年轻女子笑着抿了口酒,漫不经心道:“大概真是下山太久了,竟连这点风雪也开始抵御不了了。”
掌事定住脚步,拱手作揖:“属下见过楼主。”
李中禹比了下身侧的位子,“过来吧,我给你引荐。这是北方‘五仙馆’之首的清风坊主,这生意经,你可得好好向她讨教讨教。”
萧夕撩袍坐下,随即又是拱手一拜。
“楼主过奖了,晚辈不过是会些雕虫小技而已。”阮靖唯淡淡说着,抬眉朝那年轻掌事看了一眼,“萧公子……呵,李楼主好眼光。萧公子看上去单薄,却能入李楼主慧眼,今日看来,萧公子果然有大能。”
李中禹回头看萧夕:“世上能被阮坊主称赞的人可不多,你小子可以嘚瑟了!”
萧夕再拜:“谢坊主赏识!”
年轻女子轻笑一声,没有说什么。
酒过三巡,楼里的管事陆续退席,回楼前工作。
厅里除了火炉旺着,气氛则逐渐冷却。
李中禹见阮靖唯停筷已久,时候也差不多了,就开口邀请:“阮坊主有没有兴趣到楼前听听我欢喜楼花魁弹曲子?皓月最近谱了新曲,我都还没听过呢!”
阮靖唯的视线若有若无地掠过楼主身旁的年轻掌事,浅笑道:“晚辈虽不是什么风雅之人,但也听闻皓月姑娘的名声许久了。”
李中禹当即起身,抬手:“阮坊主,请。”
一行人走至楼前。
阮靖唯今日作男子打扮,在欢喜楼这样的花楼倒没惹起什么麻烦。只是连李楼主都为这俊俏的南方公子开路,不免引人猜测身份。
欢喜楼里装潢豪华俗艳,莺声燕语不绝于耳。客人高谈阔论,甚至偶尔会出现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
楼里的姑娘都已经司空见惯,见状即使劝解,也是敷衍的成分更多。
阮靖唯在二楼的厢间冷眼看了好一会。
李中禹看她神色像阴像晴,一时捉摸不透,心里嫌弃又烦躁,却只能陪笑说:“阮坊主再稍作等候,皓月很快就出来了。”
“李楼主。”阮靖唯回过头,似笑非笑地看着李中禹,“贵楼昌盛,楼里的姑娘们也都训练有素。晚辈想请教前辈,虏获那么多女子从妓的方法是什么?”
这语气不重不轻的一句话,如警铃般在李中禹脑中响起。
尽管保持着脸色如常,但其实李中禹已经能感觉到自己后背一凉,开始渗出汗来。
李中禹微变,牵强地扯着嘴角:“阮坊主,这话是什么意思?”
“其实也没什么意思。”阮靖唯神色平静,似乎真的只是随口问问一般,“良家妇女多矜持守道,别说从妓,一般女子光是踏进过花楼一步的都会遭人唾弃。晚辈自然知道这样的声色游戏更招生意,可始终想不明白个中源头,也就无从做起。”
李中禹皮笑肉不笑地“呵呵”笑着,没有接话。
身后侍立一侧的年轻掌事垂睑轻轻别过头。
这时楼下传来热烈的欢呼。
厢间中众人纷纷低头望去,果然是皓月登台了。
阮靖唯点点头:“果然是花容月貌。”
李中禹刚想开口,想起方才那问话,有讷讷地合上了嘴,老实坐着。
少顷,楼下的女子开始奏琴。
虽然皓月在北方名声颇响,但就琴技而言,和江南琴娘相比还是差了一截,更不要说和名满京城的卓幺娘相比了。
李中禹听的乐在其中,阮靖唯则兴味索然。
目光一转,和站在后方阴影处的人对上了视线,又意味深长地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