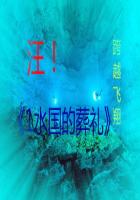姬凌薇在众人的劝说下,自己又着实思量了好久,也许正如他们所言,这毕竟是家,是根,是牵挂,虽然没有了亲人,但到底还有很多可以眷念的东西,比如说:友爱,互助,温情,这些都是她以前在匪窝里不曾遇到的啊,也是她日夜渴求的啊,现在好不容有了一点开始,自己怎么又因为不习惯而放弃呢。遂也把那卖方置业的念头抛弃了。
而现如今说到来生泪和诸葛天了,来生泪那天是的确给太微给训了的,她又答应了太微,自己已经失信一回了,是万不可再食言的。而况她也隐隐地发觉自己是有与凡人不太一样的地方,也对自己的身世十分好奇。太微那天和她说的又十分郑重其事,按照太微所说的她所剩时间不多了,她也开始有些捉急了。
这日清晨,来生泪拉了诸葛天到得房屋避静一角,说道:“小天哥哥,你还记得我们要一起去喜马拉雅的事吗?“诸葛天听罢,不觉挠了挠头,想着自己之前是因为伤心难过,又找不到事儿做,有来生泪相伴,才不得已答应的,现今有了亲人,有了家,哪里还想去讨那没趣的,遂说道:“去喜马拉雅?”样子仿佛没有听过来生泪说过一般,诸葛天继续说道:“小泪,你去那里干嘛?”来生泪见他这番,自己心里早就有气了,忙不高兴地道:“去那,反正就是去那呀。”诸葛天听见来生泪这番说,也不知道她什么意思。而况他根本就不知道喜马拉雅在哪里,也只当来生泪要去玩罢,所以竟是多不放在心上的。
诸葛天见来生泪这说法也是敷衍,尴尬地说道:“可是我们都不知道去那里干嘛,也都不知道喜马拉雅在哪里,我们……我们怎么去呢?”来生泪道:“我们可以问路的,你之前不过答应过我么,要和我一起去的,怎么现在想反悔了?”诸葛天听罢,为难地道:“可是,我才刚找到我表姐,她现在才好一些,我又是她唯一的亲人,我……”来生泪见他这番说,自己却是不依,急切切地说道:“这么说你是不去了!”
诸葛天无法而且无奈顿了顿,起初他是因为没有家人,梨香书院没了,没有寄托才想着和来生泪一起去的,也是带着见世面、玩耍的心态去。现在他有了亲人,而且姬凌薇刚刚重掌家事,正是否极泰来之际,来生泪又不说明缘由,诸葛天哪里放得开的和来生泪去。诸葛天道:“也不是,小泪……”他刚刚一转过来,来生泪却急急地“啪”的一巴掌打了过来,诸葛天很是吃了一惊;他捂着脸看着来生泪,只见她满眼泪水,他万料不到来生泪会这样,也从来没有见到她这样痛苦难过过。
来生泪也不知为何自己竟打下去了,也许她觉得诸葛天在推脱,也许是她觉得自己为了诸葛天折腾这么久,拖延这么久,诸葛天却不肯陪她一道,也许她是觉得在诸葛天心里她没有诸葛天的表姐或者是这个新开始的家重要,也许她是害怕,至于害怕什么,她不知道,只是今天自己却会无端控制不住,非得要诸葛天给个明确回答不可!
来生泪打完了诸葛天,自己却痛哭着跑出去了,诸葛天还未反应过来,他只是觉得今天的来生泪好生奇怪。待他顿醒过来,自己忙跑了出去找来生泪,哪里还有她的踪迹。诸葛天想她定是乘风而去的,要不怎么一点影儿也没有。他也不再去追了,因为他觉得来生泪现在正气头上,去追了也白搭,而且现在他也有很多事要做了,他呆头晃脑地进来,只觉脸火辣辣的有些疼。
姬凌薇是很早就起床晨练了,这会子刚刚去那边井里打水过来。她看样子精神不错,姬凌薇见诸葛天捂着脸过来,他似乎不快,忙问:“小天,你怎么了,怎么这么早?”诸葛天道:“表姐,你也很早啊,你平时都这么早起的么?”姬凌薇道:“对啊,哦,小泪呢?她还没起么?”诸葛天听了,尴尬地挠挠头,说道:“她,她走了。”姬凌薇听了,忙说道:“走了?!怎么会,昨晚子还好好的,怎么这一大早的就这样子走了?”诸葛天听罢不语,姬凌薇见着,又见诸葛天脸上几道青红的伤痕,忙问:“小天,你的脸怎么了?”诸葛天听罢,忙摇摇头说道:“没什么,没什么的……”姬凌薇忙伸手过去,一手掌在诸葛天的肩,一手不扶住他的脸,只见那粉白的脸上无端多出几道隐隐的疤痕,自然也猜着了三分,忙说道:“哦,是你们又闹气了?”诸葛天摇摇头,说道:“不是的。”姬凌薇道:“那她怎么走,你怎么没留住她?”
诸葛天道:“我……她,她是要去什么喜马拉雅的,我又去不得。”姬凌薇听了,也着实吃了一惊,喜马拉雅,自己都从未曾听说过,怎么来生泪要去那个地方。忙问:“她去喜马拉雅,去那里做什么?”诸葛天听了摇摇头,尴尬地说道:“我也不知道,她说是去给别人送东西的。”姬凌薇听罢,她也知来生泪并非常人,诸葛天也许不合适她,便也不再追问和深究。
这时曹太夫和曹麟儿走将进来,提了一大袋柿子,曹太夫道:“凌薇,小天,看——这是我和熙然昨天上山采药摘来的野柿子,你们试试看。”说完扫了一眼,并不见来生泪,曹太夫道:“咦,小泪呢?”曹麟儿道:“对啊,小泪姐姐呢?”诸葛天听了,尴尬地道:“她走了。”曹太夫道:“走了,怎么就走了呢?”诸葛天不觉摇摇头,说道:“我也不知,说是要到那西方的喜马拉雅山去。”
曹太夫是见识广博之人,又是有些道行,起初他看见来生泪时便觉她并非凡体,这次听诸葛天一说,更加确定不已,只是他也不知道来生泪的来历和去那喜马拉雅做什么,他也不再追问,毕竟很多规则不是那么易容就变的,诸葛天和来生泪也一样。有些事不说还好,说了只怕于谁都不利。
他们叙过一会儿话,曹麟儿在姬家帮忙理茶叶,曹太夫是又出去了的,姬凌薇见曹麟儿面目娇滴可爱,和诸葛天也是同龄相若,看起来也是十分的般配的,虽然来生泪强过她,到底人还是要务实的,这些她懂。姬凌薇道:“麟儿你多大了?”曹麟儿听罢,骄里娇气说道:“我今年十一了。”姬凌薇道:“你平时在家都干什么?”曹麟儿道:“帮我爹爹熬药,帮我娘做饭。”姬凌薇听罢,见她仍旧一脸天真的理着那些茶叶,心下越发喜欢。
而说来生泪呢,一气之下竟然乘风一跃数十里之外了,跑到一棵千年银杏古树下停住了。抱住那树默默落泪,自己也不知道今天抽的什么疯,竟稀里糊涂地把诸葛天给打了,还稀里糊涂的哭了。待她哭过静心之后,深吸几口气,眺望远方,见的湛蓝晴天,虽然衰草枯荣,远远地望去却也是一片广阔无垠的远景。
她遂在那棵树枝四散而开、形如锥形伞状的古银杏树下坐着,树下羽落的全部是晶莹剔透得发亮的金黄色的银杏树叶,映着日光灿灿然。那美得璀璨美得纯粹的金黄着实令人舒然,聆听银杏叶随风飞舞的声音,却感受的是那华华丽丽的生命和落叶时的淡淡忧伤。秋——一个如此特别的季节,一个离别的季节,一个令人满腹愁肠的季节。来生泪是孑然一身静坐铺满银杏叶的树下,还一动不动的抹泪。
他是身袭一缕浅粉红参白的衣裳,映着这金光浮色,纯若仙女了。一阵风吹过,银杏树叶随着飘落,如雨,如花,如絮,却十分的与众不同,来生泪还未见过这么美的落叶,以前所见落花,繁华而缤纷,以前所见细雨,绵绵如愁丝,却没有一样比得上这眼前的美景。只见那金黄得透亮的银杏树叶飘落下来,如一只只蝴蝶洒满了一地,虽若秋愁,却恬静而淡然,令人有种说不出的忘忧,忘我,忘掉一切。
“恍若前尘如初见,金秋风露欲缠绵;青枫道上路遥远,几经波折人缘边;孤许独去应自怜,轻烟老树谁人眷;闲云白霜日不悠,物换星移一度秋。碧海云天,杏花满地,北雁南归,霜林染醉,离人落泪!今夜月明明几许,秋后又宿谁人家,一往情深从来是,深山夕照梦不归,一往情深从来是,深山夕照梦不归……”
是一位老妪的声音,这声音十分沙哑,却浑厚无比,入耳争鸣。来生泪正呐喊这荒山野岭的,哪里来的人声,而况是一位老人的声音。她又抹了抹眼泪,用衣袖擦了擦脸上的汗丝,忙忙地站起身,那银杏树叶从她的肩膀上衣褶里滑落。来生泪踮了踮脚,张目四下望去,却不见一个人影。
“姑娘。”那个嘶哑的声音又响起来了,来生泪吃了一惊,那声音仿佛是四面朝来的,怎么没有一个方向的辨别呢?她正惊诧,“姑娘……”来生泪听罢,回头一看,唬了一跳,退了几步之地。声音是从那银杏树里传来的,不多时,那银杏树的树干便隐隐地显出一张人面来,闪闪地发着金光,虽然满面皱纹,目光却还是明亮矍铄的。
来生泪怔怔地道:“你……你是谁?是鬼是妖?”那银杏人面听罢,不免淡淡地微笑道:“呵呵,姑娘妳不要害怕,我既不是鬼,也不是妖,我是棵树,只是我已经有上千年岁月,多吸了些世间灵气精华,遂通了灵性,会成人型,会言人语罢了,姑娘莫要吃惊。”来生泪见她仍旧面目和蔼慈祥,说话语重心长,而况自己本就有法力,是降妖除魔的,怎么会怕?
来生泪道:“哦。”那银杏老妪道:“姑娘刚刚在这里哭什么,怎么那么伤心?”来生泪听了,不免又想起今天的事儿来,自己又懊悔又迷惘。那银杏老妪又道:“呵呵,看来是情缘难却啊。”来生泪听罢,忙说:“你怎知道?”那银杏老妪道:“我怎会不知,我在这一千多年了,所见之人间因缘孽缘不计其数,哪就不知呢?只是不知姑娘这般小小年纪,竟有这样的心思呢?”
来生泪听了,自己却不解,说道:“什么心思?”那银杏老妪道:“人生于天地间,时间短暂,总有许多事务要去处理,许多心愿去达成,许多情缘去完结,怎么囿于所有情缘中最粗拙的爱情,而深陷进去呢?”来生泪听了,却是不承认的,忙忙地说:“谁……谁说的,我是为那事呢?我只不过……只不过一时没缓过来而已。”
银杏老妪听罢,淡然微笑道:“我看姑娘非凡脱俗,定非一般人家,只不知如何会到这里来?”来生泪道:“我……我,是有一位老爷爷给我一样东西,让我带了那东西和另外一样东西到那西方的什么喜马拉雅去的。”银杏老妪听了,想她在人间呆了千年,自然人间万物皆知一二,也万料不到面前这不过十二三岁的女娃竟然和喜马拉雅珠峰之巅有情缘,料必定是轮回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