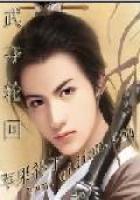说话之间,宫车停驾。刘彻抬手掀起帷幕,侍臣撑着华盖候在车前。刘彻下了宫车,与陈阿娇一同拾阶而上,进入长信宫。
“皇上、皇后驾到。”伴着侍臣一声长叫,刘彻携着陈阿娇走入正堂。刘嫖起身下座,一齐拜道:“恭迎圣上。”刘彻摆了摆手,与陈阿娇上前拜道:“孙儿叩见皇祖母。”太皇太后摆手道:“免了,免了。彻儿,你们坐,都坐罢。”
刘彻应了一声,与陈阿娇坐到一旁,将长形漆盒放置桌上。太皇太后环视众人,道:“该来的人都来了。”刘嫖陪笑道:“什么该不该来的?母后说话,越发玄妙了。”太皇太后转向刘彻道:“彻儿,你知道我叫你来,所为何事?”刘彻明知故问道:“孙儿不知。”
太皇太后道:“你可知道赵绾、王臧在狱中畏罪自尽之事?”刘彻佯作惊状,诧道:“什么?两位老师死了?”太皇太后哼了一声,道:“此等贪赃枉法之徒,何德何能做天子之师!”刘彻拱手道:“孙儿实在不知。”
太皇太后起身道:“皇上以为,他们可是罪有应得?”刘彻心中有气,亦起身应道:“证据确凿,即是罪有应得。”太皇太后道:“皇上觉得他们犯了何罪?”刘彻愣了一下,道:“难道不是贪赃枉法麼?”太皇太后摇头道:“不止如此。”她从侍臣的手中接过一个书简,举在身前,道:“这是几位王爷、侯爷联名上的奏章,皇上可要看看?”
刘彻心头一沉:“终于来了。”他在刹那之间,便即宁定,应道:“皇祖母有命,孙儿何敢不从。”太皇太后交给侍臣,递到刘彻身前。刘彻伸出双手接过书简,展开阅览。刘嫖坐立不安,伸长脖子,好似要去看个只言片语。刘彻忽然卷起书简,握在手里,咬牙切齿地道:“这帮王公大臣既有主意,为何不早些劝阻朕!”说着便将书简扔到阶下。
侍臣连忙拾起书简,呈到太皇太后面前。太皇太后微微一笑,道:“你念出来。”侍臣应道:“诺。”展开书简,念道:“伏惟太皇太后圣听:今天下息宁,臣等奉道而行,颇得章法。奈何赵绾、王臧独掌大权,恣意妄为,搅乱法度,天人共愤!兴明堂,虚耗府库,其罪一也;迫列侯就国,伤君臣之义,其罪二也;奏请毋事东宫,坏孝道礼法,其罪三也!数列其罪,纵三千奏牍难尽。臣等惶恐,恳请太皇太后斩此逆贼,以正视听。”一言念毕,满殿无声。忽闻惊雷顿响,刘嫖登时吓了一跳。
太皇太后笑道:“嫖儿,你怕什么?”刘嫖手贴胸口,道:“雷声好大。”太皇太后冷笑一声,道:“皇上,你觉得如何?”刘彻诧道:“人已自尽,还当如何?”太皇太后坐回正位,道:“罪魁尚未伏法。”刘彻一时猜不透她的想法,皱眉道:“皇祖母所指何人?”
太皇太后抬手指着董仲舒,道:“你可知道他是谁?”刘彻顺着看去,端详了一会儿,叫道:“董仲舒!他怎么在这?”原来当初刘彻下诏举士,董仲舒亦曾上书,刘彻召见了他,是以识得。
太皇太后听了这话,不禁微微蹙眉,向玄冲道人投去询问的目光。玄冲道人苦于无暇解释,这时只得勉力答道:“此人确实是董仲舒。但请太皇太后,听微臣一言。自圣上举贤问策以来,董仲舒就逗留长安,寄居于申培府上,与赵绾、王臧日夜同谋,对二贼所为逆行多有参与。凡此种种,臣皆有实证。”
董仲舒笑道:“不错。这些事情,小民不敢否认。”太皇太后怒道:“好呀,你倒是直爽!皇上,依你之见,该当如何?”
刘彻面露难色,犹豫未决。话至此般境地,他也明白太皇太后的意思。一则,要他承认此前所为皆是错举;二则,逼他斩杀一个儒家大师,与儒家彻底断绝关系。刘彻早料及前者,后者却大大出乎意料!刘彻心道:“董仲舒这是要置朕于何地!”他偷瞧馆陶公主,刘嫖抿嘴不语;回看陈阿娇,阿娇向他连打眼色。
霎时又是一记惊雷!太皇太后逼问道:“皇上,你意当如何?”刘彻尚未应答,董仲舒突然开口道:“小民不敢否认所作所为,可也不敢承认此为逆行。”太皇太后冷笑道:“你还有什么说辞?”
董仲舒道:“其一,兴设明堂,尊圣王之教,序上下尊卑,功在当代,利于千秋,岂可言罪;其二,列侯就国,各享其地,使物尽其用,人尽其责,岂可言罪;其三,子爱利亲谓之孝,太皇太后罹患眼疾,而夙夜忧心国事,无利于养生之道,小民深以为忧,妄自揣摩圣意,故兴此议,或可言罪。至于其它,小民一无所认!”言辞慷慨,满殿皆惊。
东方朔不禁暗赞一声:“此人的胆识见地远出申培公多矣!”东方朔本还略带担忧,这时全把心收回肚中。他斜看玄冲道人,此际面色十分难堪。再看馆陶公主,眼神飘忽,似在观摩太皇太后的心思。阶下刘彻喜形于色,身材挺直,胆气倍增。陈阿娇还坐在他右下首位,已是面带倦意,心有旁骛。
堂上太皇太后先是起身踱步,又背过身去,忽然拍掌连声道:“好,好!”回身道:“如此说来,还是本宫错怪你了!”
董仲舒知这太皇太后亦非等闲之辈,心里也略为迟疑。站在末位的东方朔突然高声叫道:“既是一场误会,何不放人?”太皇太后登时怒道:“你又是何人?”
刘彻循声看去,又是一惊:“东方朔!”他********应付太皇太后,不曾注意旁人,陡然见到奇乎怪哉的东方朔,哪知是敌是友,自是一惊。
太皇太后看看刘彻,又看看东方朔,见他身穿道家青袍,愈觉不可思议,心道:“穿此袍服,当是道家名士,怎么排在末位?”眼瞧玄冲道人面色铁青,心里愈加狐疑,道:“你叫东方朔?”东方朔不喜不忧,拱手道:“正是草民。”太皇太后道:“你是道家人?”东方朔应道:“非也。此袍服是青冥大师送予草民御寒。”
太皇太后含威斥道:“你方才在哀家面前大呼小叫,难道不怕死吗?”
东方朔迎目相对,迥然不惧,答道:“心中有感,忘乎所止。”太皇太后冷笑一声,道:“直性子的人可不长寿。”东方朔叹道:“草民也说不上是直性子,其实就是贱嘴一张,怕是幼时老母鸡吃得多了,染上这病。”
陈阿娇听他插科打诨,禁不住“扑哧”一笑。东方朔续道:“草民早年也曾见过一名神医,他告诉草民,若要医这病,需得做到三样事情。”
陈阿娇浑然忘却身处何地,奇道:“什么事?”东方朔瞟了一眼太皇太后,见她面色越发和悦,心知得计,伸指道:“第一,只笑不哭。”陈阿娇不解道:“这种事情如何能做到?难道你跌了、撞了,也不哭麼?”
东方朔道:“皇后娘娘所言极是。可这还不算,后面还有更奇的。”又抬起一指,道:“第二,能睡不吃。”陈阿娇纳闷道:“这件事情有什么难的?”东方朔叹道:“娘娘有所不知,草民嗜睡如命,每得空闲,便犯困意。几年下来,瘦成如今这副模样。”陈阿娇笑道:“再过几年工夫,你不得瘦成竹竿儿了。”东方朔拜道:“娘娘所言极是。”
陈阿娇走到近前,道:“那第三件事情呢?”东方朔伸出三指,道:“第三,光说不做。”陈阿娇只觉他有些呆,笑道:“你不会真听他的话罢?”东方朔又是一叹,道:“所以草民至今还是一无所成。”陈阿娇拍掌道:“你这个病是医不好啦。”
东方朔道:“是啊,所以草民斗胆,请太皇太后恕罪。”说完伏身一拜。太皇太后默然许久,经东方朔这么胡闹,情势全消,只得摆手道:“罢了罢了,且将董仲舒押入牢房。容哀家再思量思量。”
玄冲道人面如死灰,语塞无言。侍臣高声道:“太皇太后懿旨,将董仲舒收监。”两个甲士闻声进殿,带走董仲舒。
太皇太后回坐堂上,久不言语,众人皆不敢说话,殿内寂然无声。刘彻心道:“这个脸是非得丢尽不可了。”他知时机难得,也顾不得多人在场,上前拜道:“皇祖母,孙儿有件东西献给皇祖母。”太皇太后讶道:“彻儿还有此等心思。也好,取出来与哀家看看。”
刘彻行至桌前,双手捧起桌上的长盒,举在头上,道:“皇祖母。”太皇太后示意侍臣去接,递到跟前来。她起身道:“皇上送的东西,哀家当亲自打开才是。”
众人引颈而望,只见太皇太后缓缓伸手放到长盒上,抚弄一阵,不少人看得汗流浃背。太皇太后把双手按在盒沿,轻轻往上掀开。刘嫖起身探看,忽地惊叫一声,跌坐在地。
太皇太后怫然不悦道:“嫖儿,你怎么老是大惊小怪!”刘嫖面流冷汗,道:“儿臣,儿臣最怕这些玩意了。”太皇太后伸手取出一把三尺长剑,用力拔出剑身,只见上面秀有花纹,饰佩七彩珠、九华玉,寒光凛凛,刃如霜雪,正中间镌刻两个大大的篆字:赤霄。众人看得嗔目结舌,皆不明其中深意。
太皇太后收起宝剑,道:“这是何意?”刘彻拱手道:“此剑名曰赤霄,是高祖配带之剑。高祖凭借此剑,斩白蛇,灭暴秦,破项羽,立不世之功,兴帝王之道。父皇晏驾之日,将此剑交于孙儿,嘱咐孙儿定要做个好皇帝。可孙儿登基未久,就错用贪赃枉法之徒,险些坏了祖宗基业,有负父皇所托。”言语哽咽,举袖拭泪:“孙儿心里有愧!近些日子,孙儿思前想后,自思还不是一个好皇帝,不足以承继赤霄宝剑。”言辞情深意切,令人动容。
东方朔听得这话,暗思:“经此一事,陛下当收心不少。”心里暗自宽慰少许。
太皇太后微微蹙眉,若有所思,道:“你是要哀家保管此剑?”刘彻拜道:“还望皇祖母督促孙儿。”
陈阿娇插嘴道:“是啊,皇祖母,彻儿他知道错了。”太皇太后斥道:“说话没有半点分寸,他可是皇帝。”话虽严厉,面色愈见平和。刘嫖这才将心放进肚子里,笑道:“这丫头被我宠惯了。”陈阿娇撒娇道:“皇祖母,孙儿不依。孙儿是皇后,难道还得‘皇上’长、‘皇上’短地叫他麼?”
太皇太后坐了回去,摆手道:“带回去好生管教管教,一点皇后的样子也没有。”刘嫖道:“是,是。那母后的意思是……?”太皇太后道:“都回去吧,本宫也乏了。”刘嫖如蒙大赦,道:“是,是。”走下木阶,与刘彻、陈阿娇一齐拜道:“母后(皇祖母)好生休息,儿臣(孙儿)告退。”
待皇帝、皇后、馆陶公主退下后,太皇太后将赤霄剑放在案上,喃喃道:“总算长进了些。”抬头向玄冲道人道:“大师也请先回,代本宫问候齐元君。”玄冲道人茫然应“是”,领道家众人离去,东方朔毫不见外,紧随在其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