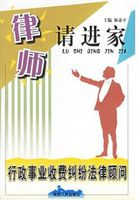宁远和滕与岳恰好在正七点钟同时抵达CornerClub,谁也没早一分钟,谁也没晚一分钟。似乎谁都不肯为对方浪费一分钟用来等待,也不愿让对方多等自己哪怕一分钟来让情感的天平上缺斤少两。
无独有偶,两个人都是单刀赴会,不携一枪一戟,不带一兵一卒。
势均力敌,公平较量。
这本来就是仅隶属于他们两个人,而别人的炮火抵达不了的战场。
六年不曾谋面的两个人没有拥抱、没有寒暄,因为他们根本不是朋友。
会所走廊上的油画同样也吸引了宁远的目光,宁远想,那天宁彩是否也在这条走廊上经过,经过的时候是否也曾像他现在这样驻足。
“宁少也喜欢欣赏油画?”滕与岳的声音从宁远的身侧传来。
“谈不上喜欢不喜欢,时间久了,总会潜移默化的受到一些影响。”宁远声音淡然。他看着这些画,全部是超现实主义绘画,总是有让人意想不到的比喻和想象。和彩彩朝夕相处六年,彩彩的每一幅画他都认认真真的看过,每一个细节都不放过。很长时间,彩彩都不说话,她的画成了她和这个世界的交流方式。他只得从每幅画里获得信息,揣测他的彩彩,是否快乐。
“是很久了,一晃,都六年了。”滕与岳也看着面前的画,“宁远,这六年,你是在以什么身份同她朝夕相处呢?兄妹?还是爱人?”
是啊,是以什么身份同她相处呢。宁远转身,面向滕与岳,直视着他,目光坚定如炬,“滕少,你原本就这么八卦吗?喜欢探听别人的私事。我们是兄妹也好,爱人也好,似乎都不管滕少什么事吧。滕少不是恨她入骨,她死了你才开心吗?难道时间真能让一个人对另一个的恨慢慢的熬成爱意?”
“我说过,她是褚言溪。”滕与岳反驳着,却明显的底气不足。
“褚言溪?哈哈.”宁远笑,“滕少,是你装傻还是我健忘啊,褚言溪早就死了。活着的是褚言汀,你最讨厌的褚言汀。她也曾想变成褚言溪,可是你,滕与岳,还是要把她往死路上逼。”
只要闭上眼睛,宁远就能看到褚言汀躺在血泊里的样子,没有一点的生命迹象,那个时候,他想杀了滕与岳。
该怎么回忆这段往事,太过悲情,太过鲜血淋漓。
时光退回到七年前。
退回到褚言汀割腕自杀的那个晚上。
那时,医生说,我们已经尽力了。
那时,虚弱的宁远在褚言汀的chuang前说了好多好多的话,却还是没有把床榻上的人儿叫醒。
万念俱灰的他那么低声下气的去求滕与岳。
原来,不论多么骄傲的人儿,都有一些东西,比尊严更重要。
他跪在了滕与岳的跟前。
褚言汀啊褚言汀,倘若你知道,那个叫宁远的男人,那个手里沾着血即使对待有血缘关系的亲人都能恨绝的男人,却为了你,放下所有的自尊和骄傲,跪在另一个男人的面前,能不能毫不犹豫的去爱他呢。
他跪在了滕与岳的眼前,虔诚的像是在跪拜一尊弥勒佛,眼睛里却已经空空无物。
因为抽了太多的血,本就消瘦单薄的他脆弱苍白的像一个纸片人,好似风一吹,就会飘走。
他跪在滕与岳的眼前,张口吐出的字节里全是祈求,他说,滕与岳,求你去告诉她,你收回你的话。收回你曾说过的你永远不会爱上她的那些话。对你来说,你只是表达了你的立场。可是对她而言,却像诅咒一般烙印在她生命线上。你可以不爱她,但请不要连她心里的期盼都剥夺了..
滕与岳终于心软。
他走进病房。
褚言汀的呼吸已经细若游丝,她安安静静的躺在那里,哪里还有平常的跋扈嚣张。
靠在病床前,他的声音很轻,褚言汀,我收回我曾经说过的话。如果因为我而导致你最后的消亡,那我的身上就永远烙上了一条人命。所以,醒来吧..
如果再给滕与岳一次机会,他还会不会去说那样的话?
生命总是充满了无限奇迹。
命运选择了谁又选择了牺牲谁,不到最后,谁又知道呢。
褚言汀醒了过来。
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滕与岳。
他说我收回曾经说过的话。
他说的这句话,就像一只手,揭开了隔开黑暗与光明的封印。那一瞬间,一道光射进了她被黑暗裹挟着的微弱生命中。
她听到了,什么东西发芽的声音。
是什么东西在复苏。
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滕与岳那张帅气的让人窒息的脸。
褚言汀想,上帝是有多优待这个人啊,所以才会那么精雕细琢成这样。
虚弱的像蜉蝣一般的褚言汀用全身的力气去绽开一个最灿烂的笑靥,尽管这样的笑容与她而言,那样陌生。
滕与岳望着那样苍白却纯然绽放出的笑容,她的眼睛里,迸发着的是照进黑暗里的第一道光。
滕与岳不自觉的勾起淡淡的微笑。
褚言汀以为自己看错了,第一次,这是第一次,他对她笑。
“你醒了就好,我去叫宁远进来。”滕与岳朝门口走去。
“等等”褚言汀叫住了滕与岳,“刚刚我听到.你说.收回那句话,是我听错了吗?”
滕与岳没有回头所以看不到他的表情,“是,你听错了。”
“我明白了,滕与岳,对不起。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恩,那样最好。”他回头,“褚言汀,假如真要选一个然后放弃一个,我会毫不犹豫的选择褚言溪,因为我爱她。但是,请不要再做出自杀这样的事。命运选择谁就交给命运决定,我想言溪也不想要你施舍来的活着的机会。”
言汀怔住,她点头,动作很轻很轻,我知道了,不会了。
滕与岳转身出门。
她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一片凄凉。
原来,那些光,只是海市蜃楼呢。
醒过来,还是那么冷。
原来,连自愿放弃生命都是错了呢。
是不是一定要按照命运安排的死亡方式才可以终结呢。
她那么坏,命运一定不会客气吧。
会死的很难看吗?
会死的很疼吗?
她那么坏,会下地狱的吧。
她是魔鬼,人人喊打的魔鬼,定是要下地狱的吧。
不知道十八层会不会够,有没有人收留。
******
褚言汀在医院里住了三天。这三天,除了宁远,没人来看她。
宁远不分昼夜、衣不解带的守着她,寸步不离,他害怕,才一个转身,她就会不在了。
“阿远,你脸色为什么也这么苍白?”
她终于发现了,三天了,她一直望着门口,他知道,她在等那些人的出现。
那些人,有她的家人,有她喜欢的人。
言汀,如果有一天,我突然不见了,你会不会像现在这样等我呢?
宁远心里一阵苦涩,却没有回答她。
三天了,从她醒来,宁远没有同她说一句话。
他也不知道自己这是怎么了。似乎在生气,是在和谁置气呢?又是置什么气?
“阿远,你是在生我的气吗?”褚言汀问。
宁远正在一勺一勺往碗里盛鸡汤的手顿住,这是第一次她用小心翼翼的语气同他说话。那声音里,包含着太多的患得患失。是害怕连陪伴了她那么多年的他也不再离她了吗?
“阿远,你是在气我没有跟你走是不是?”褚言汀试探着。
宁远端起鸡汤,拿着汤匙,坐在床沿上。
“张嘴”他命令着,却无视她的问题。他继续对她置之不理。
褚言汀听话的张开嘴巴,宁远把鸡汤送进她嘴里。这三天,宁远每天都亲自为她煮各种补血的汤,她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不再是那么渗人的苍白。
鸡汤自她的嘴角溢出,滋润的她双唇油光水滑。从桌上拿出纸巾为她擦拭,眼神粗暴蛮横,动作却特别温柔。
“阿远,我错了,你不要不理我。”褚言汀扯了扯他的衣角,眼睛里再也没有那样尖锐的防备。即使褚言汀活了过来,依然是一只扒光了刺的刺猬,不再盛气凌人,不再不可一世,不再骄横跋扈。可是,那些东西,都是她的铠甲啊,没有了铠甲,她只能把她最柔软的心亮出来,任何人,只要一个不友善的目光,就能把她扎的鲜血淋漓。
“阿远,跟我说说话吧,从我醒来,你没有骂我,却也不理我。你这样,让我害怕。”褚言汀轻轻的乞求着,嘴里堆着微笑,笑的很尴尬很丑。
宁远看着她极力讨好的样子,再也忍不住,放在手里的碗,一把把她搂在怀里。如果可以,就把她镶嵌进他的骨血里吧。这样,便共生共死,再也不用承受失去她的痛。
“褚言汀,我该拿你怎么办。”
褚言汀,我该拿你怎么办?
如果可以,我愿命运将那样的诅咒加诸在我身上,也再不能承受一次生离死别的痛,那种痛,我承受过一次,承受过两次,却再也不能承受第三次。
如果可以,我愿抽走你生命里的所有黑暗,不再不祥,不再承受鞭笞之苦,不再孤单,不再害怕。
如果可以,我愿给你爱情,我亲爱的宝贝,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你宠成世界最幸福的女孩,可是怎么办,我却给你起你想要的爱情。我终究不是你爱的那个人。怎么,都叫不醒你。
如果可以,我愿带你私奔。你不做褚家人,我不做宁家人。我们去一个有海有向日葵的地方,相伴终老。可是,这是我一厢情愿吗?
如果可以,我愿给你亲情,护你一生周全,免你一世颠肺流离。可是,我害怕自己一颗不甘寂寞的心无法站在亲人的立场上看着你和别人相爱相亲,永不相离。
如果可以..
如果可以,亲爱的,告诉我,我该怎么办,该拿你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