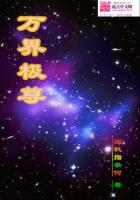萧梧前脚走,白榉带着人后脚至,两人也只堪堪来得及打了个照面,白榉看到萧梧怀里抱着个血糊的人,心中猜想便是夏一生,但看样子伤势沉重,要想救回来恐怕难上加难。
竟将我白楼的人伤到这般地步!白榉的眼神一厉,她虽然和夏一生算不上深交,但同处一处,低头不见抬头见也难免有了感情,夏一生为白楼尽心尽力,白榉便不能容人如此伤害于她,这便是底限。
“嗯?!”颜钧披了件斗篷从书房里出来,他看着外面林立的官兵仿佛对事一无所知,“怎么回事?我是朝廷命官,堂堂内阁阁老,谁这么大的胆子敢围我的府邸?”
“是我。”张怀辛自人后走了出来,火光映在他的脸上,他的面容便如刀凿斧削般的坚毅清冷,“我巡视东市的时候闻人来报,说是有一帮恶匪从阁老府中出来追杀张玉成大人,属下担心阁老已经出了意外,所以逮着匪人就立马赶过来了。”
“那你现在看到我没事还不快将人撤走,深更半夜如此扰民成何体统!”
颜钧将袖子一甩,张怀辛便抱拳赔礼,“惊扰阁老了,那这几个人我便带回去了。”
雷秦挣扎着想要说什么,他的手被反剪着,白榉点了他的哑穴,他“恩恩呀呀”了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上京里的水太深了,所以纵使各人心里都明白却还要装个糊涂,否则家不家国不国,外未争,内先倒。
“颜阁老,白榉是个江湖人,很不懂规矩,所以有句话要讲。”
天仙一个姑娘站在雪地里,她神色倨傲冷淡,带着轻蔑的笑意,婉转言道,“今夜的事不小,皇上也不傻,阁老可要多多保重啊。”
她说完,便头也不回的抽身而去,张怀辛于公门内,很多时候不便表态,可白榉不一样,天下之大无处不能安身,上京不容她,她还可以去苗疆蜀中,江南漠北,所以不该她畏惧颜钧反而颜钧该畏惧她。
风雪交加,萧梧将夏一生紧紧地抱着,砂砾血迹沾染在他身上,这该死的凛冽寒风正在夺走夏一生的体温,萧梧第一次察觉到自己竟这般无能。
“思奴!”
唐思奴刚刚将张玉成安顿下来,他身上的雪才化,荫的地上薄湿,正想泡杯茶去去寒气时便瞧见萧梧飞快的掠过眼前,扑面而来的血腥味让他心中一跳,唐思奴赶紧应声跟上。
萧梧怀中的人垂落着手,流动的血顺着指尖从门口滴到卧房,简直触目惊心。
白楼紧闭着门户,唐思奴替夏一生把脉下针,他的额上渐渐渗出了薄汗,经脉连着骨血,常人若是断最多也只断手脚,但夏一生全身经脉无一处完好,这份痛楚想想也叫人生不如死。
在唐思奴施针之时,夏一生曾经醒过一次,疼得龇牙咧嘴的无力呻吟,她嘀嘀咕咕的说了什么,旋即又晕过去了,亏的萧梧与唐思奴都靠的近耳力又好,才分得出她在喊人救命。
“疼死也要救我!不要放弃啊,萧老大!”
萧梧真想将这张嘴缝起来,旁人正经她说笑,旁人说笑她正经,都什么时候了,还叫人酝酿不出心疼来,萧梧叹了口气,他教夏一生倚在自己怀中,两双手紧握着,落一针,萧梧的手背就要被掐出点血来,时间一久,萧梧习惯了疼,便连手也忘了抽出来了。
“如何?”
唐思奴抹了一把汗,他的手刚搭到热乎乎的毛巾就被萧梧自然而然的接了过去,萧梧替夏一生擦了擦满脸的血迹,见她仍然气息微弱,不禁问道,“思奴,你的医术是不是退步了?”
得亏的唐思奴修养好才不至于给他脸色看,“经脉尽断,失血过多,如果不是她求生意志坚定现在就该过奈何桥了。”
唐思奴说着,认命般的将萧梧递过来的毛巾泡进热水里,“楼主,你也太强人所难了。”
“那……还有得救吗?”
萧梧摸了摸夏一生的脸颊,竟不觉得这人是伤重快要死了,这般流着哈喇子的酣睡模样纵使一个健康人也不常办到啊,萧梧思量着,下手一重,已经掐住了夏一生的腮帮子。
“她真气散尽之前还有余力点了自己几处大穴,死是死不了,但也只保住了几根手指,其他地方怕是一生都不能动了。”
“那你说这人怎么还能这么安心?”萧梧恨铁不成钢的又掐了掐那软和和的腮帮子,“武功尽失形同废人却还想活下去,倘若我不是先给她把了脉,还真当她能再支撑下去呢。”
“她这样的人天生傲骨,不得人疼。”
唐思奴也只得一边擦手一边叹气,他又道,“从楼主回来开始,郁南风就在门外等着了,我看他似乎还是放不下那东瀛双刀的事。”
“我身上有刀痕,待会儿让他看看,如果与唐詹身上的伤口一致,那基本就和鬼门脱不了关系了。”萧梧将夏一生缓缓放平,顺手替她掩好了被子,“找个贴心的丫鬟看着她,让王孙负责她的安全。”
“知道了,我会安排下去的。”
萧梧又回头看了躺在床上的人一眼,他苦笑着摇了摇头,对随后跟过来的唐思奴道:“思奴啊,我觉得我的心瞎了。”
“楼主知道就好。”
“哈,哈哈哈哈哈……”
两人齐声而笑直笑的门外站着的郁南风有些震愣,他开口询问夏一生的伤势,萧梧摇了摇头,“不谈这些,只要她还活着,我就算穷尽天下之力也要将她治好,她是我白楼的堂主,也是萧某的救命恩人,我曾见过断筋重续的例子,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只有萧梧这种人说出这般与天争命狂妄无畏的话才能令人信服,郁南风的心稍安,他这时才着眼于萧梧身上的刀伤,除去欧阳嗔造成的不提,共还有四处,主要分布在握剑的手上,萧梧身上的伤都不重,但这四处刀痕却十分诡异。
伤口浅薄,但十分杂乱,一处伤里好像包含了数十道的刀风,由此可以想象现场之乱,唐詹死时郁南风虽不在唐家堡中,但他回来后却也曾去唐詹卧房中看过,遍地都是这样的痕迹,当时不知是刀,还以为是形状古怪的剑,而今看来,这两处伤痕分明一致,该是同一把刀所为,同一把剑形的刀。
“萧楼主可否告知此伤是何人所为?”
“伊贺椿,大概十几年前的东瀛第一,郁堂主不曾听说过吗?”
郁南风摇了摇头,“我十几年前有大部分的时间都不在中原,但我也曾从另外两位堂主口中听说了这个人。”
“萧某劝郁堂主一句,倘若你遇到她绝不能硬碰,否则贵门门主和夏一生就是你的下场,报仇不急,命可只有一条啊。”
“我明白。”
郁南风抱拳道:“现在的上京太乱了,郁舒不能在此久留,我会尽快带他离开,还希望楼主不要见怪。”
“我还是那句话,只要郁舒自己愿意,我绝不会强留。”
“多谢。”郁南风撇过头去,只见回廊的转角贴边站着一个人,抱着刀曲着一只腿,默不作声。
郁舒面前的灯笼在风里摇摇晃晃,他已经在这里站了好一会儿了,萧梧和郁南风的话也听得八九不离十,想起来自己已经在上京里呆了不少的时日,也算博得了小小的名头,但却也受到了局限。
上京说好不好,说坏不坏,毕竟是朝廷重地,寻衅滋事肯定不许,大多数江湖人也很规矩,但总像困在笼子里的鸟更多一些,郁舒常常觉得自己是出了郁家村的监牢,却掉入了一座更大的监牢里头。
如果可以,郁舒其实也想回唐家堡一趟,为了自己模糊不清的记忆,也为了能够突破武学上的限制,他还想去了解了解唐曲与唐詹,兄妹姐弟一场,究竟谁对谁错,谁负他更多。
“明日我便同你启程。”
郁舒只说了这一句话便转身离开了.
郁南风欣慰的一笑,“萧楼主,那我先回客房收拾收拾,今日蒙你之恩,若有机会,唐门再报。”
“嗯。”萧梧背手行过,他还有事待办,屋里躺着的便是最紧要的那一件,说不担心是假的,只是萧梧更着眼于解决问题。
“思奴,苗疆的人来了吗?”
“还不曾,半月多以前的书信了,怕是路上耽搁了,毕竟风雪大。”
“他们若是到了,立刻先带来瞧瞧夏一生的伤势,苗疆稀奇古怪的东西多,说不定能寻出个办法来……咳咳……”萧梧捂着嘴轻咳了两声,这一晚他也消耗甚剧,此时寒气入体,一松懈也就疲累起来了。
唐思奴赶紧上前扶住了他,“楼主,你先去歇歇吧,苗疆的人我来等。”
“也好。”萧梧往隔壁房间走去,“我今晚宿在这里,和衣而眠,如果有人来了直接带进来就是,免了那些规矩。”
“思奴知道了。”
唐思奴将萧梧扶入房中后方才离开,他当空吹一声口哨,自天上俯冲而下一只金喙鹰凖,他从袖中掏出一张卷纸塞入竹筒中绑在了鹰腿上,鹰迎风雪振翅而上,转眼便消失无踪了。
这时,只闻有人来报苗疆的人到了,唐思奴抖了抖身上的积雪,去往外堂。
来的是个少年和个小姑娘,唐思奴见了那少年,向来冷静漠然的脸上也有了些微喜气。
“岐公子请随我来。”
刚落马的岐连与多言还未弄清楚情况便被唐思奴挽着手往内行,一路走一路化雪,滴滴哒哒的往下淌水,唐思奴这才反应过来,赔礼道:“抱歉,近日白楼事多,上京也乱,夏堂主如今又身怀重伤,怠慢到两位了,等过了这个难关,唐思奴再向两位赔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