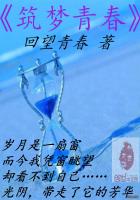赵清枢道:“锡兰的伙计飞鸽传书,说有海客带着玉玺往三佛齐来了。”赵慕炎沉思片刻,低声道:“这里的事情交予你,我带十三昆仑去趟锡兰。”赵清枢道:“大哥何必劳师?西海这几月都在刮西北信风,若海客果真要来三佛齐,顺风行船,不消几日便可。不如以逸待劳。”
赵慕炎道:“我此番并非去寻玉玺,而是顾念家主漂泊海外,去接他回来。若是中途遇到那帮海客,也顺道取了玉玺。待我送回家主,便去中原报仇。”
赵清枢微微颔首,若有所思,忽然指着阿六叫道:“就这娃娃,听归叶禅师说起,是从天竺来的,海船遭了贼寇,不如问问他玉玺的消息。”阿六坐在黑岩上,突然看到两人望向自己,心头不觉一紧,手脚并用地滑下地。
赵慕炎下马走来,道:“小少年,我们问你个事儿。”阿六看他高大轩昂、虎目剑眉,只觉得气势逼人,脚下一时犹如生了根,动弹不得,结结巴巴说道:“大人,甚么事儿……”赵慕炎哈哈笑道:“你这少年甚是可爱。无他,我且问你,可是从天竺而来?”
阿六老老实实答道:“我们海船从古雅出发,快到锡兰了遇到海盗。”赵慕炎问道:“那海船呢?这几日不曾有天竺来的大船进港。”阿六回想这几日遭遇,不禁眼眶泛红,道:“海船遇到大海蛇,也不知如何了,我和阿兄、李老儿坐着小船来的这儿。”
赵慕炎还要再问,赵清枢附耳与他说了,赵慕炎叹道:“那回回刺客委实可恶,再问你一个问题,若你答得好了,我便去三佛齐宫中杀了那回回,与你报仇。”阿六眼睛一亮,道:“当真?”
赵慕炎点点头,低声问道:“你们来三佛齐,是否带了贵重货物?”阿六摇摇头,道:“我们是逃难来的。”
“大哥,与他直说了罢。”赵清枢急道:“是否见过传国玉玺?”阿六心中大震,心转数念,反问道:“两位大人,可认识三佛齐将军梁衷?”
两人闻言一怔,赵清枢道:“我们的确知晓此人……此人不是别人,正是家父。不过,梁衷只是化名而已。你如何知道这个名字?”
阿六脱口而出:“无妄道人告诉我的。”赵清枢闻言一震,扳着阿六肩头急道:“先生何在?”阿六肩膀单薄瘦弱,被掐得痛彻心扉,急喊道:“清枢大叔,容我细细说来。”
赵清枢自知失态,放开阿六,歉意道:“对不住,先生是家父的知己好友,也是清枢最敬重的长辈。自从二十年前被老家主逐出山庄,便立誓此生不再踏足中土,也不参与朝代更迭的恩怨。”
赵慕炎道:“现在说罢,无妄道人在何处?”阿六低头嚅嗫道:“恐怕……恐怕已经不在人世……”赵清枢笑道:“小娃娃莫非寻我们开心?先生精通易理,可知前后百年,岂不会趋福避祸?”
阿六面上一红,梗着脖子道:“两位是好人,我杨六从不对好人说谎,是我亲眼看着大海蛇碾碎了船楼,先生和他的奴隶都在楼里呢!”赵清枢眉头皱起,却听赵慕炎冷冷道:“那老家伙绝招便是金蝉脱壳,说不准早躲到船舱里了。只是借这娃娃的口骗人,我们比较容易轻信罢了。”
赵清枢长舒了口气,笑道:“那也是,先生纵横捭阖,多次死里逃生。连元廷都拿他无可奈何,更何况是一头畜生。”两人相视而笑,却听阿六支吾道:“无妄道人说了,要我找到三佛齐汉人将军梁衷,便能回杭州……”
赵慕炎闻言沉思半晌,忽然讪笑道:“如此说来,那个老家伙要你送玉玺去杭州?”阿六闻言一愣,点头道:“是……”赵慕炎道:“那玉玺呢?”阿六想到李老儿临死的样子,心头一硬,张口就道:“李老儿与回回刺客争夺时候,落入海里了。”
赵清枢大惊道:“落到哪里的海中?”赵慕炎冷哼道:“不管落到哪里的海中,都是决计找不到了。”赵清枢还要说话,赵慕炎道:“罢了,既然玉玺落入海中,这个事情就告一段落,不再提起,家主还在西海,我去接他回来。”
赵清枢低声道:“慕炎兄,玉玺事关重大,这般轻易放弃,恐怕几位叔伯那里无法交代……”赵慕炎自顾自地看向阿六,问道:“小少年,我的神机舰日行千里,若是跟我去西海寻回家主,必定带你回去杭州,你看如何?”
阿六急道:“我不识得你家家主,一起去了也是无益,不如带我去码头,寻一只海船回去。”赵慕炎道:“如今西北风正起,都是从浙闽来的船只,如何有回去的?”阿六道:“没事,我在码头做几月苦役,挣够了盘缠就可以回去啦。”
赵慕炎又劝说一阵,见阿六仍是不依,便冷笑道:“如此说来,小子是不肯跟我走了?”阿六心头一惊,转身要逃,赵慕炎猿臂轻舒,拽着阿六的领子提了回来,阿六惊叫道:“归叶和尚,快来救我啊。”归叶正在左近,闻声而来,洪钟也似的声音喝道:“赵家兄弟,怎地出手为难一个孩童?”
赵清枢也劝道:“慕炎兄,玉玺找不到便罢了,这小童凄惶,就算了。”赵慕炎冷哼一声,将阿六手脚缚好,放在马上,道:“大和尚,我三弟媳的事还没与你做个了结,可不要自讨没趣!”
归叶面色涨红,昂然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于心无愧。这孩儿失了兄长,又身中剧毒,经不起你这般折腾。”赵慕炎哈哈笑道:“中了什么毒?海剑山庄庄主清虚道人善解百毒,随手给他解了就是。”
归叶沉声道:“不是普通的剧毒,而是波斯毒药柔筋散。”赵慕炎面色一沉,自语道:“那回回刺客竟有此种毒药,不可能……难道是,那个人,又回来了?”赵清枢奇道:“慕炎兄,几十年了,家里长辈提到‘那个人’总是摇头叹息,你们说的那个人究竟是谁?”
赵慕炎望向归叶,归叶面沉如水,苦声道:“当年山门数位长辈,身中此毒,死状极惨,只知西域众高手中,有一位蒙古人收服的山中老人,此人服食奇药,已经活了数百年,武功之高,令人乍舌。”
赵慕炎颔首道:“此人无名无姓,或者说,知晓名姓之人要么寿终而死,要么被他所杀。唉,当年慕炎还是孩提,亲眼见得三叔四叔身中剧毒,浑身融化而死。所幸先师承阳子前辈修成出关,亲身前往中原,时值元廷捕杀武林正道,先师带领汉家高手上百人迎战,西域武者全军尽殁,唯有这山中老人施展毒功,力敌众人,却还是被先师打败,从此立下毒誓,永生不得再入中原。”
赵清枢闻言不胜唏嘘:“先师正气凛然,独步古今,如今一去,宛如大树飘零……”赵慕炎道:“我辈若不接过先师衣钵,中原武林岂有出头之日?如父亲那般沉迷于商道,钱是赚了不少,这中原,却是回不去了……”
阿六叫道:“说得对,回了中原好把我放开。”归叶走近阿六,赵慕炎斜刺里一闪,挡在前头,道:“这孩童慕炎还有要用,待事情了了,自会替他解毒,自会送他回家。”归叶沉声道:“和尚受故人之托,非得护得这娃娃周全。”
赵慕炎冷声道:“故人又是谁人?”归叶道:“不是别人,正是檀越尊父。”赵慕炎朝天大笑,道:“我父亲扬帆南洋,眼中只有黄白之物,怎会识得这褴褛童子?”归叶道:“两天前,贫僧收到令尊飞鸽传书,书中只说要救下杨六小友,好待他回来。”
赵清枢劝道:“慕炎兄,既然是令尊的意思,便留下徜徉几日,待船队归来了,再做定夺。”赵慕炎低头默思,脸上阴晴不定,忽而喝道:“老子偏不信这个邪……十三昆仑何在?”
远处几名随从齐声应答,气势赳赳而来,归叶放声断喝道:“赵家兄弟,和尚虽敬你武功高强,却不能失了故人之托。”袈裟一鼓,双拳犹如铁钵,次第打来,赵慕炎暗喝一声“好”,以掌化拳,出肘反攻归叶丹田,归叶身形一闪,一招龙爪手撕下一片衣衫。两人顷刻间交手,待赵清枢欲出手相劝,已然打过三合。
几名随从围住归叶,借着火光,只见几人面貌狰狞冷酷,目光直欲择人而噬。归叶口宣佛号,朗声道:“赵檀越,和尚受人之托,以死守信,若今日不敌,还请不要伤了杨六小友。”赵慕炎微微颔首,道:“禅师多虑了,慕炎绝非残酷无良之辈。”
那几名随从纷纷活动筋骨,吧嗒之声不绝,赵清枢晓得那是极厉害的硬气功,一旦发动,必有所伤,于是厉声喝道:“十三昆仑,如何敢对归叶禅师不敬?毁坏三宝,想着下十八层地狱么?”
十三昆仑虽是南洋武功极高强的土人,却笃信佛教,一听此言,不觉面有愧色,双手合十,求告道:“归叶大师,不如听我们主公一言,也少得许多纷争。”归叶摇头道:“除非和尚随你们出海,才放心得下。”
赵清枢拍手道:“如此极好,这般出门也有个照应。”赵慕炎本是心高气傲之人,闻言啐道:“本公子行事何时轮到和尚插手?有这身武艺,便是天王老子也要让我三分!”手上加力,震开归叶铁掌,反手擒他臂弯,归叶手臂滑如泥鳅,脱开钳制,却扣向赵慕炎脉门。
两人斗得难解难分,赵慕炎望向十三昆仑,怒道:“一群狗奴才,要你们何用?”十三昆仑进退两难,只得哀求道:“主公,若要我们兄弟毁坏三宝,不如直接取了我们性命。”赵慕炎急道:“如何要你们打杀和尚了,就围住他,别让他跟着我就是。”
言罢身下一矮,一招扫堂腿逼退归叶,十三昆仑上前转眼围得密不透风,归叶不忍出手打伤,一时又难以推开,急得满头大汗。
赵慕炎哈哈大笑,转身正欲上马,却见骏马打着鼻响,四蹄躁动,再往上一看,竟是一名青衣小厮不知何时已跳到马上,胡乱拽着缰绳,不禁雷霆大怒,断喝道:“大胆家奴,还不下来!”
那小厮听得这雷霆之声,险些从马背上掉下来,阿六叫道:“快点打马,打马!”说着手脚乱挣,恨不得自己行事,小厮吓得大哭道:“荆条呢?我的荆条呢?”
赵慕炎冷哼一声,走近几步,伸手就要拽下小厮,那小厮情急下,手中荆条一把抽在马臀上,马儿长嘶一声,吃痛狂奔起来。赵慕炎面色铁青,喝道:“来人啊,拦下那匹马来!”十三昆仑闻言散开,发足狂追,那马只顾奔走,竟往人群中撞去。
老管家正在呵斥下人,身后惊马疾奔而来,丫鬟小厮们纷纷惊叫四散,老管家转头一看,手杖将地板敲得咄咄作响,怒骂道:“好你个七鸡公,吃了熊心豹子胆呐,还不快给我下来!”七鸡公骑虎难下,吓得心胆俱裂,抬眼瞧见平日刻薄的老管家,手中缰绳下意识一拉,竟而避开人群,直往山下跑去。
却说阿六横卧在马背上,心跳如鼓,待到心中稍定,已经奔出半个时辰,但见四下漆黑,耳边风声呼呼,便叫道:“七鸡公,别瞎叫唤了!看看有人追来没?”七鸡公还在闭眼惨叫,闻言叫道:“我眼睛都不敢睁开,哪里晓得有没有人?”
阿六哭笑不得,道:“早知如此,还不如甭救我了。这马儿要失了前蹄,咱俩被翻下山去,那不得摔得爹娘都不认得。”七鸡公闻言伤心更甚,哭喊道:“爹娘啊,救命啊,俺一辈子都不骑马啦。”
阿六怒道:“整日便晓得哭嚷,你这般无用,活该一辈子见不到你爹娘!”七鸡公一怔,认真道:“是了,这般无用,怎生寻得到爹娘。”下了好大决心,才睁眼来看,只见惊马正跑向一条陌生的小径,四下林木甚密,枝叶刮在脸上生疼。
七鸡公惊叫道:“杨兄弟,死啦,死啦,咱们慌忙跑到野人山里去了。”阿六奇道:“甚么野人山?”七鸡公哭丧道:“野人山中自是有野人啦,还藏了许多鬼怪。”阿六也觉害怕,便问道:“可知道是何种鬼怪?”
七鸡公道:“飞头蛮,僵尸,人蛇,还有许多,平日听年纪大的说起,不下几十种呢……”正说时,月光下一条黑乎乎的藤蔓急速迎来,七鸡公惊叫一声,慌忙矮下身去,不料那马竟纵身一跃,自藤蔓之上跨过。
阿六身形不稳,立时被颠下马去,七鸡公被带得一歪,也落到地下。两人疼得龇牙咧嘴,恶语直骂,解开绳索,起身看时,那马已经不见所踪,只见四下林木极密,蚊虫飞舞,仔细听来,唯有走兽爬虫窸窸窣窣,时而有山风呼啸而过,夺人心神。
七鸡公颤声道:“杨兄弟,我看不妙啊,咱们还是原路回去罢,顶多被打个半死,可总比这儿送命强。”阿六心下一横,咬牙道:“鬼怪猛兽都是蠢物,机灵点还可以应付,那赵慕炎凶神恶煞,铁定不会放过咱们。”七鸡公赞道:“杨兄弟果然是中土来的,说的话都比七鸡公在理。”
阿六朝天打了个哈哈,得意非凡,却听身边有声音道:“七鸡公?”七鸡公张口要应答,阿六慌忙捂住他嘴,颤声道:“谁在说话?”
七鸡公四处环顾,却不见人影,登时体如筛糠,道:“杨兄弟真不是你叫我名儿?”阿六点点头,放声喝道:“哪里的鬼怪,老子不怕你,有胆出来打一架。”七鸡公胆气一壮,也恶语相向,两人骂得兴起,各自捡了树枝拨拉四周的林木,却一无所获。
阿六啐道:“咱们指不定听错了……”冷不防那声音又隐隐道:“杨兄弟?”阿六只觉一股寒气直上心头,竟答应道:“你……你叫我?”七鸡公失声叫道:“完了,完了,这是人蛇,你若是答应,半夜就要来取你性命。”
那声音却道:“杨兄弟,你是有缘人,随我来一趟。”七鸡公吓得魂不附体,拔腿就跑,阿六却怔怔地答应:“阁下是谁?又在何方?”话音未落,那条横在树丛间的粗大藤蔓竟而活动起来,在树杈间缓缓游走。
月光下,一颗乌黑的蛇头凑近了阿六,咝咝地吐着信子,阿六吓得魂不附体,道:“前辈,小子方才胡言乱语,可不要放在心上啊……”那声音又道:“我在这里待了几十年,总算找到说话的人。你不要走,陪我说说话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