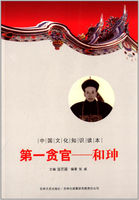嗬,还真是缘份,竟又碰到一起了。
“我是主事的。”李云鹤提高嗓门儿应了一声,大家伙儿寻声一瞧,自动地就让开了道,李云鹤走上前来,冲着对面的官差抱拳一礼:“赖九爷,可少见啊!”又才说:“这宅子是我的,赖九爷有什么话可与我说,这些工匠是我请来拆房子的,这事儿不与他们有关系。”
“哟,感情是李大娘子!”赖九一见李云鹤,顿时将那拽吊的模样拉了下来,摆出副熟络的样子来。“这宅子是你的啊?”
李云鹤点了点头:“不瞒赖九爷,这宅子本是我家的老宅,因着家道中落就失了手。前几****刚从一个姓肖的人那里买来,只说将其修整一下,不想却出了这事儿。”
“不是哥哥看你笑话,你可真够倒霉的!”赖九啧啧嘴说道。
“确实挺倒霉。”李云鹤苦笑道:“不过,谁叫我摊上了呢!”
本来赖九还想敲一杠子的,可见事主是李云鹤这心思也只好歇下了。请了李云鹤到边上,赖九跟李云鹤说,让她不要担心,这事儿赖不到她头上来,只是这工程就得暂时停一下,有些事情还需要李云鹤配合一下。
“这是应该的。”李云鹤点点头应了。
这事儿查就得从肖平安身上查起,不等下午肖平安便被拘到了大兴县衙里,不等打板子肖平安就老老实实地全交待了。“那是我姐夫家的婆子一家,那婆子姓张,打我姐夫考中进士到安阳做县丞起就在我姐夫府里当差了。因着姐夫死后家散了,那宅子便给了我,家里的仆从也是走得走散得散,唯独那张婆子哪里也不去。我看那张婆子也是勤恳忠诚的,便想着她也没个去处便留了她在宅子里。也不知道怎么的,那婆子本是个孤婆子,却不知道怎么的没过多久又冒出一儿一女、孙子、外孙来。我想着家里头的宅子多得是,看她那儿女也是老实人,自是能养活自己的,便也就由着他们在那屋子里住下了。前两年,租住在我那宅子的张相公是个疯子,半夜里病发,杀了自己的婆娘、孩子和家里头的下人,我嫌晦气,便不大到那边去了。张相公他们走后,那宅子里就只住了那婆子一家,去年下半年,有人说要买那宅子,我带着人去看,才知道那婆子一家都吊死在了宅子里头。”说着连连摆手,直道:“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我和我婆娘害怕惹祸上身,这才瞒着没有报官。可真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借给他们房子住,我,我没有害他们啊!”
“你说得这些谁可以作证?”坐堂的县令将惊堂木一拍,厉声喝问道。
“谁?谁能够作证?”肖平安愣了愣,忙道:“有有有,那个说要买我宅子的那个人可以给我作证。”
“你说的这个人是谁?现在又在哪里?”县令问道。
“在哪里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姓穆,好像是哪个府里的管事。”肖平安说。
“哪个府里的?”县令又问。
肖平安使劲地想了一气,才想起来点,说:“听他提了一句,好像他们家老爷姓秦,是在户部任职。”
涉及户部的官员,大兴县令不敢马虎连忙派人上报,一家七口人命案情重大,案子转交给了顺天府,大兴县辅助办案。
顺天府府尹赵志元看了卷宗后就派了人按图索骥,不出两日便找准了这个有一个姓穆管事的秦大人府上,这个秦大人现在已经不在户部任职了,现在已经外放,不过也没有走远,就在保定府任知府。
传了那穆姓管事到堂上来,叫肖平安一指认,果然就是当初去看宅子的人。
一经审问,审出了一段陈年公案来。
李云鹤的父亲李道济擅画,自己创作倒还平常,只是将顾恺之的画临摹得真假难辨。那一年,李家突遭变故,知道是被人所陷害,遭了无妄之灾,却不知道那灾是从何来,今日这公案告破才知道事情的原由。原来,就是从这个张婆子起的。
故事要讲,就得从李道济进京赶考说起。
那年李道济进京赶考,行至保定府的雄县,在县衙县衙见得一帮恶棍欺负一母子三人,便挺身而出,做了回英雄好汉。后来李道济高中二甲,被留了翰林院观政,再后又放去了安阳做县令。在李道济做安阳县令第二年,那年桃花汛闹得十分厉害,李道济忧国忧民整日都在河堤上转悠,有一日,就见那河上漂下来了一个人,忙叫人打捞上来,嘿,还是熟人,就是当年他在雄县所救的那个寡妇张氏。
张氏哭哭泣泣地跟李道济说了一通,道她的儿女叫婆家人抢了去,又闹得她没法在家乡安身,这才一路流浪,有一日没一日地混着,没曾想竟到了安阳县来,还碰到了李道济。
那时候李道济刚和李云鹤的母亲成亲,家里头也正缺人手,也瞧着这张氏可怜,便留她在了府里。
这张氏倒也不错,做事勤快不说,为人也老实,一来二去李道济夫妻倒将她看作了自己家人一般。
却道是好心没有好报,顺顺隧隧地过了二十多年,李道济熬啊熬的终于熬到了京城当了京官,占的位置还不错,顶的是实权的差事。他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一直顺风顺水的,只道是前途无量,却不想祸从天降,莫明其妙地被人安了一个受收贿赂,贻误战机的罪名。李道济本想清者自清,他没有做过那些事,总会真相大白的时候,却不想一下狱就被人不停地折辱,李道济气愤不过,为证清白打破了喝水的陶碗割破了自己的手腕,在墙上写下“冤枉”两个字后便撞墙而死。
非李道济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而是他看明白了就是有人成心整他,为了不让妻儿受到牵连这才轻生自杀的,只是他还不知道这里头更深的牵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