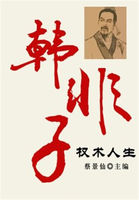进入正厅,早有美食摆在三张案几上。光城县主让夫君居于上榻,自己坐在左侧,郁青坐在右下侧。
“燕郎,羊羹可好?”光城县主亲自奉汤上茶,又面露遗憾,“惜居丧之时,不可备酒。”
塔寒看那金盘银碟之中,盛着四样主菜,胡炮肉、蒸豚、腩炙和羊羹,还有两样点心,油炸的酥脆的截饼和烘烤的松软的髓饼,都是他素日在家最爱食的肴馔,也是光城县主的拿手菜。
胡炮肉以现杀的肥羊肉切细,加入豆豉、盐、葱白、姜、花椒、荜拔、胡椒调味,包裹缝制入羊肚中,盖上灰火烘烤而成,肚味厚重,异香扑鼻。蒸豚,以整只肥小猪和生秫米,加生姜、桔皮、葱白、桔叶调味,放入甑中蒸熟后,再淋上熟油和豉汁盛盘,小猪肉肥美鲜嫩,秫米饭酱香浓郁。腩炙用的是獐子肉,切方寸脔,用葱白碎、盐、豉汁淹渍后,碳火烤制,肉香四溢。
同是胡食,光城县主烹制的羊羹,和上党宴席之上的羊羹,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风味。北地羊羹,现杀活羊,大块解开,羊骨羊肉同头、蹄、肠、肚等下水杂碎,一镬烹之,肉块油腻,汤汁腥膻。光城县主的做法则讲究得多——精选鲜宰上好的羊肋及纯肉,加水、煮沸、去血、撇沫,小火炖熟后,抽去肋骨,切肉成小块,再加入盐、葱头、芫荽,以安石榴汁调味,汤汁清甜,羊肉鲜美。
“县主劳矣!”塔寒拱手示谢,委婉笑道:“北地胡食,日日酪浆羊汤,脱险得归,倒不念……”
光城县主抿嘴一笑,拍拍掌,便有仆妇端上一只双耳漆木鎏金盘,盘中放着三只银盅,各盛着半盅煮得酥烂绵软的豆粥。
“县主妙手调羹汤!”塔寒刻意放大眼中的惊喜,边吃边啧啧赞叹。说实话,这十几日,不啻过了十几年,不测之忧,朝露之危,满满的淤塞在心里,哪里还能有好胃口?以往贪恋的珍馐美馔,全都食不甘味,不过怕爱妻扫兴,只装作吃的津津有味。
“怪哉!北地虏家儿,亦思汉家食!”光城县主打趣,又歪头娇嗔一笑:“妾身尚腌有鳢鱼脯,夫君可食否?”
“有何怪哉?食色性也,人之大欲存焉,遑论胡汉!”塔寒一口气喝完豆粥,笑着摆手,“惟鱼脯,虏家儿不敢领教!”
“燕郎,汝可知四通市鱼鲜贵于牛羊?汝不食,他胡儿食此多矣!”光城县主边笑,边用银著拣了一块腩炙,放入塔寒的食碟中,热切地催促道,“此獐子肉,乃燕郎行后,王兄来府探看妾身所赠。腩炙法最宜,此宜热食,冷则不美矣!”
“唔,元子攸……彦达子……”塔寒心下一动,夹起獐子肉,放入嘴中狠狠地咀嚼着。伴着葱白的辛辣,浓烈的肉香在嘴里四溢开来。香獐香獐,此肉若以亚孜皮亚子腌渍,加点荜拨,或是天竺国的胡椒,应该更提味。只是现在,哪有心思和楚华讨论如何炮制吃食。
“彦达子难得来此四夷里,何故贵脚踏贱地,倒是罕事!”塔寒边嚼边说,毫不掩饰话语中的酸涩之意。
长乐王元子攸,是光城县主的兄长。按理说塔寒在洛阳并无外援,应仰仗妻家扶持,但两家亲戚,平日里并不常走动。只因当初元子攸自认出身显祖苗裔,对其妹楚华缔结柔然外藩,心下不满,不过因胡太后赐婚,楚华又因此封了县主,才表面上承情而已。
可惜,他元子攸就算出身显贵,却连父荫也无福消受,不过是个苟且偷生的穷鬼罢了!
人称六皇叔的彭城王元勰,是高祖孝文帝生前最为信任倚重的六弟,密助孝文帝迁都、扶助幼主登位,是一位文才武略、孝悌忠信的贤王。元勰娶陇西李氏、司空李冲之女李媛华为王妃,生嫡子元子攸、次女元楚华、幼子元子正。无奈宣武帝元恪偏信外戚高肇,猜忌父皇遗命辅政的几位皇叔,尤其是这位功高震主的六皇叔。虽然元勰早有“周旦遁逃”、“忘退之祸”的先见之明,在高祖生前便请辞官,并手持高祖不杀遗诏,最终宣武帝还是听信高肇谗言,将其废黜爵号、贬为庶人,最终以毒酒逼死。
父死母丧后,元子攸兄妹三人只能在父亲舍宅的京郊龙华寺艰难度日。同宗连宗的王爷王叔们无不避嫌,唯有清河王元怿和李氏舅家时常接济。直到元诩帝登基、高肇被除,元怿力主为元勰昭雪,元子攸才得以承袭封爵,方有温饱生活。
好景不长,又逢权臣元叉当道,觊觎彭城王宅,元子攸恐前情重演,将贵里府邸和王子坊的别墅统统拱手相让,自己再次躲入龙华寺,装聋作哑避世六年,直至元叉被处死,才敢出头露面。
塔寒对这位妻兄的为人,原本就一百个瞧不上,拘拘儒儒、安弱守雌,浑身上下没一点男儿血性!却还遭这种人嫌弃,心中自然不忿!平日里在朝中街上见了,也从来没个好声好气,私下里更是彦达子长彦达子短,毫不吝啬刻薄言语。特别是在光城县主面前,一提起彦达子来,反而更为置气。
光城县主瞅着夫君,微笑着抿嘴不语,半晌轻念了一句,“虏家儿!”
“虏家儿?犹无义之蛮夷、累世之勍敌、天亡之丑虏也!”塔寒推开碗碟,没好气的回道。
光城县主依然笑而不语,往塔寒手里递上一条熏了浓重乳香的汗巾。塔寒拿起抹了一把脸,又甩回县主手中。见光城依然笑靥如故,自己倒也笑了,“彦达子此次来,可有何言?”
虽然对妻兄元子攸心怀成见,但对于自己的妻子、光城县主楚华,除了容貌并非绝色之外,塔寒实在挑不出刺儿来。
楚华儿时际遇坎坷,但性格和顺,为人安分守常。塔寒贪好侈衣美食,从小操持家事的楚华,不惜亲手学做各种胡食、汉食,甚至南方的烹鱼之法,无不精通。四夷里的新奇食法,倒有一半是从朔方郡公府里流传出来的。两人结亲时,楚华十五,塔寒十六,少年夫妻结伴十年,斯抬斯敬,伉俪情深。唯一的遗憾是至今膝下无子,楚华体质羸弱,两次怀上身孕,均小产告终。
对于塔寒与娘家的不虞,楚华并无抱怨。元子攸遭元叉排挤避入龙华寺那些年,楚华时常接济,却都避着塔寒偷偷摸摸行事。塔寒知道了,必定会尖牙利嘴的数落她几句,她也不以为意。不过多数时,塔寒都是装作不知而已,并暗允楚华将内弟子正接入府中抚养。骨肉相亲,人之常情。其实看到楚华有兄有弟,塔寒心里少不了暗自羡慕,老哥阿那瓌如此对自己,自己心里还常怀雁序之情,何况幼时相依为命的元氏兄妹呢!
“别无他言,乃嘱妾身养生而已。”
光城县主俯身端起银盅,用银调羹搅动了一下豆粥,又幽声轻叹,“幼年居于伽蓝,缺衣少食,饔飧不继,莫言羊汤鱼脯,便是舅家接济豆粟,亦不敢费柴慢煨,惟以热水浸泡一日,再以小火收之。先奉兄长,再奉幼弟,妾身惟以汤汁果腹,便觉美味异常……今每日持梁齿肥,而不知其美,可谓美味不可多食焉。”
光城县主几句话说的风轻云淡,塔寒不以为然,一旁的郁青却听得目瞪口呆。塔寒见状,有意努努嘴:“楚华,且惊着青儿!”
郁青听说,立刻飞红了脸,放下杯箸,两眼只瞄着塔寒。这孩子在塔寒面前一向无赖,在光城县主面前却十分拘谨。
“傻青儿!”光城县主莞然而笑,“汝至府上已近六载,却不知吾生于王家、长于****,自小不知富贵滋味,与汝幼时无异。”
郁青瞪大眼睛,摇摇头,“青儿怎敢与县主相比!青儿出身军户贱口,县主乃一代贤王之女,太师领司徒公彭城武宣王墓志铭之上,高祖孝文皇帝尚赞老王爷‘清规懋赏,与白云俱洁,厌荣舍级,以松竹为心,’字字确凿,谁人不知!”
塔寒见已不待阻拦多嘴的少年,转头看光城县主,果然见她愀然变色,“忠奸、贤愚,不过乃身后声名,儿女惟知无父无母之痛……”
眼看爱妻便要戚戚然泪眼洗面,塔寒突然转起一念,一板一眼的念诵起来:“问松林,松林几经冬,山川……山川——楚华,此下阕……”
这首《问松林》,乃彭城王元勰少年时,随高祖孝文帝前往平城时,路经上党铜鞮山时,奉旨所作。据说十步成诗,得高祖盛赞。塔寒此次前往上党,楚华以父亲诗作送行,望夫君能奉旨而去、平安而归。
“山川何如昔,风云与古同——汝皆忘矣。”楚华扭过头,忍不住接了下阕。塔寒顺势扳过她的肩头,笑着示意她看郁青——郁青虽是少年家,体格却比一般成年人都高大壮实,坐在那里像一座小山似的,外表看着甚是威武,脸上却依然一团的孩子气。这会儿,正懊恼的用蒲扇似的手掌,悄悄的打自己的嘴呢。
楚华不禁拭去眼泪,噗嗤一笑,“青儿,且食罢!今日正月晦日,不可复添晦气!咱同食粥,一为侯爷扫晦气,一为府上送穷神罢!”
郁青见县主破愁为笑,重又兴奋起劲,夸嘴道:“县主尽放宽心,上党尔朱将军何等威风,侯爷笑言数语便解危难,着实机变如神!”
塔寒看了郁青一眼,那孩子赶紧乖巧的转移了话题——“既为晦日,饭毕,孩儿陪县主洛水游船,送晦气可好?”说完,觑了一眼塔寒,小声嘟囔道,“吾忘之,国丧,不可行乐也……”
光城县主没接话,自斟了一杯茶,郑重的向着郁青擎起,“青儿,汝虽年幼,却是少年健勇之时,此次保侯爷出使,平安归返,汝功不可没,母亲以茶敬之!”
“县主,母亲,青儿当不起!”郁青慌忙退离坐榻,膝跪向前,拜伏在地。
塔寒也忙说,“楚华,青儿乃你我义子,小子后生,如此拘礼,倒折煞他也!”
光城县主突然间泪眼婆娑,急声问道:“燕郎,闻兄言,汝此行……凶多吉少,北地兵戈抢攘,尔朱人强马壮,汝兄亦为其所恨,燕郎如何安然脱险?”
塔寒心中猛然腾起一丝不快,脸上却不动声色。“汝且放心,彦达子亦多虑也。塔寒虽无止戈散马之才,然奉旨出使,北地小胡安能目无主上。”
一天之内,接连面对两个女人的质疑和眼泪,怎能是赏心悦事?便是同床共榻的妻子,便是她全为忧虑自己的安危,但毕竟出身不同,各有际遇,举事事成则已,一旦败露,情逐事迁在所难免。
“主上?今朝廷……皇太后陛下亦……汝非其……”光城县主显然疑虑未消,却又难以直面疑惧。
“先意承颜,阿谀顺旨,逢其所喜,避其所讳,贿赂并行,做小伏低……塔寒一域外小藩,势孤力薄,人微权轻,死里求生之道,尚有何术?不过低眉折腰罢!”
塔寒心中苦涩,言语中带出明显的不快。光城县主平时颇善体情察色,此时却置若罔闻,继续紧逼:“爱生恶死,乃人之恒情,夫君所行,皆为全躯保妻子,今祸乱交兴,吾心甚为忧惧,恐有不讳之变……夫君,但请勿瞒妾身,妾身惧之——”
“汝病体初愈,多虑也。”塔寒冷言敷衍,又对着一直伏在榻前的郁青命令道,“青儿,汝且备车马,须臾吾将往市肆。”
郁青向光城县主拜了拜,然后诺诺起身,带着一脸的如释重负,转身一溜烟的去了。
“燕郎,妾身虽畏贫贱,亦怕富贵,惟愿两厢厮守,长相安好……”
见郁青离去,光城县主不再有所顾忌,膝行至塔寒身边,紧紧抓住他的手,一句话未说完,已经嘤嘤的哭出了声。
塔寒暗暗苦笑,楚华啊,你父母的前尘往事犹在眼前,两厢厮守,长相安好,在这荒唐乱世,在这贵胄人家,恐怕是最奢侈的愿望了……又说什么虽畏贫贱、亦怕富贵!看看你兄长活得狼狈样吧,世间可有全福避祸、四角俱全之事?不置于死地,焉有生路!
元子攸曾说,妹妹楚华的容貌酷似亡母。此刻,看着光城县主悲切无助的模样,塔寒倒想起这位平生素未谋面的岳母大人来。宣武帝宣彭城王元勰进宫那晚,王妃刚好诞下幼子元子正。王妃苦苦哀求丈夫不可入宫,元勰也不舍妻儿,无奈黄门官强逼,诀别而去。次日凌晨,黄门官将元勰裹尸送回,王妃看到丈夫的死状,恸哭道:“皇天!忠而见杀,可有天理!高肇枉理杀人,天道有灵,汝还当恶死!”竟当着黄门官的面,将宣武帝和高肇一起骂在内,随后咯血不止,不几日也气痛而亡。
但自己的妻子光城县主虽貌似汉女,并不是刚烈的彭城王妃。楚华的眼神里从来看不到扎人的利刺,她是温和的,也是柔弱的。幼时的际遇,让她惧怕命运的变化,自然也难以承担变化的后果……楚华是个可以忧戚与共的好妻子,但恐怕不能助自己达成心愿,她的焦虑和无助,反而会扰乱自己的决心。
塔寒这样想着,嘴里仍以软语虚言安慰,“放心,吾必不负汝意。”
光城县主抬起一双泪眼,“信乎?”
塔寒笑笑,不禁替她拢了拢松乱的发髻,微微点了点头。
“燕郎,不若走之!”光城县主泪光一闪,随后更紧的依傍在塔寒身侧。
“走之?何往?”塔寒几乎要冷笑出声了。“碛北?南朝?何地可容留我等?!”
“燕郎幼时居于西国——”但看到夫君的脸色,光城县主终于没再继续说下去。
案几上,残羹冷炙。厅堂内,阒然无声。团聚的家宴,久别的惦念,被心思各异的猜忌冲淡,余留即将不欢而散的清冷。
塔寒从光城县主的怀中抽出僵硬的胳膊,强笑了一下:“县主安歇,吾往市肆——”
“燕郎稍停!”光城县主挺直身子,紧紧拽住塔寒的衣袖,“女生外向,从夫之意,夫为何事,吾皆从之。妾身笃挚一心,只为君计,惟有一事——”
“燕郎——”光城县主黑亮亮的眼睛瞅着塔寒,再次欲言又止。过了一会儿,似乎终于鼓足了勇气,红着脸说:“燕郎,吾难生养,汝在外若有一男半女,不论出自何人,定送与妾身善养之……”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塔寒将妻子揽入怀中,纵声大笑。
光城县主安然偎在丈夫的怀中,不解他此时吟诵父王新婚时赠予母妃的诗却是何意。又听他似哭似笑,轻抚着自己的脸庞,“楚华楚华,汝亦执者,汝所忧所惧之事,不过为此,真乃妇人女子也……惜哉虏家儿,不解汉儿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