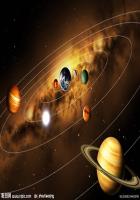第十一章 风云
就在晓惠满月后的几天里,袁树国从锡城写了一封信给袁树军夫妇俩。袁树国告诉他们陈媛媛又给他生了个男孩子,他给两个孩子分别取名叫晓栋和晓梁,为的是想让两个男孩将来成为社会的栋梁。
日子在有了小生命以后的点滴幸福中度过,太阳不用说一句话便将人们身上的衣服一件件的脱到单层,袁树军在工作之余喜欢领着钱郁英抱着晓惠到村里的小河边捉蛐蛐,或者将她们扔在岸上自己跳到河里独个儿享受摸鱼的乐趣。有时,到了晚上,黑暗的草丛周围亮晶晶的停留着美丽的萤火虫,他们便会抓几个萤火虫放在透明的瓶子里逗晓惠开心。
晓惠在父母的宠爱下,一天天成长起来。到了十一个月大的时候,她开始练习走路了,起先晓惠的胆子总是很小,似乎迈不开脚步,一直需要大人的帮助。有一天,钱郁英和袁树军商量着怎么能让晓惠勇敢地迈出独自行走的这一步。袁树军二话没说就将晓惠抱到离他俩较远的墙边,然后再回到钱郁英的旁边看着晓惠。
晓惠困惑地看着父母,一时着急了起来,她张开双臂,样子无辜地快要哭了,她见爸爸妈妈都假装不理她,就使劲儿地拍着双手发出声响。钱郁英和袁树军仍然不理睬这个既可爱有可怜的小家伙。这时,晓惠好象意识到自己可以走过去,她看着父母的眼光,由原先的无助转变成自信,她一鼓作气,面带着纯纯的笑向钱郁英身上扑去……
成功了!钱郁英和袁树军兴奋致及,开心地将她抱了起来,两个人在空中虚抛着晓惠,把晓惠乐得“咯咯”直笑。从那以后,晓惠就喜欢自己走路了,出门也不用两个大人抱,而且,她几乎很顺利的,没有跌倒过几次就进入了起跑阶段。
一天,工厂休息,袁树军早上就带着晓惠到河边看小鸟。旭日刚刚升起来,红红、圆圆的倒映在小河的一端,河面上的晨雾淡淡的化开,象一层薄薄的轻纱,只听到草丛边发出一只小鸟微弱的轻叫声。晓惠走过去,看到一只小鸟正挪动着身体怎么也飞不起来,晓惠“呀呀,啊啊……”地用手指了指自己的脚跟前,示意爸爸过来看,袁树军走了过去,一看是一只受伤的小麻雀,也许是哪个枪法稍差的猎手用气枪击中了它的腿部。袁树军将小麻雀捧在手里对晓惠说:“哎呀,是只受伤的小麻雀,我们把它带回去帮它疗伤吧。”晓惠虽然还不会说话,但她明白了爸爸的意思,开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袁树军领着晓惠回到家,看到钱郁英手里正捧着一封信在看。钱郁英见丈夫回来了,便将信交给他。袁树军先找了根绳子栓住受伤小鸟的一只脚给晓惠拿出去玩,然后再接过妻子手中的信,信是大哥袁树国写来的,字迹非常潦草且歪七扭八,好多字要费好大的劲才能勉强辨认出来。
弟弟:
这些日子我快崩溃了,万不得已才给你写这封信。你嫂子在两个月前身体开始不舒服,经常咳嗽,时而还会腹痛难忍,她家里人带着她到医院看,可查来查去也查不出是什么病。于是她家的亲戚在村里找了人给她算命,说我们夫妻俩的属相相克不能生活在一起,便把她和两个孩子带回了勤新村。现在我的生活变得一团糟,药也记不得要吃多少,经常大小便失禁,我想我快垮下了。写这封信给你,完全是在我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写的,但我已握不紧笔了,心里想写的字怎么也想不起来该如何写出来,如果你能抽空来一趟锡城的话最好帮我到勤新村去了解一下陈媛媛和两个孩子的情况,没有他们在的日子,我每天就象行尸走肉般,快不行了!
哥:袁树国
袁树军放下了手中的信,心情异常沉重,他万没有想到一个成长在知识分子家庭的陈媛媛,竟然还有那样愚昧无知的亲戚和家属。大哥的生活会变得如此不堪一定是那些人从中搅乱了他们美满的生活。
这时,晓惠手里拽着那只受伤的小鸟,哭着走进了屋。原来,晓惠看小鸟飞不起来,就牵着绳子的一头甩着小鸟帮它飞起来。哪知小鸟经受不起晓惠的几下折腾被活活的晕死了。晓惠见小鸟没了动静,就哭着跑来找爸爸。
袁树军抱起哭泣的晓惠,耐心地安慰道:“晓惠不哭哦,等爸爸有空再给你逮一个回来。”晓惠听明白后“恩”了一声点点头。
袁树军看看妻子的眼神,有一种请示的期盼,钱郁英看出了丈夫的顾虑,抱过他手中的晓惠说:“你要是实在不放心,就去一趟吧,你马上到单位去请假,我在家里帮你整理行李,你去了锡城,家里你不用担心的,我会照顾好晓惠的。你大哥也怪可怜的,真不知道他一个人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那,我这就去单位请假啦!”袁树军其实是知道妻子会答应的,但他最不放心的还是晓惠,他太爱这个孩子了,怕他真的走开一段时间会适应不了没有爸爸的日子。
袁树军到单位请了假,他打算第二天一早去锡城,他不想马上就离开是因为他想在家多呆半天的时间,陪陪晓惠和妻子。
晚上,吃过晚饭后,袁树军拉着钱郁英说出去走走,钱郁英抱着晓惠走在丈夫的身旁,却不说一句话。这几年,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一种默契,她知道丈夫现在需要的是安静,她只想和丈夫走在一起享受夜晚的美景,她不想因为自己一句多嘴的话而影响了丈夫的思绪。
空气里夹杂着清爽的河土腥味,他们就这样默默地走着,生怕多说一句便会触动某个心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袁树军就轻手轻脚地起床洗漱完了做早餐吃。因为,他不想让晓惠知道爸爸要离开她一段时间。他不想见到孩子离别时的哭泣,那样,他会不忍心离开。袁树军吃完了早餐便背着行李匆匆出门了。
太阳慢慢升起了,夏日的太阳红得象火。袁树军顺着小河一路走,有一种惆怅而惬意的矛盾感。
人世间的事情总有些奇怪,特别是缘分这东西,更让人说不明白,袁树军觉得大哥和嫂子原来就是两个生肖都不相配的人,一个属老鼠,一个属蛇。两人差六岁,应该说是相冲的。可命运偏偏又将这两个人栓在了一起,一旦离开了对方就魂不守舍。
他看看河水碧绿,花草繁茂,树木葱翠,河里的鱼儿自由嬉戏,一切美好的生态物质都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生机勃勃。而现实的生活中却有那么多的不尽人意。此时,他多想成为一只天空的飞鹰,威猛而来去自由地保护自己的家人。他已经好久没有细细地去观赏身边的这些景物了,之前总是无规律地为生活的一些琐事而思绪万千。
一路颠簸的车终于在傍晚前赶到了锡城。虽然天空的云彩红透了半边的天,夕阳渐渐落下的景色也是那样的美,但袁树军却无暇欣赏了,他几乎是一路小跑着冲回了袁树国的住处。
袁树军一推门,发觉房间里臭气熏天,地板上到处是滴落的拉稀粪便,床上的被褥表面印着黄色的尿迹,象一幅幅国际地图。桌上的碗筷表面发了厚厚的一层霉;衣物杂乱地堆放在每一个角落。一只野猫从窗户外面跳了进来,窜到了桌上把袁树军吓了一跳。若不是看到藤椅上坐着个半死不活的袁树国,不知道真相的人走进来肯定要错认为这里已被“四人帮”抄家了,来这里居住的只不过是一只流浪的猫。
怎么会变成这样了?袁树军一阵心酸,他不忍去打搅坐在藤椅里似睡非醒的原树国,他找来笤帚和抹布将屋子打扫个遍。他象个家庭主妇似的把床上发着恶臭的被褥全部拆洗了换上夏天的凉席垫在床上。最后他到厨房烧了一大锅的水给袁树国洗澡。袁树国象个小孩子不停地张开嘴想说话,但他已经讲不出话来了,总在喉管里发出沙哑的声音,袁树军只是给大哥檫洗着,一声不哼。他觉得自己要是开口说句话,会忍不住流下泪水,一个大男人在这个时候哭,会很没有骨气的。谁知,袁树国反而在浴盆里“嗷嗷……”地哭了起来,那声音如同一个苍老的冤魂在哭诉着自己的痛苦。袁树军闭上眼睛,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不想听到这样的声音,但又不得不去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他知道这个时候和大哥说什么都是无能为力的。他惟有做好当下的事情,然后再去勤新村打探陈媛媛和两个孩子的消息。
袁树军帮大哥穿好衣裤后,用剃须刀帮他刮掉那貌似野人的胡须。袁树国直挺挺地坐在那儿,象个僵尸般目光无神地照着整个屋子,屋子里开始都变得死气沉沉。袁树军去熬了一锅粥给大哥吃,但,袁树国的手已经不会握勺子了。袁树军一口口地喂,粥的流汁就一点一滴地从袁树国的嘴里流出来。喉咙里仍然发出那鬼哭狼嚎般的“嗷嗷……”声。
袁树军再也喂不下去了,他走到墙壁的一边,抬头看到墙上贴着一张大哥抄的诗歌:
山外青山楼外楼,
西湖歌舞几时休。
暖风熏得游人醉,
只把杭州当汴州。
袁树军把它揭下来,折好了放在口袋里。他知道这是宋代诗人林升的诗,这首诗是作者怀着满腔的愤慨,谴责南宋统治者偏安江南一隅,苟且**的腐朽生活。袁树军想,大哥可能在某个时期抄录下来以发泄其对当时恶势力的愤懑。他回头看了看眼前神情呆滞的大哥,轻叹了一口气,摇摇头,感叹此人已是今非昔比、困窘不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