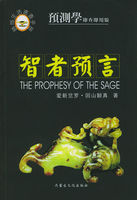那棵树旁逸斜出的枝叶刚好遮蔽住落雁的身体,身后一条小路,若被发现,也来得及退下。她听的真切的,也只是两段话而已。
“妹妹现今在府里,每日里吃穿用度消耗着,我们哥几个每日里东奔西跑,累死累活的,她倒清闲,也不会帮衬帮衬。眼瞅着这年纪也不小了,为什么父亲还不为她物色好人家?妹妹模样自不必说,配着寻常人家,没的被浪费了。我看定远侯不错,光大宅子京城里就有3座,人物也好,加上侯爷的妹妹又是当今皇上的爱妃,攀上这门子皇亲,料想以后我们锦绣坊的销路不再会碰到多少阻碍。不知父亲意下如何?”
--------心突然一沉,像灌满铅一样沉入海底。
“我儿话虽不错,只是,为父早知,这个定远侯已过古稀之年,更兼有3房姨太太,雁儿还是年轻轻的大家闺秀,嫁过去,就不得不做小四,成日里被几个大的使唤来使唤去,让雁儿受这样的委屈,说实话,为父想着,心里实在不好受。再者,若你赵姨娘知道了,岂不要怪为父的心太狠。这事儿还是日后再说吧。”
嫁给定远侯?没错,那个胡须花白的老头子。怎么办?谁可以救救我?我该怎么办?落雁一只手扶住树干,支撑着身体。心脏里像压了一块石头,费力地跳动。大哥哥亲手铺好她将来的路,而她,连反抗的能力都没有。
发白打颤的嘴唇,远在天边的寒光,以及,骨肉分离的疼痛。
风越刮越猛烈,有落叶在晚风中簌簌坠落,落雁的双手已经冰冷僵硬,而她,还在树后面站着,头发被迂回的风吹乱。
黄昏,夕阳,断肠人在天涯。
如果不是这场偶遇,只怕到死都还会存有嫁给自己所爱人的幻想。现在,幻想逃不过现实,什么都破灭了。她感到非常非常的无助。
无人安慰,也无人关心。她流泪了,却无可奈何。
沈景元已经走了,而该来的,不用人请,迟早还是会来的,躲也躲不掉。可,那份寿礼,还要捧到父亲面前吗?曾抱她去逛集市的父亲。
其实,在她还是小女孩的时候,那时,锦绣坊也只是个小绣坊。经营范围略显单调。父亲也还年轻。非常非常地疼爱她。常从母亲手里接过她,带她到市面上去买糖葫芦。于是,她看到了憨态可掬的泥娃娃,白嫩嫩的水萝卜,热气腾腾的桂花糕。父女之间的感情,就像皮肤下温热的血液,总是源源不断。
有时,她的脑海里会一直浮现出一个模糊的影像,再凑近一点看,是二哥哥继元的面孔,小时候,她在沈府里没有亲近的伙伴,二哥哥继元只比大哥哥小三岁,却比他更有主意。只是他一直是淘气好动的样子,如同一匹四处撒欢的野马。
这些朝夕相处的亲人,却与她相隔甚远。他们是蒙老天爷眷顾的幸运儿,而她,只是一个姨娘的孩子,还是女的。彼此间就像横着一条长长的大河。
偶尔,他们会给她一些糖炒栗子,逗着她笑,落雁想,不知道她在他们心目中是怎样的印象。在她儿时的记忆里,他们只留下一张若隐若现的笑脸,而她只觉得,那笑脸好像被清水漂洗过的素描,用手指一抹,什么都没了。
记忆如此之萧索,那些飘飘忽忽的人与物,像近在咫尺的幻象,见得到,可不能触碰。
之后,大哥哥开始学着打点家中大小事务,二哥哥也变得渐渐不那么一味贪玩了,不时帮着管理往来账务。日子一成不变,平平淡淡。
当年的小小孩儿,一转眼,大成了俊朗少年,妙龄女子。父亲,也老了。
二哥哥爱在年末去山林里打猎。仗着身强体健,清晨出门,傍晚满载而归。猎物中常常有一只受伤的兔子。府里丫头、婆子围了一大圈,大家检点猎物,欢天喜地。大概因为她与它都是弱者,抗不过命运的。所以,她愿意保护它,也唯有她,有心保护它。她悄悄抱起受伤的兔子走向柴房,谁都没注意她。她就像一个轻灵飘逸的影子,人前晃一晃,就不见了。
之后,大哥哥满十八岁了,府里热热闹闹地大办婚宴,娶的是隔壁绸缎庄的大小姐梨落。
梨落属于典型的深闺女子,自她嫁入府中后,大哥哥沈景元的心里、眼里,满满的装的全部都是她。
人情淡漠,纵然有血亲关系,心里各自仍打着自己的小算盘,物质利益面前,亲人往往成了对手,甚至敌人。人心不如水,从呀呀学语到长大懂事,落雁渐渐体会到这五个字的深长意味,人情之冷暖,只有凉水方可比拟一二吧。她本就没有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疼爱以及怜悯,她就是这样外柔内刚的倔脾气。只有她,才能始终保持着一份淡然,要换作别个,怕要终日愤愤不平了。
百年老字号,江南锦绣坊,身在这里,时光凝滞,朱门紧闭,落花卷繁华。
落雁在这里长成少女,这里的一草一木,就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她的呼吸,息息相通地与它们联系在了一起,她曾试图割断这层关联,却发现,无论到哪里,呼出的,全都是它们的气息。
若是要推出沈府里最开明、公平的人,落雁认为,不必说,沈母是毋庸置疑的。然而,府里的人大多势利眼,地位尊卑,皆是衡量人的标准。然沈母对她很疼惜,过去,碰到下人曾给她脸色看,都是沈母替她出头。还对赵姨娘说:“雁儿既是老爷的孩子,那就是沈家的人。我也不许府里人小瞧她。平日里不要舍不得花钱,每年添置新衣裳只论质地好,样式得当就得了。若是月钱不够了,直接跟我说,再不许给孩子穿旧衣服,寒碜了我沈家人。”
落雁当时就坐在母亲身边,还只七、八岁,太嫩,想到每年都有新衣服穿,很高兴。
她就这样在沈母的庇护下过了一年又一年。
在沈府众人眼里,生母赵氏只是一个从良的歌妓,嫁入沈府,得个姨娘的名分,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地位。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歌妓都有这么好的运气,有嫁入贵府的命。当初,沈老爷为感情不惜忤逆父亲迎娶赵氏,赵氏为肚里的孩子洗尽铅华抛弃荣华,一时间,街头巷尾,传为美谈。也许,每个人的命,是在娘胎里就注定好的了,生出来该是谁,当主子,或者是奴才,还是沦落风尘,这些,不容你挑三拣四,也无法抗拒。
歌妓,卖艺,这两个词也可以是年轻美貌的代名词。女人最宝贵的年龄,却要葬送在那个夜夜笙歌不断的风月场。
不是恋风尘,似被前缘误。脂粉掩不住,疲惫的凄凉。
名分,在落雁看来,不过是一张华丽空无的标签。她看重的,是母亲与父亲两个人真心相爱。其余的,好像都无关紧要。可,过去,让母亲赵氏像一个可有可无的人一样生活在府里,三姨娘陈氏倒是出生清白,可是入府多年,连半个孩子都没给沈老爷生下,还常挤兑落雁母女俩,发起脾气来只怕连悍妇都过犹不及,落雁从来对她敬而远之。
所以,落雁眼瞧着,家庭温暖还不如寄居在府内屋檐下的燕子,一窝几口子,还能团结一心,反倒其乐融融,对它们而言,没什么勾心斗角,即使食物短少,也是一群小的围着你一口,我一口地吃。或许,所谓的亲情,就像点在窗台上的烛火,摇摆不定,风吹一吹,就悄无声息地灭了。
听说,母亲自生下她以后,便终日吃斋念佛,不问世事。她好奇母亲的过去,有向沈母问过,那一次,沈母轻描淡写地说,都是过去的事,不提也罢。
她有一个,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