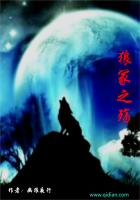梧桐树叶沙沙地作响,树下的青石台阶变得光影斑驳,晌午时分,人迹罕见,四下寂静无声。庭院深深深几许。眼见得主子们大多正在睡中觉,两个随侍小厮好容易偷得半晌闲暇时光,蹲坐在左厢房门口,已经禁不住困意,耷拉下脑袋,打起瞌睡来。偌大一个后院,花木扶疏,蜂蝶飞舞,好不热闹。
沈景元早列出暗地要送给陈公公的礼单,吩咐满福儿尽快呈给宋总管定夺。满福儿接过礼单,不敢怠慢,一径往左厢房赶去。
满福儿是沈景元手下最受宠的小厮,如今手头接着如此重要的任务,自然希望立马完结,好回去向沈景元复命。左厢房守门的小厮睡得人事不省,哪里知道来人了。满福儿停在房门口,犯了难:“打扰宋总管的清梦,想来他不会乐意,可,眼下这事儿,爷那边又偏生催得急迫,”下定了决心,抬起手。
正待要敲门,厢房里传出男女调笑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右手顺着门迟疑地滑下来。男的正是宋总管。
只听宋总管不无得意地说:“老头子给了一万两银子做今年选御绣的活动开销,我琢磨着只拨出部分给沈景元那小子,剩下的,就留给咱们两个潇洒快活啦!”
女的声音娇媚:“不好吧?要是被发现了,你这沈府大总管的头衔还要不要呀?”
宋总管胸有成竹地说:“放心吧!若有人问起,就推说是用钱买通见陈公公的关节了。宝贝儿,来,亲一个!”
女的纤纤玉指一戳:“你真坏!”
满福儿一个寒颤,不由“啊呀!”地叫出声。声音虽说不大,可也足够惊动厢房内的那对男女。惊醒两个睡觉的小厮。很快,他们停止了相互调笑。宋总管推开门,不等守门的小厮说话,一人扇了一个耳光:“我叫你们偷懒!”
两个小厮捂着半边脸,吓得跪在地上,捣蒜也似地磕头:“小的该死!小的该死!求爷爷饶命!”宋总管看两人皆是平日里自己手下伶俐的人,此刻额头青紫一块,脸色煞白,倒也十分可怜,沉下气,摸了摸胡子,说道:“既然这样了,就都起来吧!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来,再给爷守着,再偷懒,改明儿打断你们的腿!”小厮们唯唯喏喏。
趁着满福儿还没有回过神来,宋总管揪着他的衣领子,像拎小鸡一样把他拎进西厢房。“砰”地甩****。满福儿舌头结成一团,吐不出完整的话:“这,这个,宋,宋总管,我,那个,”宋总管拍拍满福儿的肩膀:“什么这这那那的,小兄弟呀,我一看就知道你是自己人,有话好说,别紧张嘛!”接着,又回头对那个妖艳女子说:“你先回去。记得从后门走。”那女子点点头,扭着细腰退去。
满福儿毕竟是做下人的,哪禁得住宋总管这番热乎乎的客套话儿,当下壮着胆子,指天指地地保证:“爷放心,小的今天什么都没看到,什么都没听到!”宋总管满意地笑了,走到穿头柜前,拉开抽屉,取出五十两银子:“拿着,爷赏给你的。”
满福儿又惊又喜,刚才的恐惧早丢到九霄云外去了,瞪大眼,推开银子,道:“谢谢爷!爷折杀奴才了。小的消受不起。”宋总管是沈府一等一管事的,沈老爷跟前的大红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沈府无人不知。眼下被撞破丑事,没对自己不利,已是万幸,怎好再收他的银子?
宋总管大方:“爷给你你就拿着,日后自有用到你的地方。”
满福儿顺从地俯下身子磕头:“谢谢爷打赏。”遂留下礼单,点头哈腰地走了。
宋总管知晓了他的心意,看着礼单,心里头盘算着:“今天真真晦气,撞上这么个冤大头。不过,这也未尝不是件好事。”
两个守门的小厮眼巴巴看着满福儿满面春风地远去,推开门,走到宋总管身边:“爷,您老就这样放那个小子走啦?您老就不担心,”
宋总管瞪了他们一眼:“你们懂个屁!这小子是个软骨头,更何况又收了我的银子,拿人手短,他会把这档子事儿烂在肚子里!”
两个小厮赶着附和:“还是爷算得精准!”
宋总管点了一支烟,说得感慨万千:“你们两个小猢狲,到底小孩子脾气,哪里看得透这复杂恼人的旁支关系。爷十八岁就跟着沈老爷子,好歹也在府里呆了几十个年头,走的桥比你们走的路还多。为人行事尚且小心谨慎,唯恐有半点马虎,捅出什么大篓子来。主人家的性子,大胆说一句,就是鸡蛋里边也给挑出刺来。你们家人可就指望你们每月那点子月钱了,你们若是像今天这样办事,他们靠谁吃饭去?”
一席语重心长的训教说到两个小厮心窝里去了,他们拍着胸腹说:“谢谢爷,爷教训得是,小的们记下了,以后,但凡爷交代下来的事,小的就是累死了,也绝不再有半点马虎。爷,时候不早了,该去大公子那回话了。”
两个小厮一提醒,宋总管方才想起还有礼单要过目。他拨了拨灯芯,在灯下聚精会神地审看起来,两个小厮一旁忙倒水陪侍。“看不出来,沈家这次可是下老本了。够大方的呀。”他一边叠起礼单,一边往门外走。经过清水桥,不巧正看见一群人从假山那边走过,领头的是府里陪房慕容家的。后面跟着一群姑娘。看不清头脸。
宋总管寻思片刻,对小厮们说:“走,一道上去看看。”两个小厮巴不得好好表现一下,将功折罪,紧随着宋总管,快步往假山方向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