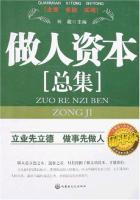在我那美丽的家乡,我的父亲母亲并不是很幸运,穷了一生,累了一生,苦了一生。劳作、自信、坚强地走到人生的终点。生前没有让我看到脸上有多少幸福的笑容和快乐。而闭上眼睛后,面容又是那么的慈祥和安逸。想到这,我无比的悲痛,我对他们有太多的亏欠,我真舍不得他们就这样的离去。虽然他们遭遇的不是天灾,也不是子女们不孝,而是人制。但是我们也没有给父母带来多少幸福。
我父亲(杨道吉)出生在公元1924年农历7月。那时代,中国山河破碎,人民饥寒交迫。他8岁时,我的奶奶吸鸦片自尽,他痛失娘。他11岁时,我的爷爷病故,他又痛失爹。从此,他和一个妹妹、一个弟弟成了孤儿。当时,邻里族亲也很苦,只能照顾很小的弟弟,妹妹送出去当了童养媳,而他只有出去当童工。他是被一个叔伯族人带到15公里外的溪口镇上,找到一个开中药铺的店家,当了童工。从这时起,这家药铺的切药、磨药、晒药、抓药活儿,就是他每天必干的工种。哪里稍有疏漏或失误,就会招致店主的打骂。这时候的父亲是一个懂事聪明的孩子,一边老实干活,一边学着读字写字、打算盘和制药技术,不到两年就成了一个很好的药剂员了。博得店主的喜欢,这就有了一个稳定的安身之处。并一直干到成年。成年后的他,也想出去闯一闯,于是就跟了一个地方民团,挑夫、打杂十来天,感到这里并不是他呆的地方,还是回到那个药铺干起了他的老本行。
我母亲(张竹莲)出生在公元1927年农历3月。她出生的家境比父亲出生的家境要好的多,她的爷爷(我的外祖公)是当地一个大户人家,有几十亩田土和两栋四合院的木板房。但她出生后的好境并不长,我外公仗着好的家底,好赌成性,把祖外公分给他的田土几乎输得尽光。母亲只有十多岁时,外公又被国民党抓去当了壮丁,结果一去不复返,查无音寻。我外婆是小脚女人,只能干一些家务活儿。我母亲是长女,她下面的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年龄都很小,最小的妹妹还是一个婴儿。于是这个家庭的农活儿,就几乎落在了我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因此她从娃娃开始就整天高强度地劳作是可想而知的。
我父亲母亲成婚是娃娃亲,他俩先后一出生,双方父母就结成了亲家。我母亲稍一懂事就不同意自己的婚事,但没用。当初就说好了的,哪能反悔?于是,公元1948年,我的父亲母亲走进了婚姻。因此,他俩婚后的生活并不是很幸福。他俩结婚后,父亲还是在那个药铺当药剂员,母亲在家里干农活。公元1949年,新中国诞生。社会制度由资本主义变为社会主义。这一年我大哥出生,又两年我二哥出生。当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行公私合营和土地改革,父亲成了集体药店的药剂员,母亲成了公社社员。但这些改变并没有改变父亲母亲的穷苦和劳累。随着我们兄弟姊妹的增多,反而更加重了他俩的拖累。父亲母亲养育子女八个:大哥、二哥、姐姐、我、大妹、弟弟、二妹、幺妹。到我大妹出生后,家务、农活靠我母亲一个人是怎么也顾不过来的,于是父亲离开药铺回到了家里。家里虽然多了一个人参加集体劳动,但父母因孩子多还是摆脱不了贫困。大妹就是在一岁左右,因身体严重营养不良造成脱水、走“猴胎”而不幸夭折。后来我再下面的弟妹出生,随着两个哥哥的长大,生活状况才好一些。但不管怎么说,七个子女养育成人,这其中的沉重和艰难,让我无法想象。
当哥哥、姐姐和我的逐一长大成家,父母应该会轻松很多,但天有不测风云。大哥成家不到四年,就患了不治之病---肝癌,年仅27岁离开人世。父亲母亲从此丧失长子的伤心痛苦难以言表。大哥留下两个孩子,小的随嫂子改嫁带走,大的由我父亲母亲护养。大哥离去12年之后,二哥又患了同样的病,父亲和我一起陪送他到省城医院治疗,而医生的药方只能缓解他的病程,却挽救不了他的生命。年仅38岁的二哥又离开人世。我的父亲母亲再次遭受丧子的打击。二哥同样留下两个孩子,小的随二嫂改嫁带走,大的又由我父亲母亲护养。磨难、痛苦、劳累、养育,就这样伴随着我父亲母亲的一生。当两位老人刚好把两个孙子(女)护养成人,他们应该安度晚年时,却已经心理憔悴,心力耗尽。没有生命的时间来感受幸福的一刻。
1998年初冬,父亲病故,享年74岁。2002年夏天,母亲病故,享年75岁。两位老人即使病去,也是很匆忙突然,虽怕拖累儿女们,也生怕多花儿女们的一分钱。他俩的离去,给我留下太多太多的痛楚,留下太多太多的遗憾···
父亲耿直正义,诚实认真,教子威严,生活俭朴。母亲勤劳善良,节俭持家,敢做敢为,倔强坚定。敬爱的父亲母亲啊,您的离去,成了我永远的怀念和追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