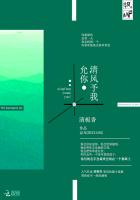过了一会,大夫人身边的淳欢来传,说是大夫人请了宫中王太医来给渠芙请安胎脉,渠芙一听这消息,心道,来了!按理说一个贵妾有喜犯不着请宫中御医来诊,只是这一胎对子嗣单薄的邵家来说尤为珍贵,更何况只是邵玦和渠芙口头所说,算不得准,邵玦不是大夫人亲子,大夫人既怕这个继子以后强大了给自己难堪,又想让他变得强大与二房争一争候位继承权,而且二房邵钰无子,所以希望邵玦先有一子,这样族里就会因侯位稳定而重新考虑候位的继承。所以,大夫人心里是尤为矛盾的,因此更加关注这个孩子的降生。
渠芙心里暗叹,这一仗,真是难打呀,究竟要装到什么程度,才能不被大夫人发现呢?
渠芙坐在自己的床上,大夫人说是为了安胎,特别恩准渠芙就在安芜居里等着,不用移步去主厅,她听见外面哄哄嚷嚷一群人的脚步声,像是大夫人和太医过来了,便吩咐清弦出去迎候,这小丫头急得不行,她担心自家小姐被休离邵家,又失去这个依靠,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渠芙安慰她道:“清弦,没什么的,大不了就回到那个空宅子里去了却余生,最多损失一个名声,而且我都与邵玦商量了,此事若是失败,我还能拿到一笔钱回去,毕竟此事是因他而起,”清弦睁着泪水朦胧的大眼睛不相信地看着她,渠芙又无奈了,既然哄不好就只能用吓的了,“快把你的眼泪咽回去,再这样在外人面前落了你家小姐的面子,看我怎么处罚你!”清弦这才抹干了眼泪,低着头去门口迎候了。
渠芙先是挑开床帐见了大夫人,自己仅仅是在新婚第二天有机会见过这所谓的婆婆,她是一个保养十分得当的夫人,三十多岁的女人仍像二十多岁的容貌,皮肤光滑没有一丝皱纹,只不过却躲不过岁月给她的气质上的烙印,眉宇间没有少女脸庞上该有的青春活力与飞扬的神采,有的反而像是日日为候府操劳所带来的疲态,不过,渠芙不信袭勇候的六个姨娘只有一个在外地产下两子,其他姨娘的不育中不知大夫人又有没有功劳。
大夫人握起了渠芙的手,面带慈祥地说了许多话儿,不知道的人看到这两人脸上的表情,定会以为这是哪家的慈母孝女。大夫人说话的内容在渠芙听来只有一个真实目的,就是打探在新婚那夜到底有没有与邵玦圆房,可是渠芙以女儿家害羞的神态绕了许多圈子,最终也没有回答她这个问题,渠芙虽是做好了事发被休离此生再难嫁出以及计划难以执行的最坏打算,但还是努力不让最坏的结果提前发生。
那王太医是为袭勇侯府诊了十几年脉的,自是没什么避讳,便在渠芙的腕上蒙了一张方巾,然后隔着帐子开始诊脉,诊完买后又问了渠芙和清弦几个问题,二人皆按照事先准备的答了。
王太医请了大夫人到外间说话,渠芙撩开帐子,二人说话的声音便清晰地传过来:“侯夫人,老臣诊了脉,这脉象并未显示九少夫人是怀了身子的,但听其主仆口述,症状倒是符合有孕之表征。”渠芙心里一沉,都怪邵玦,自己明明提到用药装一装脉象,但他说什么用药会被发现,根本瞒不了太医,这下可好了,真的被发现了,看来邵玦这人是摆明了想要休离自己了,当初就不应该相信他。
当下渠芙也管不了什么礼制了,直接下了床提上鞋,换了一副悲戚的样子来到外间,把大夫人请到里间来,大夫人此时脸上已满是怀疑之色,渠芙压低了声音强忍悲痛道:“母亲莫要相信一次诊断的结果,妾身真真是怀了身子的呀,这么大的事,妾身怎么可能欺骗您呢?妾身也知欺骗族人的后果,这若是误诊耽误了,妾身怎么对得起邵家的列祖列宗呢?”大夫人不知是不是认定了渠芙是在欺骗她,依旧没有说话,渠芙便继续说道:“烦请母亲再请一位太医来二诊,若能证明妾身清白,妾身将感激不尽!”说完便立即倒地而拜。大夫人略略想了一下便点头同意了,她叫人送了王太医出去,渠芙在里间又听到一人和缓低沉的声音:“儿子给母亲请安。”是邵玦!渠芙此时听到这声音,终于长舒了一口气,感觉整个人都松懈下来,还好,只要他来了,就算没背弃承诺,整件事情,就算有救。
“如若母亲要请人再诊,那不如就多请几个医生来,不仅仅是太医,还有郢阳名医,这样也可保证万无一失,母亲觉得如何?”邵玦问道。
“不行,”渠芙听见大夫人坚决的声音,“家丑不可外扬,这事若真是像王太医所诊的一样,岂不是叫人看笑话吗?”
“那母亲是想请谁来?”邵玦继续试探。
大夫人回答道:“城东医馆许千城许大夫给我们邵家看过病,他为人最是刚正不阿,定会据实禀报;太医院郑太医给你祖母诊过病,也很让人信得过,且看这二人如何说。”
两个人很快就到了,渠芙想,看来这袭勇候在朝中还是有些威望的,要请个太医说请就能请得来。
那二人分别给渠芙诊了脉,这回倒是顺利,结果一致,均认为渠芙的脉是有孕之相,大夫人的眉头终于不再皱了,正当渠芙为自己通过了考验而内心雀跃之时,却听大夫人一扬眉道:“不过,王太医毕竟诊了十几年的脉了,他那么说,毕竟是有缘由的,对这个,两位怎么说?”
渠芙感觉自己的心跳又开始加速了,想到自己被休的可能,也就意味着自己为了加入侯府所做的那些努力即将灰飞烟灭,又是一阵心酸。
那个姓郑的太医说话了:“侯夫人您不必担忧,就是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