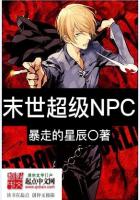我有点惊讶,我爸自从越战后就从部队退役,虽然和以前的一些老战友、老部下还有一些联系,但毕竟不动刀动枪很多年了,对于战场的感觉应该衰退了才是,而在这事上面,他仅仅凭当时我在病床上给他的描述,就有了和我亲身经历后发现的类似感觉,我不得不佩服他。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道。
我爸叹了口气,说,“我也只是感觉而已,你们那个小组的人我也见过几个,特别是小天和小龙,以他们的身手和脑子,居然都折在那里,很难让我没有这种感觉,其他的我也说不上来了。过两天去你干爸那,他应该会告诉你一些事情。“
我点点头,没再说话,顺手把正趴在沙发上的狗狗拖过来一顿的揉搓,弄得狗狗的眼神都有些哀怨,乘我不注意跑回窝里怎么喊都不出来,直到我妈抱它出去散步才朝我皱了皱鼻子,一溜烟跑了出去。等他们出去,我洗了个澡上床躺着看电影。
第二天早上,我早早就醒了,看爸妈还在睡,一个人溜达出去吃早饭。南充的特色早餐是米粉,虽然在外边多年,各地的早餐吃得也不少,但最怀念的还是南充米粉,纤细的米粉在熬制多年的老汤中烫得软糯,就着老汤捞进碗,配上一瓢炖得烂熟的牛肉或鳝鱼,那味道不摆了。如果再加一个油干,诚满汉全席不换也。
正吃着,我妈电话来了,让我带两碗米粉回去,我奇怪她怎么知道我在吃米粉,我妈说我每次回来早上必吃米粉,根本不用猜。
提着外卖的米粉、油干溜达到家,我爸刚带狗狗撒尿回来,一进门就说,“呆会儿回老家,你小叔已经接你爷爷去祠堂了,刚打电话叫我们早点回去。”
“我……这是准备三堂会审么?”我极其郁闷,不就是一年多没回家么,怎么还要去祠堂。
我爸呵呵一笑,抱着狗狗去洗衣台洗脚,“你也知道怕?今天是什么日子知道不?”
“知道啊,今天星期天嘛。”我把米粉往桌上一放,进厨房拿来两双筷子,随口说道。
我爸还抱着狗,顺手抓起洗衣台边的狗毛刷就扔了过来,“你个龟儿子!今天是你曾祖父的忌日!老子昨天接你前已经在老家忙活一天了。”
我伸手把刷子接住,看着上面密密麻麻的狗毛,“我说爸啊,幸好您现在不是在切菜啊,我到底是不是亲生的啊。”
看着我爸正准备发作,我急忙转移话题,“开我车去吧,老家路烂。”
“现在路修好了,村村通柏油路。”我爸把狗狗放到地上,端起碗吃粉。
“还是开我车去吧,我显摆一下。”我蹲在地上逗狗。
我爸拿着一块油干嚼着说随便,然后又说不是我自己买的车,显摆个屁。
回老家的路果然如老爸所说,一水儿的柏油路,开起来异常舒心。我们老家在一个叫做搬罾的乡里,离市区不过20多公里,但以前路不好,轿车基本上不可能开到乡里,小时候回家要不是我爸开着212吉普晃晃悠悠的摇上1、2个小时,要不就是到邻镇的码头上坐渡船横渡嘉陵江。而现在路通了,半个小时不到就到了祖屋的祠堂。
老家现在的模样变化很大,到处是新农村建设新修的房子,一溜的联排别墅,有农民自家修的,也有因为这里离市区近,城里人过来买地修的,反正又不贵,30来万就可以修一套,比在城里花30来万买个6、70个平方呼吸汽车废气强得多。
下了车,几个亲戚给我爸打招呼,看上去熟络得很,我爸给我介绍,什么远大爷、四姑、七堂叔等等等等,说我小时候都见过,我却一个都不认识,只能一一招呼,一圈下来,脸都笑僵了。
进了堂屋,我爷爷正在和几个老辈子抽旱烟聊天,有说有笑的,心情貌似不错。我正心想这一劫应该是免了吧,爷爷一扭头发现我进来,脸一下拉得跟马似的,“你小子舍得回来了?过来。”我只好腆着脸走到爷爷跟前站军姿。
在老家,我家这一脉从曾祖父那一辈起就是长房,虽然一百多年传下来,辈分低得要命,但一直都是族里主事的一房,因此在家族里,我爷爷有着很高的威严。哪怕平时我可以揪他的胡子玩,这个时候是一定不敢造次的,不然要是把他老人家气出个好歹来,这个玩笑就开大了。
虽然气势汹汹,但我爷爷还是疼我的,呵斥了两句后又开始问我的近况。我一看没事儿了,就拖了竹凳坐下,给老辈子们散烟,把一年多来遇到的稀奇事添油加醋地吹给他们听。几个老头都是几乎一辈子都没离开过乡里的人,最远的地方无非就是去过市里,年纪大了更是无聊,所以我海阔天空的瞎侃,他们也乐呵呵的听。
午饭是在三叔公家摆的,因为我们家在老家已经没有人了,曾祖父的一儿一女解放后都在城里工作,下面的儿女也都在城里定居,所以老家的田地、房产都转给了亲戚。三叔公的父亲和曾祖父是亲兄弟,家里两个儿子都在外地做生意,家庭条件比较宽裕,所以房子也大,容得下一大家子人吃饭。
等着吃饭的时候,我无聊的在三叔公的四合院里到处晃悠,突然听到二叔从三楼的窗户里叫我,让我上去看个东西。二叔在我们家是个头脑极聪明,而且胆大包天的人物,年轻的时候闯了不少祸,有些事如果不是我爸四处奔走,估计到现在还在里边吃皇粮,他让我去看的一定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我嘀咕着,在这个一百多年才出了我曾祖父这么个秀才的穷乡僻壤里会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让二叔有兴趣。上了楼,二叔正在一间储藏室似的阁楼里背着手看着什么,见我到了,指着墙角的一幅字问我,“夜娃子,你读过大学,这几个字你认识不?”
我顺着二叔的手看过去,墙角靠着一幅装裱过的字,纸张已经泛黄,估计有些年头了,上面的字我一个都不认识,我觉得奇怪,就问二叔:“这谁写的?怎么一个字我都不认识。”
“不知道,我也不认识,没见过这种字,是不是上面甲骨文啊?”二叔晃着脑袋说。
听到二叔说甲骨文三个字,我突然觉得这种字好像在哪见过,但一时又想不起。正想着,楼下叫开饭了,二叔顿时失去了研究字的兴趣,拖着我下楼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有点心不在焉,人在觉得一个东西很熟悉但又始终想不起的时候是最难受的,说得严重点就像猫挠似的。正想着,白马打来电话,说是我们在洞里发现的那几个字已经送给古文字学家研究,但没人认识,目前只能大致确定是属于战国时期某小国使用的文字,让我安安心心的多玩几天。和白马闲聊了几句,我挂掉电话继续吃饭,忽然一个念头一闪而过,楼上那幅字跟洞里的字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