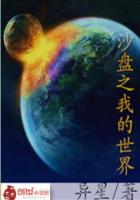清晨的太阳笑容可掬,把它妩媚的光华撩过窗帘的缝隙,在叶子的被子上轻灵地跳跃。静谧笼罩着整间房,即使延长到凌晨三点的呻吟也暂时停了下来。她的眼神跟着那道阳光在被子上渐行渐远,直到无法再追踪下去。
柳晔醒着,更准确的说,是根本没睡过。对于她来说,睡和醒又有多大的分别呢?睡是魂灵的茫然,醒是茫然的魂灵,她连思维的能力都失去了。除了生理上的痛苦逼使她不得不调动所有的精力来对抗来忍耐,她几乎已经做到了无知无觉。昨天的整个下午,她象贵宾一样躺在床上被簇拥着推来推去,进行一项又一项的检查和诊断。记忆已经被她自己强行撕碎,零乱,颠倒,闪烁,终于再也拼凑不起来。她忘了曾掐紫了自己腿,忘了泪水曾经狂奔;她忘了心是怎样颤栗疼痛,忘了那种被**似的羞耻;她还忘了那些器具的生硬恐怖,忘了有一只手在“探测”她的病灶,却把她的世界象敲碎一面挡风玻璃一样轻易击碎,只留下了一地的渣滓和些微的血迹。。。。。。她恨自己为什么没有象上一次一样湮灭在黑暗里,她更恨自己做不到把自己当做一具尸体,她尤其切齿痛恨的是没有提早把自己掏空,而让她的灵魂面对凌迟,接受苟且偷生的羞辱。一切不啻于被腰斩!亲眼看着自己变为两断的身体,还在拼命蠕动,拼命在互相召唤,她的心就碎成了飞灰。
她听不到大夫对老妈有关妇科检查为什么迟迟没做的疑问,她看不到她们如释重负似的微笑,对于她们来说她的生命可以继续了,而对于她来说,她的生命已然结束了!生活从来就不是“童话”,没有一则童话不是骗人的,不是虚构的。灰姑娘永远是蜷缩在灰烬里,白雪公主不会死而复生,他也不可能是她的王子!歌里不就是这么唱的吗?梦想无法成真的!
她听到大夫对她安慰地说“别紧张,情况还好”,她又听到她对老妈说“帮她换换衣服吧,都湿透了,这孩子身体太虚了”,她还听到老妈的叹息“咳,她个性太强,没有征求她的意见,我们不敢......”哀怨无措象汹涌的冷汗不肯放她片刻,难道我还不够顺从,不够体谅?难道您还没看到,为了抚平您的伤痕,我却已经遍体鳞伤了吗?心在哭泣,她却挤出一个空洞的微笑,然后逃了,逃进来的太迟的昏沉里去。
“从今以后,叶子死了,你们再也看不到她了!”心底的话掩藏在那个笑容之下,她睡了。
可惜的是,这种逃避被呻吟声唤醒了。柳晔睁开眼睛,首先看到了老妈的脸,心底忽然象被针刺了一下。
“小晔,醒了?想吃点什么?”老妈柔声问着,从来没有这么温存过。酸楚忽然滑过,她莫名地想哭。尘封的记忆里,曾经有过这样的温暖,但是它被自己忘记快二十年了!曾几何时,还有过近似的感觉呢?她摇了摇头,好累啊。
“你们这姑娘也是这病啊?”附近的病人忽然问,老妈警觉得回过头。
“啊?啊,不是吧?应该不一样吧?”她还在试图瞒着她,难道老妈不知道,我都明白了吗?叶子好疲倦,她无力地看向隔壁。
“阿姨很难受吗?”第一次这样主动和人交流吗?老妈忽然带了惊喜的眼神看着她。不,老妈,您不用这样看我,这不是我第一次和人打招呼。第一次,是在列车上,是寒松建议她和中铺的一位女乘客交流,大概是想让她有所照应吧?可惜,她已经今非昔比了。
“咳,就是啊。还不如早点儿死了呢!”隔壁的阿姨恰恰说的是叶子想说的话。
“又胡说!你看你这是干什么?当着人小姑娘的面?”那位大叔嗔怪着,老妈也露出了极不自然的神色。
房门在这时忽然被推开了,又有病人来了。只是是哪一个呢?进来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中年妇女和看起来象她爱人的男子,另外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
粉色制服的护士又跟了进来,“卓荷雅,是你吗?”她亲昵的用手摸了摸那个小姑娘的脸,“快上去,30床。”
一刹那间的惊骇使叶子难以保持镇定,怎么可能真有这么小的癌症患者?太残忍了!她的父母该有多心痛啊?好不容易拉扯了这么大!看着那为人父母的把孩子扶上床后,就开始整理忙碌,叶子忽然有了一种想保护那个小女孩的冲动。
“你叫什么名字啊?”柳晔尽量想用她最好听的声音说话。
“我叫卓荷雅,荷花的荷,文雅的雅。”小姑娘有些怯生,但还是大方的回答着,带着一口京片子,显然是本地人。
“我叫柳晔,叫我姐姐好吗?”叶子不知道自己怎么会一下变得这么爱说话了。郭素玉也从床边站了起来,热情地帮着那两夫妇整理着。护士插好卡片走了出去,看样子,这间病房的人又满了。小姑娘有些腼腆地看着叶子,忽然笑了起来:
“姐姐,你长得真好看!怎么叫柳叶呢?就是柳树的叶子吗?”
“呵呵,”柳晔又不禁脸红了,小姑娘真诚的赞美让她心里泛起一阵暖意。“姐姐不好看,你才好看呢。”
“不,姐姐好看!姐姐的眼睛又大又亮,还是双眼皮呢!我的眼睛太小了......”小姑娘的声音忽然就变小了,显然对自己很没信心似的,大人们有些失笑地看着她们。
“不是啊,你的眼睛很有特点那?而且你的皮肤也很不错,你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呢!”柳晔从心底赞美着。小姑娘一下显得高兴起来,扒在妈妈耳边说了一句什么。中年妇女笑着转过头来,
“欢欢问你,能不能去你床上?你看,这孩子挺喜欢你的,你们隔这么远说话也挺不方便的呺?嗯......你不会介意吧?”
“不会不会,怎么会呢?我家小晔也很喜欢小孩子的。”郭素玉急忙接过话来,她是很乐意女儿有这种表现的,何况叶子也在笑着表示同意。几个大人把欢欢移到了柳晔床上,让她们对面坐着,合盖一床被子。叶子忽然觉得她就象自己的小妹妹一样,疼爱和怜惜充塞在心底。她真的不明白,为什么连这样的小女孩也要忍受命运的搬弄?上帝何其不公啊!
“姐姐,什么叫有特点呢?”
“嗯?特点就是与众不同,非常特别。”柳晔不由伸出手去摸摸她的头发,黑亮顺滑的象一匹软锻,短短的赫本头。
“那是好还是不好啊?”
“当然是好的了!”柳晔笑了,“你多大了?”
“十二岁,就要上初中了!我老妈说,做完手术我就好了,就可以回去上学了!姐姐,你上大学了吧?”
“嗯,姐姐就要毕业了!”
“哇!好羡慕啊!什么时候我才能上大学呢?还得好几年呢!”叶子心里忽然一疼,鼻子酸酸的,她急忙转移话题。
“怎么会呢?很快的,只要你好好学习就行。你的小名是叫欢欢啊?”
“嗯。姐姐你呢?”
“我啊?我叫叶子,就是树叶子啊!”
“哇,姐姐你的小名好有特点啊!”欢欢偏着头,很俏皮的说。
“是啊。”叶子忍不住去捏捏她的下巴,笑了起来。
那一边,几个大人也笑了起来。欢欢的妈妈偷偷用手擦拭着眼角,老妈轻轻拍了拍她,她们互相凝视着。柳晔知道,她们和她俩一样,是同病相怜。
不一会儿,医生走了进来,指挥着几个护士把欢欢推了出去。柳晔心里有些明白,她不知道对于欢欢来说,那意味着什么?又是怎样的一种惨痛?会给她刚刚解事的稚嫩心灵造成多大的创伤?两个多小时过去了,大家已经开始吃晚饭,才看见她被推了回来。可怜的小女孩,沉默的出奇。柳晔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看着她苍白的小脸,她没有想到自己,只是为了欢欢在狠狠得痛,本来就已食不下咽的她颓然地放下了碗。郭素玉也漠不作声,大家都一言不发,屋子里静得压抑。
整晚,大家都在辗转,欢欢的爸爸回去了,第二天还要工作。不知道是因为古阿姨的呻吟,还是因为来到了陌生的环境,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床上翻动,除了叶子和李叔(古阿姨的老伴)。叶子不想动,她觉得自己已经是一副被掏空了的躯壳,无知无觉,无可无不可。李叔已是沉沉入梦了,也许照顾病人是一件足以使身心疲倦的事吧!后半夜,一切声响都停了下来,柳晔在与腹痛的较量中等来了黎明。现在,怕已经六点多了吧?也许,他已经看到了我的信,已经和迷迷谈过话了。也许他会心痛,也许他会以为受了欺骗,也许他会恨我?不管怎么说,至少这样一来,他会很快忘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