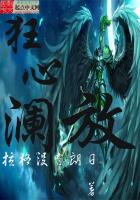碧海青天,斗转星移,随着各省的军管会进驻,革命委员会的全部成立;那些‘一切权力归红色造反者革命委员会’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理性之光”开始喷薄~~;许多新生活方式悄然走进人们的生活;不过人们还没来得及回头总结以致没察觉。就像东门村那样,就算外面的口号喊得震天响,社员们依旧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完生产队又忙自留地。没有闲人,也没有闲工夫去参加一系列的社会活动,但最新指示发表除外。每当有最新指示,个子高的陈篮秋不用点卯,自动准时到附城公社报道做旗手——游行。这是公社书记暨定的。游行这活儿谁都愿意干,不花力气且得工分高,斯又但是这活儿名额有限,不是每个社员都能去。自军管会成立以来,于金清首长就把游行队伍按照阅兵似,以单位为主,编成方队,一个单为就一个方队。先集中在北门运动场,以这为始点环城一圈,这本是非常好的游行计划,一个方接一个方上街游行队伍有条不紊,就像条游龙似。可问题来了,由于小城的环城路也就是四五公里,第一次组织游行来人太多,以致龙头走完一圈(城内城外)回到始点,龙尾有一半人呆站在始点还没动。这样游行从效果说也好,从计划不周说也罢,都不甚理想,在加上一个最主要原因,帮农民头上街游行,甭说组织纪律怎样,人人十足赤脚大仙,那衣衫不说不蔽体,先整得条游龙像掉麟片似不美观。尤其是鞭炮一响,赤脚大仙们怕脚踩着带火焰的红炮纸,人人绕到街边的或骑楼底或走廊走,把个游龙咬的不是龙肚没了就是龙腰折了。不是说我们是农业大国吗,那天才来三个公社的社员,如附城、白沙、沈塘,已经乱的不得了,倘再加客路、南兴、龙门,那这个城池非塌不可。所以第二次就出规定:游行队伍,附城公社方队名额在一百五十人以内。而公社机关包括吹炊事员已占去七十人,余下八十就只能摊分,附城公社有一百多个自然村,这不是僧多粥少吗,所以名额到了大队就是这味了,先大队干部再到生产对干部再到社员同志。幸好这条村社员一心埋进耕作中,吃自己应得的那份。从来不计较这个工分奇高的活。高会计就是这村的典行,每当大队书记有意分他一个名额,他都让出去,他说:“犬子已占一个名额,我就算了吧。”
犬子还不是陈篮秋,这人依然是桃花依旧人依然,赤条条社员一个。有所不同的是,如今已有婚约,其约就是那个媒人岚姨带来那个艳红跟他定的。自定婚后,岚姨也曾来过两三次,从来不带什么特别口信,好像女方不那么急于结婚。这下可急坏了老爷子,一个不思娶,一个不急于嫁,老爷子除了反复唠叨别无他法。岚姨来也敢多问,只是单单几句,“艳红她家可好吗?”
岚姨胆怯,由其是这个老人,所以不敢轻易在他面前说什么,只作唯唯诺诺点头。这是高会计教她的,“你多点头。唯唯诺诺,我包老爷子满意你。”
难道说不满意,是岚姨有什么问题。这问题问的好。因为岚姨来了总爱留宿,对于一晚宿高家的做法老爷子最不能容忍。不能容忍哪来的满意,是不。然而问题得一分为二,岚姨对高家有贡献,有功,是功大于过那种,她超越了平凡平的走动,做出劳动的功劳。给高家带来个宝贝儿——元宝圪瘩,艳红娘子没过门就投钱二百块给高家翻新房子。公祖(天啊)啊。二百块呀,这个数,高爸说:“我要收多少捅尿来淋菜才有这个数啊!”所以高家一直在攒钱再攒钱。这下一个公祖,天上就掉下个大元宝给接牢了,这个陈文宾(高会计)也不客气,紧接着冬歇期,农田少活时,二话不说将旧茅屋掀了,再添五十块,新盖了三阶(三间)屋。现住的是明砖明瓦三阶屋,还特照艳红的吩咐,全装上了玻璃窗,打开就窗几明净、光线充足、简直和县人委宿舍一样。这就是岚姨功劳。不过老爷子总在岚姨走出家门口时,看着她那左摆右扭的丰八月十五絮叨:“娜是北来吔姣(尽知道来这发情),口信不曾带半句。这媒人也太好做了。”
每听到这声音高会计就会出言安慰:“婚都定了你还愁什么。顺艳红的意思,爱什么时摆桌(酒席)就什么时候摆。”
“哎呀,高会计,我这不是想快点抱上孙子嘛。”老爷子说:“现在我真后悔,要知道是这样,那晚我就叫秋儿锄了她。”
“你又怎么知道秋儿没锄呢。”
“你傻呀,要是锄了,这会还不现形?她还能呆在杨家公社?”
——这爷俩估计没少呼猪头和吵(抄)红烧,而每次都以高会计让步而完事~~。
这一天傍晚,晚霞在慢慢消退,搞田间管理的陈篮秋结束了一天辛劳,扛把锄头回家。他一进院门马上将锄头撂一边奔水缸去:“渴死我喇!”陈篮秋这时恨不得一个猛子扎水缸里。不过他没这么做,现在长大了,定婚了,很快就做大人了,得懂规矩讲卫生。于是见他推开水缸盖,抓住浮在水面的舀瓢把,迅速舀了一瓢端起,嘴巴不贴瓢沿直倒进口,瞬间,清澈的井水大部分落入口中,一小部分洒溅式落在衣领级胸襟,仿佛水会开花似。这种开花似喝法方那叫一个痛快。
爷爷就坐在厅阶(厅屋),见此情形,急忙站起从屋里走出来制止说:“诶诶,别喝生井水。厅阶(厅屋)暖壶有开水。”
管它生熟,陈篮秋已灌下半瓢,嘴角正溢着水沫,他就这么喷着沫说:“啊!痛快!爷爷,没事,井水甜,喝后回力快,诶?高爸呢?”
“还没见回,可能在队部搭工分(记工分)。”爷爷说:“粥已煲好,片(送)咸刺花(金丝咸鱼),肚子饿你就先吃,不用等,谁吃下肚是谁个(的)。”
“谢爷爷。”
“谢你个鬼头,”没想到一句客气话又惹爷爷吹须突眼:“婚定不想结,家里一个女人都没有,想做死我这把老骨头啊。古人讲三个和尚没水喝,你还要等到么时才娶艳红过门,我都看(择)三次日子给你了。”老爷子愈发来劲:“艳红有单位有粮出(发工资)又有容貌,又够高够大,还没入门就给二百元咱们翻新三阶(间)屋,”爷爷用手拍墙说:“呐!这砖墙是艳红的钱砌起的,”完俩又用脚跺地板:“呐!还有这红毛泥(水泥)地板,和屋顶的瓦片是和院子的三面墙,都是用艳红的钱,你也可以放眼全村,除大队书记住的那间屋是瓦屋,刀下(剩下)就是我们这家了,你这个契弟仔(你这个家伙)命好摊上艳红你还不知足。”到这,爷爷突然想到那晚的事:“相睇(相亲)那晚,你俩不是呆在厢房到天亮吗,你不要跟我说,你斋坐了一晚上?”
“这~~,”陈篮秋差点没噎住,显然是没想到爷爷跟他说这事,不过,他也不想隐瞒什么,只愣神一会就如实说了:“还真是斋坐了一晚,头发丝也不曾动一根。”
“动头发干嘛。傻呀,”爷爷好像比孙子还急:“书都有说,哪个少年不多情,哪个少女不怀春,你这~~这不扯淡吗,怎么回事?”
可能真是本书扯蛋了。
爷爷不相信耳朵:“我就不信,娘子貌美如花,又有前有后(胸大腚肥),谁看谁馋得口水都要滴下来。你倒好,你倒有定里力来容忍,忍着光坐不做,不会是打球打的太多打出毛病吧,”可能是觉得此话不吉利,猛地就:“呸呸!”完了才转口说:“如果真是坐到天光,那我孙子得有多大毅力啊?”
“没办法,高爸有指示爷爷,我得照做。”陈篮秋尤显无辜。
“嗳嗳,我孙子办事他来吐什么象牙。”爷爷有点生气,同时也觉得意外,因为哪晚,深夜时分他在院子里支耳偷听了好长时间。曾断定厢房里有好事发生。且走照程序,按逻辑,当时就是‘雷公’的话也不济于事,没有什么能抵得住横陈的支条柳腰,于是说:““高爸跟你说些什么,说给我听听,看我怎么去敲他的像牙。”到这,他挠挠头皮转揭:“那晚厢房时不时传出嘎嘎笑声是嘛个事。不是乐事吗。”
陈篮秋不假思索:“不是,爷爷,高爸说,没结婚之前最好不动人家娘子身子。要不然,娘子害怕起来往后的事就难说了。我还如实照搬高爸指示,坐时不能开帆坐(不能打开双腿坐),尽量两**叠。爷爷,你说一晚都这样坐,人幸苦不,哎呀,那晚我没个舒服地。你问的嘎嘎声,那是我俩各自说自己曾遇到过最有趣的事而引发了止不住的笑。”
爷爷摇起头来:“唉!”的一声,楞没下话。没下话原因是他已意识:“咱家这遗传是不是在害人。”这时他反而觉得儿子教导有方,为长长久久,忍耐一时还是有必要~~。
就在这没下话期间,一个身穿绿色制服的邮递员骑着单车从门前一闪而过,这老爷子马上联想起前几天就是刚过去的那个邮递员给他家送来几封信,当时家里就他一个人,收信之后的他,一个心血来潮,带上老花镜琢磨起邮票邮戳来,看是否有杨家公社的邮戳,因为艳红在那地方,还有岚姨有几个月不来他家了,一直关心孙媳妇的他要知道最新动向。可艳红一般不写信,有事总爱托岚姨来告知。所以,倘真有艳红的信,他这次肯定得撕封看。在这琢磨期间,有一封信很特别,信封是用毛笔写的,没贴邮票,但番号戳,不过这个好解释,听人说,当兵的寄信不需贴邮票。又不过,那毛笔字吸晴,老爷子反复看,因为字迹隽秀,是一手好字。惜墨如金的爷爷自然就爱不释手了,他是左看右看,又不过,看着看着就产生遗憾了,因为隽秀中少了些许硬朗,他琢磨着,这手字是女人写的?还是欠火候呢?一想到女人,老爷子脑袋一涮,很快联想到孙子有个女同学在外当兵。
——嗯,莫非是她?
想到这爷爷又来一番:“你是不是还想着姓单的那个北方解放军姑娘啊。这样可不好,这样对艳红很不公平~~。”
哪壶不开提哪壶。话触到了陈篮秋心理敏感区,触得还很深,以致一时无语。
半晌没回应,爷爷有点慌,认为孙子不愿意隐私给人揭开,于是忙分辩:“我不是有心的,是有一天鹅王叼着一封开了封口的信,在三阶屋里里外外游荡,我怕它叼到河里红掌拨清波弄潮了,焦急上来夺下,但是我给信的字体吸引了,所以忍不住就看了。”
鹅王又不会说人话,赖它身上是人都没有办法给它、他。
这个陈篮秋平时也是个能说会道的主,可这时他只好选择三缄其口。那是爷爷的话撩到他最痛之处。本来这个女解放军已经在部队二年半了,这两年半可没少来信催,第一年发的是一催,第二年发的是孖催,今年小半年过去,她就开始每两月发一催。而他这边的情况是,他当兵不上,却去搞了定婚。离了心~~,一想到这茬,陡地个人头就黯然低下。回来不曾进屋的他,就这么手一撂,咣噹一响,手里的水瓢落入水缸。接尔吱声不吭又出门去。是抗议还是去散心不得而知。
“诶诶,去哪啊?”爷爷急起直追。然而老人腿脚没那么利索,等到追到门口,陈篮秋已去到几十米处的巷道口了。
陈篮秋趁拐弯,向后摆摆手,也不没回答。可能是示意不要跟着他。他这是去竹林,想去哪里转转。
盛夏的竹林绿意生凉,此时的万枝丹彩——正灼斜阳弄影。竹林可能说大了,但竹园绝对臣得上。竹园不大不小,光秃秃的地面,不说草
都不长,连落叶也没有,因为村里的孩童专扫这落叶拿回家当柴火。
竹林空无一人,陈篮秋只身来到,初始也有点懵;不知道为什么要来竹林、来到后同样还是懵;来竹林干什么。就这样闷生闷气在竹林踟蹰,他仰头看上端竹尾梢,低头看下寻竹笋尖儿——梢尖、笋尖搞得他半开半闭更加迷迷离离。可就在这迷迷离离间,突然视线水平里一株竹子的竹皮吸牢了他的目光,倏地那双又黑又大眼睛睁得老大。原来是竹杆青皮上有几行隽秀的刻字。这下他不懵了,知道为什么要来竹林了。这竹杆是这么写:一见此君面,荒村不是村,斜阳与可笔,栖雀子猷魂~~诗虽是截诗,但很贵重,从字里行间透着一股浓情,不难看出俩同窗时,单解放军姑娘就不嫌陈篮秋是农民,在她眼里村都没了,还怎么有彼是农(农民)、此是居(居民)呢?不设城乡这条线;你我就俩自然人;只要赤诚相见。大概这就是留古诗的原本吧。诗是俩读书时来竹园玩要,单姑姑用毛笔写,尔后陈篮秋用平口刻刀沿字迹刻入竹皮,再刷油漆覆盖。当时两人还为作品合成仰天大笑,命名为:二合一体。
提到命名,里头还有个惬意故事仔呢。当时刻完,陈篮秋脱口就来:“‘二合一’成功。”
可刚说完,单姑娘已觉得‘二合一’没高度、不脱颖、容易忘。于是说:“我说是‘二合一体’,怎样。”她觉得刻字毫厘不差,刻刀吞吃墨迹——完全分不出彼此。
“一体?”陈篮秋摇头,自打疑,暗忖,“做不到吧,”但又不敢反对,于是折衷,说:“‘两相随人’随便。”
单姑娘当然不甚满意,说:“就你会变,二就二吗,怎么要变两呢,胆小鬼。”然后嗤之以鼻:“哼!我还‘两相随人’‘两兼备人’,还有‘三分割颜’‘几相随人’呢,加一个体字也这么麻烦,亏你还是个七尺男儿,就这么定了‘二合一体’!”
“能合成体吗?”有人反问。但声音内颤,且细如蚊。
“只要目标明确,谁敢说不能合。”此话落地,女声不变。
那时候,陈、单只要有机会,总偷偷在一起,陈蓝秋赚工分搞田间管理,她来陪,农忙时节,像插秧、割稻(收割)她也来,总之广袤的东洋,经常出现这俩身影,所以美好记忆留下不少。
到这陈篮秋好像不懵了,知道为什么来竹林了。
既然知道,既然已找到了当年的合体,且按情节分析本应高兴一番,对不,可现实中的情节却不这样,陈篮秋却像丢了魂似,哪有高兴的份儿,这时他不跟他高爸姓高就已烧高香啰。“唉——”陈篮秋一声长叹,长叹虽不代表谁谁,但已说明一切。不过,他还是来了个比照:两姑娘身高几乎一样,容貌也各有千秋,都属于挺美的那一种,但说感情那就是一个天一个地,天的比海深,而地的就和方才水缸水那么浅,要不是爷爷勇敢地接过岚姨死活要放下的二百元钱,恐怕深度连水瓢水都不如。因为有一夜长谈方有水瓢水深就不错了,要不然,那零式感情。那来的深浅。唉!天高的海深的却远在天边,瓢深浅的却在眼前。好在两女人都好爱他,可目前的情况是;一个不敢爱、一个爱没开启,不敢爱的他死命想,没爱上的他试图去想。交织已好几个月了。看来还是要来个了断,不然害人也害己。因为家的需要,亲人的期盼,他再脚踏两只船,就不是贫下中农的好儿子了。想到这陈蓝秋自然就有了个清醒,而他又将清醒聚了聚,一个想法跃了出来——必须将爱心传递给艳红。
你陈篮秋才想到传递,可人家艳红的二次传递情传递马上就到。不过他还不知道。
这二次传情传递自然是委托岚姨。岚姨是有所考虑,先到大队部看高会计在不在,如不在,再往家走也不迟。
“我真会找,还真在这,”岚姨一迈进大队部,就笑骑骑(吟吟):“哎唷,你这个会计还挺积极嘛,人家收工回家搂老婆孩子,你还在这埋头算账。”
“喔,来了,”高会计头也不抬,当打招呼:“坐,喝水自个倒,我还得一会才能完事。要不你先回家,秋儿和他爷爷在家。”
“不急,你忙吧。”岚姨看着这人一本正经样突然有些不习惯了。要搁往常,一见面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挨近身,然后借头借路楷点油,那男骚——胳膊肘碰胸他最拿手,哪怕是在街上他也照干。那时岚姨就会小声嗔他:“死性不改。”
今个岚姨也忍不住话,说:“哎,你改死性了。”
高会计阴嘴笑笑:“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大队部呗。”说着岚姨不由自主抬头看;四面墙有三面挂满奖旗、一面也就是头顶上方悬;马、恩、列、斯、毛,五个伟人画像。唰的一下,岚姨眼睛一亮——敛笑变严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