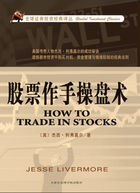“闯祸?”秦渊踏进门来,径直走到段南歌身后坐下,长臂一伸就拦住了段南歌的腰,理直气壮地趴在了段南歌的背上,“那小子差点儿一把火烧了如海军的大营,简直就是野性难驯!”
“天啊!”白鸾兰九惊呼一声,不安地看着秦渊,“那爷您……没把他怎么样吧?”
“没把他怎么样?”秦渊痞痞一笑,“那怎么可能?爷把他吊起来打了,现在还在如海军营里吊着呢!”
“爷!”白鸾兰九当即就给吓得白了脸。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旸被吊了几日了?
“你别吓她。”段南歌屈肘往秦渊的胸口上撞了一下,秦渊立刻就低笑起来。
“爷可没吓唬她,那小子若敢再犯,爷一准把他吊起来打!”秦渊咬着牙故作凶狠地说道,旋即又道,“说起来这事儿爷还没去找廖十算账呢!”
“你又找廖十算什么账?”反手递给秦渊一杯茶,段南歌顺势就靠进了秦渊怀里。
“怎么不找他算账?”秦渊一手搂着段南歌,一手端着温茶,好不惬意的模样,“将白鸾送过去的时候,爷还千叮咛万嘱咐,让他把白鸾留在广陵城,能别送到远处就别送到远处,结果他却给爷把人送到西北去了,害得爷想找人的时候找不到,差点儿连累了如海军。”
“这话倒是真的,”段南歌戏谑地看向白鸾兰九,“这天宋上下,怕只有兰九降得住那个傻小子。”
“可不是嘛,”秦渊笑笑,“白鸾你可快去营里看看他。”
“那、那奴婢现在就去!”话音未落,白鸾兰九就已经提着裙摆跑出去了。
望着白鸾兰九风风火火的背影,段南歌浅浅一笑,道:“果然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兰九在廖三身旁跟了些日子,性子也受了廖三影响了。”
“怕不止是廖三,”秦渊笑道,“所谓人以群分,廖三带的那支商队里都是那样的人。”
瞄了眼总显出几分坐立不安的潘青儿,秦渊问道:“这就是你花五百两聘回来的人?”
“嗯,就是她,”段南歌柔声答道,“先让秋心带带她。”
眉梢微动,秦渊的视线从潘青儿的身上移到秋心身上,再从秋心转到白茗,又从白茗扫向己未,打趣道:“别人家的主母选女婢都往丑了选,偏你选的个个都生得好看。”
段南歌微怔,视线也从房里的几个姑娘脸上扫过,不由露出十分满意的笑容,有些小得意地说道:“生得好看那也是我的,跟你没什么关系。”
“是是是,跟爷没有关系,爷就成天到晚瞅着你一个。”
己未嫌弃地扫了秦渊和段南歌一眼,纵身就从窗口跳了出去,白茗和秋心二人将桌上的东西归置好,然后也一齐离开了房间,走时还不忘喊上不知所措的潘青儿,两人再把屋门一关,那屋里就只剩下秦渊和段南歌两人。
秦渊满意地点头道:“你身边这几个是越来越机灵了。”
“那你也不看看是谁教出来的。”段南歌的身子往下一滑人就躺在了秦渊腿上。
“瞧把你给懒的,”秦渊低头,好笑地看着懒洋洋的段南歌,“那个潘青儿你得注意着点儿,白茗是国公府的人,秋心是宫里出来常在爷身边侍候的,己未又是南楚十二卫出身,心性跟眼界都与寻常女子不同,爷连白鸾兰九这样的都帮你送出去历练了,这潘青儿也得好生教导一番,只可惜她不好像白鸾兰九那样给送去廖氏,让她跟着秋心是好的,但现在就把她留在身边,你自己可得多留心一些。”
“我留心什么?”人懒了,便连声音都是懒懒的,“你才该多留心一些,且不说那颜雅君兴许还在广陵城附近,这潘青儿的娘可不是个知足的人,等这五百两花完,怕是又要来打王府的主意。”
眉梢轻挑,秦渊道:“爷以为你将她买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好要替她善后了。”
段南歌叹息道:“我倒是想帮她了,可对她不好的人是她的爹娘兄弟,是她的血缘至亲,只要她割舍不下,那谁都帮不了她。”
摸了摸段南歌的脑袋,秦渊柔声道:“你的心里既然已经有了主意,那爷就不过问了。”
段南歌扬了扬嘴角:“重建的事情进行得怎么样了?”
听段南歌提起这事儿,秦渊忍俊不禁,道:“爷原以为司天台里那些人都是正经的学士,有别于江湖术士,是讲求真理的,可近日才发现他们跟寻常的江湖术士也并没有什么区别,就说那徐泽,信口胡说起来一套一套的,比爷还能唬人。
祭台那边事故频发,百姓们本还在说是你我二人给广陵城带来了厄运,爷安排多少人乔装成百姓混在市井想要试着扭转局面都没能成功,可徐泽拿着个八卦盘去了之后,神神叨叨地一通乱走,几句话的功夫就将这事儿说成是广陵城中有人聚集邪祟作乱,结果乱了城中风水,这几日又在城中圈出几处邪祟聚集的地方,他说的那些个怪力乱神的东西爷不懂,反正百姓们好像都听懂了,嚷着说要配合徐泽拔除城中邪祟,爷看这事儿是没有爷插嘴的余地了,这几日便没跟着他,这事儿就全由他去做了。“
“陛下选的人,自然是有本事的。”
“爷当然也认同他们的本事,”拉过凭几靠着,秦渊的声音也懒散起来,“只不过爷原以为他们就只有观星测命的本事,没想到竟也有花言巧语的本事。”
段南歌哂笑道:“天真,你也不想想那司天台是做什么的,他们要观星测命没错,可那真正的天命国运岂是能说给文武百官和寻常百姓听的?他们若不会说几句胡言乱语,等陛下需要的时候他们要如何以玄学之论来安抚民心?”
闻言,秦渊蹙眉:“可颠倒黑白、口出虚言对他们来说是损修为的事情吧?”
段南歌挪了挪身子换了个更舒服的姿势,道:“但辅明君、佑天下也是他们的功德。”
沉吟片刻,秦渊重重地点头:“有道理!那你说咱们这广陵城要不要也设个司天台之类的官署?”
“要那个做什么?搜集江湖神棍吗?”段南歌扭头白了秦渊一眼。
秦渊无辜道:“但爷真的是头一次觉得这玄学十分好用,反正他们要说给百姓的都是拟好的虚言,就找些江湖神棍来也是可以的不是吗?”
“那你不如去大觉寺拜访住持,广陵城可没银子养一群只会胡言的神棍。”
“大觉寺?”秦渊狐疑地看着段南歌。
段南歌打了个哈欠,道:“从广陵城向西行,在安河镇北边的山上。”
“你去过?”秦渊问段南歌。
“去过啊。”段南歌不以为意地答道。
“那爷为什么没去过??”秦渊一脸不满地瞪着段南歌。
“呃……”段南歌只得睁开眼睛看着秦渊,无辜地眨着眼。
“你这小没良心的!”秦渊咬着牙捏了捏段南歌的鼻尖,“爷整日忙得不可开交,你竟瞒着爷溜出去玩儿?”
“那是……那是秋心说的,秋心说什么来了新地方得去拜一拜这边的神佛,听人说这边最有名的就是大觉寺,我们就……去了。”
“秋心说?”眉梢一挑,秦渊抬手开始挽袖子,“秋心跟你说了,你就不能跟爷说一声?还有,你什么时候这么听秋心的话了?她让你去你就去?嗯?”
一见秦渊挽袖子,段南歌连忙起身爬开,奈何还是慢了一步。
“往哪儿跑?”向前一扑就将没能跑远的段南歌压倒在地,秦渊毫不客气地搔起段南歌的痒来,“你这样的坏女人要接受惩罚!”
“等!我错了我错了!下次不管去哪里都带上你还不行吗?”
“下次是下次,这次是这次,无规矩不成方圆你说是不是?”
屋子里的夫妻俩说闹就又闹开了,屋外白茗和秋心出门后就自觉地下了一层,即便如此还是能听到秦渊和段南歌嬉闹时的声音,但白茗和秋心早就习惯了,独才刚进府的潘青儿又羞又窘地红了脸。
觉得潘青儿这脸红的模样新奇有趣,秋心就调侃道:“青儿姐姐的面皮这样薄可不行,吴王府这两位主子可是不管相识多久、不管成婚多久都跟新婚一样蜜里调油,咱们这些在近处侍奉主子的可得把面皮磨得厚实一些才行,不然可待不住。”
己未不知从哪里绕了出来,打趣秋心道:“我瞧就你是靠面皮厚撑住的,我跟白茗可都是凭着坚定的心性侍奉在王妃身边的。”
秋心不甘心地回嘴道:“我的面皮再厚也敌不过你,偷听爷和王妃的墙角都不会脸红,不知羞!”
说着秋心还冲己未做了个鬼脸。
“你这丫头竟敢在这里掀我老底,看我怎么收拾你!”己未一听这话就瞪起了眼睛,一步两蹬地跨上台阶就去抓秋心。
她那是听墙角吗?她那是亲自为爷听诊!秋心这蠢丫头竟然在爷和王妃的门口说,这不是想爷出来收拾她吗?欠打!
于是几句话的功夫,这屋外也闹开了,塔楼里顿时热闹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