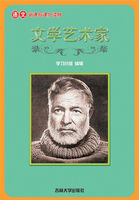杏儿这回没有猜对。因为羽然今天可是老老实实在住处呆了一天,连床也没下。
因为他病了。
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就受了风邪,从雪薇家回来之后便浑身酸痛,头目发热。也亏得铁冷棠在身边,当下便问小二请了大夫,诊了脉开了药方。因是半夜,到底捱到第二天早晨才抓了药煎好服了。
羽然吃过药,睡了一会儿便醒了,只觉浑身出汗,头目却清凉下来。他望着帐顶想了片刻,心中到底牵挂着雪薇今天的比赛,便想起身赶过去看。谁想他两脚刚一落地,便被推门进来的铁冷棠看见了。
铁冷棠赶紧叫道:“公子不好好在床上歇着,为什么要下地?”
羽然搪塞道:“我想去小解。”
“我陪您一起去。”
羽然心中郁闷不已。连小解都要跟着,这铁冷棠究竟是有多信不过自己呢?
他马上沉下了脸,道:“我已经好了,不必由你伺候。你可以歇一会了!”
铁冷棠却直戳要害:“卑职不是担心您的身体,时担心您回借小解之名,跑去丁姑娘那里。”
顿时,羽然的目光变得刀一样,直直刺向铁冷棠。但铁冷棠缺好像根本没有感觉,坦然得回望着他,道:“古人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您是老夫人唯一的爱子,更应该爱惜自己的身体,怎么能为一个萍水相逢的平民女子如此拼命?”
一股戾气从羽然心底陡然升起,他望着铁冷棠的目光里竟有了些杀气。
“铁先生,这就是你对丁姑娘的评价?一个平民女子?还是说,这就是你看待别人的眼光?我以为你真是‘铁面’之人,没想到你也如此势利!既然如此,那你更不用管我了。毕竟我们身份悬殊,我怎么会听一个下人的话!走开,我要出去!”
此时的铁冷棠本应恐惧才对,但他却出乎意料地平静,从怀中掏出一块铁牌,举到羽然面前。
“公子,卑职自然没有要求您的权力,但是它有!”
黑色的铁牌看上去普普通通,和一块平常铁片毫无二致。但羽然见了它,脸色却变了。
“我母亲将它给了你?”他冷冷地问,有些不相信的意思。
铁冷棠道:“这块铁牌,是先老爷留下的遗物,意义之重,您该比卑职还清楚。所以卑职芳草所说,不是卑职之意,而是老夫人之意,先老爷之意。望公子三思!”
羽然狠狠地压下了心头的怒火。别的他可以抗拒,但唯独这个,他无法反抗。
“既然你身上带着这个,那为什么不拿来要求我必须回家呢?”他略带疑惑地问道。
铁冷棠道:“因为老夫人嘱咐过,这铁令可以用来要求您,却不能强迫你那回家。老夫人硕,您应该心里很闷,若实在不愿回家,那就让您玩够了再回去。所以,卑职没有将它直接拿出来强行要求您回去!”
羽然心中一动。他没想到他母亲还有这样的嘱咐。都说母亲心疼儿子,从一出生便锦衣玉食的羽然从没感觉到母爱的特殊,反倒是今天,离家千里之外,听见这么一句嘱托,让他心里泛起了一丝微澜。
他眉头依旧紧锁着,却还是在床上坐了下来。
“那您已经决定不再去瑞祥楼了?”
“嗯。”
羽然答应一声,在床上坐了下来。
过了中午,羽然的病反复起来,又发烧了。虽然烧得不厉害,但四肢沉沉的,连眼皮也不想抬起来。吃过药,烧微微退了些,但他精神却始终没有缓过来。
晚间,小二给送洗脚水的时候,羽然问了问他瑞祥楼打擂的情况。小二笑嘻嘻地将他知道的讲给羽然听,那声情并茂波澜起伏的样子,真不比说书先生差多少,听得羽然满意地连连点头,最后还赏给他一块碎银子。
小二兴高采烈地揣着银子走出去,羽然则对着黄晕晕的灯光出起神来。
铁冷棠见状,咳了一声,道:“公子,您还在想丁姑娘?”
羽然回过神,微微侧头,眉毛一挑,道:“你若装会儿傻会死吗?”
铁冷棠皱起眉来:“卑职装不得傻,还有一封信您没有看过。”
羽然盯了他片刻,冷笑道:“好,你把信拿过来,我看看。”
铁冷棠将信从文袋中取出,递给羽然。羽然打开信,一纸娟秀的小字便展现在他眼前。一时间,一股烦乱和一种莫名的思念同时袭上心间,一个牡丹一样艳丽的女子的面容仿佛在字里行间凸显出来。
“惊容……”他喃喃念着那个名字,不由自主地看着那一纸熟悉的字。
“羽然吾兄:
惊容再拜,谨奉此书。不知容儿前日究竟有何处得罪吾兄,竟于订婚之日,将妹冷落一旁,独自离家,致使妹倍受奚落,落为他人笑柄。然妹今致书,非为质问兄之薄情,只为惦念兄今在外,人单衣薄,当有古道思乡之悲。又太妃年事已高,念子心切,兄纵不为惊容为虑,不觉客路孤单,亦该以太妃为念,早日回京。此惊容一片诚心,望兄体谅。另,路途之上诸多不便,望兄自珍。妹惊容泣字”
“‘非为质问兄之薄情’?”羽然冷笑一声,将信举到灯前。眼看灯焰即将燃着那张粉色压花的信笺,他又一犹豫,将信按原样折好,重新装回信封。
刚刚将信装好,忽然传来敲门声,然后便是一个陌生的男子的声音:“请问潘公子在吗?”
没等羽然答话,铁冷棠先霍然立起,走到门边沉声问道:“外面是谁?”
门外的男子答道:“小的是丁府的管家,来给潘公子送请帖。”
羽然示意铁冷棠打开门,见丁秩拿着一张大红的帖子恭敬地站在门口,等着羽然回话。
铁冷棠回头望着羽然,羽然道:“请丁管家进来吧。”
铁冷棠闪身,丁秩微弓着身子走了进来。羽然道:“丁管家,这些日子你主持擂台赛,也够辛苦了,现在又来给我送请帖?不知是什么事情?”
丁秩道:“明天家主要给雪薇小姐设宴,庆祝她成为第二十二代神厨,特地差遣小人来给公子下帖,邀公子前去赴宴。不知公子能否赏光?”
羽然刚要开口,铁冷棠冷着脸问他道:“公子,您昨夜生病,现在还没有痊愈,是不是明天该继续休息一天?”
羽然瞥了他一眼,嘴角微勾,道:“铁先生替我想得周到。但丁家主一片美意,我又不是动不得挪不得,有什么不能去的?先生就不必担心了。”
丁秩见他俩针锋相对,心下不免一紧,陪笑道:“潘公子若是身上不舒服,小的回去照实回复家主便是。不管怎样,还是公子贵体要紧。”
羽然一摆手,道:“不必了。你就回复老家主,明日我一定去。”说着,接过丁秩手中的请帖,看好了时间地方,便将他送走。
待丁秩离去,羽然冷眼望着铁冷棠,道:“铁先生,你不觉得你太过小心了?别说我现在在外面,就是在家里,老夫人也管不了我这许多事。我要和谁交往,自有分寸。便是你有玄铁牌,也不能越界太多吧!”
铁冷棠不由摸了摸修剪地整整齐齐的胡须,掂掇起羽然说的这几句话来。
他是个忠主之人,性子也比较鲁直,但他也不傻,知道这位青年王爷若动了真怒,便是连王太妃也压不住。现在他说的这几句话,已经是给自己警告了,若他再不知进退,恐怕不知这位王爷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来。于是他小心地说道:“公子误会了。卑职只是关心公子的身体,并没有干涉公子私事的意思。若是公子觉得身体无碍,明日卑职陪您赴宴便是。”
羽然冷哼一声,道:“那里又不是龙潭虎穴,我要你陪吗?这几天你跟着我,恐怕已经将我的行踪告诉给老夫人了吧?嗯……怕是花家也会跟着知道了。”
铁冷棠出了一身冷汗。正不知如何回答处,羽然又说道:“不过你不必担心,从你说要跟着我的饿时候起,我就知道你会这么做了。有句话叫‘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你可明白?”说完,便深深看了他一眼。
铁冷棠怔了片刻,目光有些黯然。他明白了羽然的意思,那便是不论你怎么做,我都会我行我素。至于回京以后将面对什么样的事,那再另当别论好了。
铁冷棠在心底暗暗叹了一口气。从他接这份差事的时候,他就知道不好做。但没想到竟让他如此为难。他又伸手摸摸自己的胡子,低声道:“那,请公子早点休息。卑职退下了。”
羽然没有理他,转身背对着他,负手而立。铁冷棠见又碰了钉子,只好悻悻地走了出去。
丁家的庆祝宴上,羽然到底没有带铁冷棠去。
他没有骑马,散步一样向丁家走去。还没到丁家所在的清仁巷,便听见一派鼓乐喧天。他微微一笑,加快了脚步。
两排吹鼓手从巷口一直排到大门口,无论吹的还是敲的,都卯足了劲儿,鼓起腮帮,甩开膀子,使劲地吹,使劲地敲。而那些前来祝贺的人也都提着礼物,有说有笑,喜气洋洋,那热闹喧腾的气氛,真如办喜事一般。
羽然一边和一些并不认识的人打着招呼,一边从人群中穿过,他真想看看此时的雪薇是不是和大家一样,满面笑容;而她满面笑容的时候,又该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