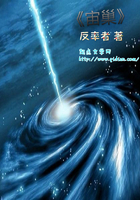川西北高原是一块神奇美丽的地方。这里世代居住着藏羌民族,他们有着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本土文化,独特而智慧的思维方式和古老质朴的民风民俗。笔者不揣浅陋,搜集整理数则,以飨读者——
路人取名
一个人来到世上,第一桩事就是要取名。名虽是一个人的代号,但是一旦确定,可能就要管一辈子,所以取名也是人生之大事也。然而,羌族人给新生儿取名既不像汉民族查字典,找依据,也不像藏民族翻经书,有由来,它是在偶然间碰上偶然出现的路人来随心所欲地取名(或曰路人取名)。这种视严肃为轻松、化庄重为随意的思维,是否隐含羌人自己的人生哲学也还有待考证。
取名的大体经过是:当新生儿满月时,舅家和其他亲朋均要来吃酒朝贺。满月当天,太阳刚出来,新生儿的母亲在众亲友的簇拥下抱着婴儿先登上房顶敬拜天神,然后再来到大门口,在端公或寨老主持下,面向初升的太阳献上刀头敬酒,点燃柏香祝颂祷告。赓即,主持人在新生儿的额头正中点上一点带黑色的猪油印记,继而口中念念有词,向空中和四周抛撒青稞籽或水子米(小米),其意是祝福这个新生儿像青稞籽和水子米一样繁衍,生生不息。敬毕,便开始盼望和寻觅经过的路人。一旦发现,便盛情款待并邀请给婴儿取名。路人的经历各异,水平各异,体悟各异,因此所取之名五花八门、雅俗不一,但是归结起来无非大多是长命、富贵、添财、添福之类而已。路过的农民为了生计大多都比较匆忙,有的扛着犁锄,有的提着筛子或拿着绳子。邂逅相逢,主人殷勤备至无非想讨个口彩,取个吉名。而匆忙中的路人毫无思想准备,虽然喝了酒,脑海里却是一片空白,所以一时弄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逼急了只好取一些与自己身边相关事物的名字来。诸如:筛筛保、绳绳保、犁犁保、园园保、长命保(保,就是保佑,表示万物有灵)……抱上婴儿能遇上路人就算有运气了,有时半天没有遇上过路人,那就只好变通取名了:如遇猫过,喊新生儿为猫猫或虎虎,遇狗过就唤狗狗,有猪过就叫猪猪了。要是没有动物过,就只好把周遭的环境作为取名的来源了,这些人名大概就与天、地、水、树、花花、草草有关了。
十多年前,羌族画家周巴等人在阿坝州民族文化宫绘了一幅新生儿喜迎朝阳的壁画。画中一个活泼健壮的婴儿在一轮金红朝日的沐浴下光着身子在母亲怀里手舞足蹈。一位银须美髯的羌族老人右手中指虔诚地弹蘸着青稞咂酒,神情庄重地祝颂着。整幅画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和神秘感,也充满了勃勃的朝气和一团孩子气。这幅画其实就是“路人取名”的艺术再现。我当时一见到这幅画,就激动得差点要流出泪来。因为这幅画也许无意中触动了我生命的起源或者是透露了某种文化的信息吧。这些年因为文化宫维修改造,这幅壁画再也没看到了。可是这幅画中的生活情景早已如岩石般牢固地烙在了我的心中。
上山打猎 见者有份
早先,山区里森林茂密,水草丰茂,到处是绿草鲜花,蜂围蝶阵。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下也有着众多的野生动物,深山的虎豹豺狼,浅山的獐麂兔鹿,随处可见。因此,当时的山民将狩猎视为主业。从事狩猎者为猎人,其家就是猎户了。长期以来狩猎者十分和睦,顾群,他们有一条不成文规矩,这就是“上山打猎,见者有份”,就是指获取了猎物,不可一人独享,凡是见到了猎物者(不一定参与打猎),都可以分一块肉,尝一勺羹。这个规矩虽不成文,似乎也没有看到任何惩戒性的手段,但在生活中十分管用,它深藏在山民的观念中,上升为他们评判某一个人的人品的标尺。
现在野生动物受到了严格的保护(当然野生动物也非常少了),打猎的人也几乎看不到了。但是“上山打猎,见者有份”的习俗仍然“换汤不换药”地沿袭着。例如,寨子里某家杀了一头猪,许多亲朋都会围着来尝鲜。再如某家需要背柴,收割庄稼,少不了请“工夫”相互帮忙。做完活,大家一起大口吃肉,大碗喝酒,敞开喉咙唱山歌,醉醉醺醺跳锅庄。这里,一寨人好比一家人,一家人就得有难同担,有福同享。
火渣当笔“十”字为号
先前,山寨里的人相互以诚相待,一诺千金。据父辈讲,数百上千年前,由于羌区农业十分落后,特别遇上灾荒之年就会颗粒无收,所以大部分青壮山民都得到内地或牧区打工维生。比如内地汉区的筑堰修坝,牧区的修房建庙都曾有过羌人的汗水和心血。这些离家外出打工者往往一去就是一年半载,有的举家外出,甚至三年五载才回来。离家时财物家当就托亲朋予以照管,比如余存粮食面粉之类,靠什么来清点记录呢?就从火塘里拿出一截火渣权且当笔,在托管物上沿画个“十”字作为记号,就算交涉清了。数月经年,外出人员打工回家,看看“十”字有无变化位移,也就了事。我相信,就凭那个时代的生活条件,他们一定会将粮食等必需品视为“金子”,因为那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命根子!然而他们却居然使用可以随意涂改的火渣画“十”字为记号,个中原因不言而喻。实际上他们把相互信任看得比金子还重,因为相互信任才是他们真正的命根子。
眼下述说“火渣当笔,‘十’字为号”,也许有人听后觉得好笑,好比天方夜谭一回、神话故事一个,或曰“古人头脑简单、愚昧”。然而,细细想来,其实愚者不愚、智者不智,终究谁笑谁也还难说呢?
添新口,立凳谢绝客人登门
在我国,按常情,有新生儿降临,举家喜悦自不必说,就是三朋四友也免不了前来道喜祝贺,羌民族也不例外。但是奇特的是新生儿刚降临的头三天,羌民族却有立凳谢绝客人登门的习俗。具体做法是:新生儿刚刚呱呱落地,一家之主就要马上向历代先祖烧香通白,祈请神灵护佑新生儿一生平安吉祥。然后,取一根长板凳到大门外立起,暗示凳子不能坐人,凳子贴上一溜红纸,以此昭示家有添口之喜,在三日内谢绝客人登门造访。生了男孩,要在门槛上绑一只草鞋,生了女孩,要在门槛上绑一只布鞋。路过的人一看见立凳和标示,规矩自明。一个村寨,一传十、十传百,一袋烟工夫,全寨子的人都已经明了。于是,这个添口之家三天以内清清静静,绝无外人一声一影之扰。但是三天之后亲朋乡邻都要前来问候贺喜,当地人称为“送竹米”或“赶篼篼会”。“送竹米”的人带上鸡蛋、猪脚、米、面等礼物,也带着盈盈的笑声和深深的祝福,和三天前的沉寂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照。我就不明白,这一冷一热、一静一动的习俗,究竟缘于何由。
羌人认为:第一,刚生婴儿,产妇体弱气虚,需静养休息,需恢复体力元气,不准外人扰攘,否则产妇易生病,易断奶水(当地人称“吕吕孤全”——意为塞奶);第二,产妇流血排秽,屋内污浊不洁(这是不科学的认识),外人靠近,有遭秽气之险,当年百事不顺。所以至今一些羌族地区,宁可靠近死人,也不愿靠近产妇。这可能是立凳谢绝客人登门所演绎的一个寻常的生活例证。这个习俗,至今看来,有其科学合理的一面,但也有其歧视妇女、封建落后的一面。
敬羊神,家家供干盘
史传羌人先民是游牧民族,这是十分可信的。就以“羌”字作考,从“羊”从“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便有“羌,西戎牧羊人也”的解说。既然是牧羊人之后,敬拜牧羊神,当属顺理成章之事。正好,千百年来,家乡就有正月头上敬羊神,家家供干盘的习俗,这是不是跟我们这个民族的生产方式有些相关呢?
每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忌讳出门,就连牛羊都不出圈。尽管牛羊饿得直叫,主人也只能在圈场里上草喂水。可是到了正月初二(只要不是属虎的日子),牧羊人就早早地挨家挨户喊着吆羊出牧。这时主人就带着早已准备好的供品(当地称“干盘子”,内有猪头、猪耳、香肠、筋肉、花生、核桃、各种水果杂糖和敬酒等)和精心制作的两面小白旗一起上山来敬牧羊神。当地羌语称为“趣趣狄”(意为给羊神敬供好吃的)。村寨有大小,遇上几十户上百户的大寨子,人就众多,大家吆着羊,说着、笑着、吼着,闹热得很。来到神山,各家约定俗成地把自带的一面小白旗遍插山头(另一面带回自家羊圈内插上),摆上干盘供品。由牧羊人焚烧柏香,虔诚地跪拜天地、羊神,祈求保佑风调雨顺,六畜兴旺,无灾无难。敬毕,大家开始围着吃供品干盘,喝着酒,唱着歌,跳着舞,直闹得红日西沉,大家才赶着羊群醉醺醺蹒跚而回。
在回程的路上,各家去敬拜的人还得沿途捡羊粪,回家后他们把捡回的羊粪“一五一十”地数着丢进羊圈。据说数了多少粒羊粪,来年就会发展多少只羊子。这近乎儿戏的做法,每家人却做得那么认真,那么毕恭毕敬,这也许就是一种习俗说不清道不明的魅力所在。
至于敬牧羊神为什么做白旗,至今无法考证。但是为什么做两面白旗,我分析可能是一种敬神的凭证,一面插在神山上,一面插在自家羊圈内,以表示这一家人在神山上去敬了神,完成了某种仪式,神与人似乎有了某些“敬”与“佑”的契约。是不是这样,聊作猜测而已。
嫁新娘,胞兄背送出门
阿坝州汶川、理县、茂县一带新娘出阁时有一系列风俗习惯,其中新娘离开娘家门口时,不准自己跨出门槛,而是由自己的同胞兄弟背送出去(如果无同胞兄弟,则由堂兄弟或表兄弟代替)。具体经过是:出阁时辰一到,礼仪先生(支客师)便大声宣布“新娘出阁——”赓即,吹鼓手(吹吹匠)开始吹奏悲怆欲恸的《离娘调》。顿时,新娘和满堂亲朋早已哭声一片。在支客师和伴娘的簇拥下,新娘来到祖先神牌下烧香跪拜,以表“辞祖”,继而,由胞兄挥泪背上背。出门前,把预先准备好的一桌筷子(一般为十二双)向背后(神牌方向)抛回去,以表辞别,另立门户,另兴家。当胞兄背出大门后,新娘转乘轿子或骑马随接亲队伍来到男方。自此,新娘被视为另户家人,除非娘家有请,不得擅自回娘屋,更不得在娘家过年过节。
这些年,老家农村办喜事,胞兄背送出门的习俗渐渐少见了,自由恋爱、男女自由来往走动的比较普遍了。出阁时的哭声和抛筷子的情景已被轻松的笑声和亲吻嬉闹所代替。这也许是一种文明和进步的表现。然而,古老习俗把喜事看作人生之大事,视结婚为人生的里程碑,是独立生活的起始,把婚事办得庄重、体面、神秘,让人感到难得,感到震撼,感到永世不忘。相比之下,今天,面对这些习俗,我们似乎缺少点回味,缺少点关怀,也缺少点传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