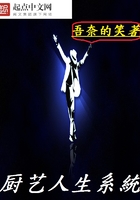门刚开,安涌灏就看到田媖爸爸田岳川一脸严肃。田父除了让他进屋里坐着也没有多说什么。田媖也早就起床,坐在沙发上,安涌灏惊喜道:“媖媖,你……你这两天去哪儿了?”
“你先坐下。”田媖没有说话,田父一边关门一边说。
“早点吃过没有?”
“吃过了。”
田父坐在安涌灏旁边,他不好再主动问什么,只能用余光窥视田媖。半晌,田父说:“你不是想知道我们和媖子这段时间去哪儿了吗?”
安涌灏看着田父,田父说:“我们从公安局把她带出来的第二天,就带她去她外婆家了。”田父停顿了一下,继续说:“给她补一个生日,可她并不开心。”
安涌灏明白田父的意思,心里有话又口舌嗫嚅。田父说:“既然公安局让你出来,说明你也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
安涌灏似乎看到希望,可田父突然说:“可是媖子被吓到了,你该知道为什么!”
安涌灏说:“田叔叔,对不起,我真的不知道……”
“你对不起的不是我!”田父说,“是媖子。”
安涌灏对田媖说:“媖媖,你能听我解释吗,那天的事情,我也真的感到非常意外,我……我……”
田媖看了安涌灏一眼,也低着头。田父说:“那天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你,不过你敢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我已经听公安局的人说了,你那个朋友,你那个‘哥’,干的可是走私文物的事情,案件公安局的人还在调查。你知道的,媖子她妈,我,再加上她,我们一家在须埠大学做的是什么,学的是什么,当这种事情把媖子牵扯进去,她是什么感受,相信你多少也会有感觉。”
安涌灏说:“田叔叔,那天的事情我真不知道,而且……而且我不相信我炎哥——我那个朋友会做这样的事情。”
听安涌灏还在左一口右一嘴“炎哥”地称呼,田父脸色拉了下来,或许是书香门第长久习染的缘故,他不会像个骂街的泼妇对安涌灏连喷带指。这时田媖母亲穆彤买早点回来了,安涌灏给她主动打了招呼,田母只是瞥他一眼,而后转过头准备碗筷。到了饭点,田父和田母也先不谈安涌灏的事,还让他坐过来一同吃早点。安涌灏和田媖什么都没有吃进去,田媖自始至终一句话都不说,不久走回自己的房间。安涌灏想追上去,田父让他坐下。接着让田母把田媖的那份先放进冰箱,田媖什么时候想吃了再拿出来给她热一下。安涌灏也没有动手,田父吃完后,田母将他的这一份也收回冰箱。
田父把安涌灏叫到客厅,坐下后,说:“安涌灏,和媖子认识四年了吧?”
“哦……”
田父说:“你们两个差不多大,她还比你大一点。她是从本科开始读,你读的是预科,今年她毕业了,而你要到明年,多读一年不是什么坏事,反而能比别人多一年时间了解大学,后面不至于过得太仓促。你现在告诉我,预科那一年,你都了解了什么?”
“我……”安涌灏吞吞吐吐。田父说:“我和媖子她妈都是须埠大学的老师,你也是里面的学生,虽然不在一个学院,但从某种角度上说还是有师生之缘。现在我就以老师的身份问问你,你读预科的那年,到底有没有好好了解过须埠大学?”
安涌灏吱吱呜呜,说:“我……我主要就是修大一和部分大二的公共课,别的,也就是和媖子在一起……”
“没有想想为什么要读大学?”
安涌灏不表态。田父说:“我听媖子说,你对须埠大学,不,对须埠都不太满意,你本来要考北京,结果来了须埠,觉得自己委屈了。”
安涌灏点了下头,说:“我以前是这么想的,可是……后面我觉得须埠很好,须埠大学也很好,这里有我的——”安涌灏觉得自己又要把傅平炎说出来,这么一弄田父肯定会板脸,改口道:“主要是因为媖媖。”
“媖子就能改变你对须埠的不如意?”
安涌灏心神麻乱。田父听得出这里面的真真假假。
“怎么改变的?”
安涌灏说:“就是……就是……我觉得可以为……为一个人找到自己明确奋斗的目标,就是……就是……”
田父说:“就是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有点手段?”
安涌灏沉默了。田父说:“我和媖子她妈妈都是老师,比不得巨商富贾,可也不是被贫穷逼怕的人。媖子对人要求也不高,当初追她的人,包括后面你和她交往时,想要从中作梗的,条件比你好的多的是,可是媖子没有动心,好几次都有人托朋友的朋友让我带媖子去相亲,至于说是为什么,不用我说你都知道。我和她母亲都尊重她的意思,皆以婉言拒绝,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你。你这个人我也清楚,人确实聪明,也很想有一番作为,但是自以为是,从不和自己的同学分享什么东西,媖子每次问你外面干什么,你都避而不谈,总是做出一副傲慢和自大的样子。后面你给媖子惊喜后,她又一笑了之。去年媖子过生日,赶巧和她的高中同学一天,人家的男朋友送了别人一个平凡的礼物,而你却大出手笔,有这么一回事儿吧?”
安涌灏点点头,“我只是想让她觉得她佷有面子。”
“面子!”田父严厉道:“那你想过别人的面子没有,你想过给她面子没有!就因为你这种自以为是的想法,让她朋友的男朋友觉得害羞,让她的朋友和她产生误会……你既要给别人面子,为何又要施人以尴尬?”
安涌灏是第一次听田家人这么看待这回事。说实话,或许他都快忘了那次生日聚会。在他眼里,田媖才是自己的主角,但就像田父说的那样,他只是想证明自己。
田父说:“论实力,天底下,就连须埠比你有实力的多得是,人家听说媖子和你交往,还看不起你是外地人。我和媖子她母亲一向尊重她的选择,并不是说背地里接受你的傲骨,而是出于长者和师者的心态,认为你还在成长之中,要一步步走向成熟,可你却令我们很失望。你作为一个学生,没有一点精心修读的耐心,反而迷信市侩禄蠹的教导。媖子不需要一个只知道把自己证明给自己看的人。”
田父的话让安涌灏内心顿感震彻,也许这会儿才是他了解自己,了解田媖的开始。他感到些不安。田父接着说:“安涌灏,追求财富没有什么错,可不能总以某一类成功人士的视点为坐标,否则这个世界太多的就是失败者,救死扶伤尽心尽责的医生是‘失败者’,披肝沥胆忘我安危的人民警察是‘失败者’,临风曝日保家卫国的士兵是‘失败者’,恪守职责安全驾驶的司机是‘失败者’……我想你知道我说的‘失败者’是什么人了吧?”
安涌灏说:“田叔叔,我知道您的意思,我只是想让媖媖……”
安涌灏怕田父批评,把要说的话又咽回去,田父让他说出来,他说:“我只是想让田媖觉得我不是甘于平庸的人,让她觉得我是个为了她可以去奋斗一切,可以什么都去做的人。我知道,我比不得您说的那些比我有实力的人,但是……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男人,我想让一个女人不为自己的生活发愁,而且欣赏男人的勇气和冲闯……”
安涌灏说着都觉得直截了当中带着些虚飘飘的味道。田父说:“那你觉得你现在是个男人吗?”
安涌灏不敢表态,田父说:“你以为我们一家学历史的就继承了男尊女卑的观点?你错了!而且为了一个女人什么都去做,这难道就是所谓的男人?”
安涌灏没有再说话。田父说:“安涌灏,你——人终归是和人生活,你不要想着人定胜天的那一套,人狂有祸,一个人要是什么都敢做,最后只会不分青红皂白,还有是非观念吗?”
安涌灏说:“田叔叔,我知道您的意思,可我觉得,我分得清是非区直。”
“没错。”田父也点点头,“可你的那个‘炎哥’又怎么样?”
安涌灏被问住了。田父说:“人会因贪婪心而误入歧途,而太多的尘世接壤会让人不辨是非。人们都说中国的历史过分强调了对与错,一个真正读历史的人,不应该以主观的立场评判某些人物或某些事件,可是要是落到具体的一件事上,要是有人议论是非,为什么人们就不愿意从细节上去关注一番,而仅仅停留在本能的感性认知上。”
田父到此觉得自己说得深了些,或许安涌灏连基础都没有打过,他继而说:“多的我就先不多说了,你就好好想想吧。还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媖子……不打算去须埠大学读研究生了,换句话说,可能是因为她想换个环境。”
安涌灏心里顿时打了个大咯噔,他看了田父一眼后又呆呆看着地,过了快半分钟才说:“田叔叔,能不能让媖媖出来,我想问问她?”
这时田母从厨房走来,说:“媖子不想见你,因为她生日那天的事。”
田父说:“她什么时候想跟你说,什么时候会说的!”
安涌灏真恨不得敲开田媖的闺室,只恨田媖父母都在这里。起身看了看田媖的房门,然后耷拉着脑袋离开了田媖家。
走后不久,田媖打开卧室房门走到客厅。田母说:“媖子,安涌灏已经走了,你也准备准备吧。”
田媖突然打开门,赤脚穿上凉拖冲了出去,田母想叫住她,田父只说让她走。有些担心的田母最终还是按捺不住跟了出去。
安涌灏这时已经走出小区大门,也许是田媖的脚步声让他过于熟悉,他驻足回头,只见田媖追了过来,他赶忙迎上去。当田媖冲到他面前时,他迫不及待说:“媖媖,你……”
田媖喘气低头,安涌灏结结巴巴问道:“媖媖——你——还在生我的气吗?”
田媖沉默了半晌,才说:“涌灏——我——我们——”
安涌灏屏住呼吸。田媖抬起头:“我们分手吧!”
田媖的话由犹豫突转果断。安涌灏反应过来后眼神木然:“为什么?”
田媖不说话。安涌灏接着问道:“难道是因为那天的事?”
田媖说:“刚才,我爸爸和你说的我都听到了,我希望你也能听进去。要知道,今年,我的生日确实……”
“媖媖,对不起!”安涌灏赶忙说,“可你要知道,我也被蒙在鼓里,我要是真的做了什么违法犯罪的事,我能在这里和你说话吗!”
田媖反问道:“你以为就是这次生日的事!刚才我还听到我爸跟你说了我去年生日的事,你以为我真的就那么无动于衷!”